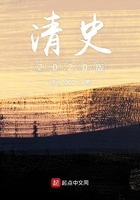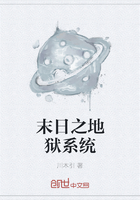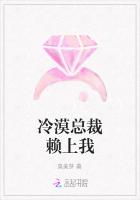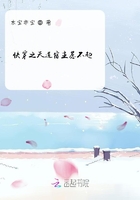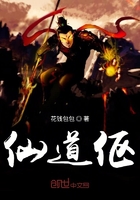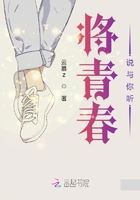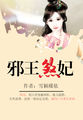巴尔干半岛位于欧洲的东南部。“巴尔干”在土耳其语中意为“多山”,而在斯拉夫语中则意为“山沟和山谷”。这里遍布崇山峻岭,湍湍河流纵横,风光旖旎动人。
在这块约7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星罗棋布着罗马尼亚、希腊、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黑、马其顿、斯洛文尼亚、黑山等10个国家;其中最大的为罗马尼亚,约23万平方公里,而最小的黑山只有1.3万平方公里。如果有朝一日科索沃独立成功,那将在这一半岛上出现第十一个国家。对于我们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一个统一国家中的中国人来说,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然而,巴尔干虽然离我们很遥远,但却并不陌生。熟读过英国诗人拜伦诗选《哈罗德游记》的人肯定会被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英勇精神所折服。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在长篇小说《前夜》中所塑造的保加利亚民族英雄英沙洛夫的形象为中国人民深深景仰。保加利亚诗人瓦普察洛夫的诗集《马达之歌》和组诗《祖国之歌》曾鼓舞世界人民为反对德国法西斯而斗争。
正是在这里,古希腊人创造了光辉的欧洲古典文明。也正是从这里,亚历山大大帝率领他的常胜军,踏上漫漫的东征之路,缔造出一个世界大帝国。长期统治巴尔干的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先后在这一半岛上传播和孕育天主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使它成为三大文明的交流和融合之处。
巴尔干并不是孤立的,它和外部世界紧密联系,息息相关。19世纪巴尔干各国人民开展的解放斗争触动了欧洲列强的每一根神经,使俄、奥、英、法为了巴尔干的每一寸土地争斗不休。20世纪初,巴尔干更成了欧洲的“火药桶”,萨拉热窝的枪声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意渗入巴尔干,随后又吞并了整个巴尔干。二战后,巴尔干成为美苏较量的第一个场所,铁托和斯大林的斗争则撕开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一个裂口。
巴尔干不仅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极其复杂,就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内斗不断,很少有和谐相处的时候。
除罗马尼亚、希腊、阿尔巴尼亚三个民族外,其他巴尔干的民族都是于6-7世纪来自欧洲东部的斯拉夫人,通称为南斯拉夫人。他们血脉相通,文化相近,可以称得上是同文同种。试以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为例,他们出自一个祖先,到了巴尔干又毗邻而居,即使是使用的语言也是同一种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其差别仅在于塞尔维亚语是基利尔字母,而克罗地亚语则是拉丁字母。由于接受文化的途径不同,后来克罗地亚人接受了天主教,而塞尔维亚人则信奉东正教,似乎正是这种差别使他们成为世仇。
在南斯拉夫王国(1929-1941年)时,塞尔维亚人掌握了大权,便千方百计欺压克罗地亚人;而一旦克罗地亚人建立克罗地亚独立国(1941-1945年)时,便依靠德意侵略者,大肆屠杀塞尔维亚人,这种相互的仇恨和残杀在二战结束后也不时表现出来。
更明显的例子表现在波黑身上,那里居住着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和皈依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他们来自一个祖先,差别主要在宗教信仰上。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是基督教徒,早就被公认是民族,然而穆斯林却长期未获得民族的资格,只有到1971年才被确认是一个民族。在波黑内战(1992-1995年)中,这三个民族相互残杀,发展到种族清洗的程度,真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随着意识形态对抗的消退,潜伏在底层的民族矛盾便处处喷发出来。正是民族矛盾摧毁了苏联,也正是民族矛盾撕裂了南斯拉夫。
在当前和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民族问题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有关什么是民族的定义就有多种,有些西方学者把它归之于纯粹精神的东西,1981年在贝尔格莱德出版的《民族与社会主义》一书中指出:“民族的真粹在于文化和精神的共同性,它是由共同的国家产生和锤炼出来的……”,甚至强调:“民族是一个灵魂,是一种精神原则,作为一个个体,民族乃长期努力牺牲和无私的顶峰……”而另一些学者则又突出民族的自然性一面,认为,民族“是一个自然的社会,就和人类、家族和国家一样……共同的起源和共同的生活使他们具有同样的身体,尤其是心态上的特征……”
我想,我们不应纠缠于一些理论和名词上的争论,而应把注意力放在历史和现实的探讨上,而巴尔干那里众多的民族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佳的研究场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人种、语言、宗教、文化在巴尔干小国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我们何不以此为契机,对民族问题作一番认真和深入的探讨。
我还是在20世纪50年代就读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时接触过南部斯拉夫人的历史,不过当时并未引起多大的兴趣,反而觉得这么多小国彼此争斗不停,令人十分费解。
只有在40多年过去,当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实施狂轰滥炸时,曾经在我心头一掠而过的巴尔干终于又激起我强烈的义愤和无比的激情。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不能容忍,在20世纪末,当人类已在革命的波涛中搏斗近300年后,仍能允许一批打着文明旗帜的强盗在光天化日下进行抢劫和杀人的勾当。
科索沃战争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巴尔干一时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大街小巷都在议论南联盟是什么样的国家,北约为什么要去打它,科索沃在历史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此时,我清晰地感受到了社会需求的脉搏,毫不犹豫地走出校门,为浦东新区发展部干部培训班、上海市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等20个单位举办有关巴尔干和科索沃问题的讲座,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和好评。
从这一接触社会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学习历史并不意味着专门啃古纸堆,而是可以借助于对过去的了解去认识现在,并进一步去预测未来。
如今新中国六十华诞已过,我国正在继续大展宏图,进一步改革开放,迫切需要更深刻地去认识外部的世界。
外部世界是很大的,但除了美、俄、日、法等大国外,其他小国也绝不该远离我们的视野。
巴尔干是个很小的地区,但在历史上起过不小的作用,即使在当今世界也不容忽视:科索沃的最终地位远未解决,卡拉季奇尚身陷囹圄,等待公正的判决。只要巴尔干平静不下来,欧洲也就得不到安宁。
光阴似箭,1999年至今一晃已十年过去。“十年磨一剑”,其间我写了一些论文,刊登在学术刊物上,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现今我又有可能在过去所写论文的基础上将一本题为《百年风云巴尔干》的文集奉献给读者,令我感到十分欣慰。
美国有位学者名叫卡普兰,1993年出版一本题为《巴尔干的幽灵》的着作,受到克林顿总统的青睐。后来的小布什总统还曾邀他到白宫去长谈,在制订波黑政策时征求了他的意见。
中国很大,但研究巴尔干的人真是太少了。我半途出家,使用的资料基本上是俄文的。希望年轻一代的我国巴尔干学者能直接用保加利亚文、塞尔维亚文、马其顿文、阿尔巴尼亚文、罗马尼亚文……来研究这一地区的历史,形成我国的巴尔干学派。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早已是古稀之年的我,愿与同志们共勉之!
金重远
2009年10月于复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