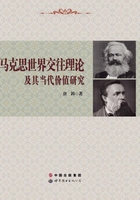在晚期,海德格尔把天、地、人(要死者)、神(不死者)均纳入其思想阐释之中,力图建立一个天地人神四元和谐的至美图景。他早期的世界是此在的世界。在中期,海德格尔放弃了早期的此在,让艺术作品这一独特的存在者,担当通达物性或存在的重任。在作品之中,世界与大地的争执发生为真理。在晚期,他把这个生存世界的结构概括为天、地、人、神的四元合一(dasGeviert)。世界的本性是敞开,是开放性。在技术时代,无家可归作为现代人的规定。“因此,海德格尔的存在的悖论正是这种无家可归的思想表达,这样所谓存在的悖论具体化为人的生存的悖论。”居住是要死者在大地上的一种方式,居住于天空下,居住于大地上,居住于神圣者前。在拯救大地中,在接受天空中,在期待神圣者中,在指引要死者中,居住作为四元的四元保护而出现。天、地、人、神四元世界与语言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四元却是一语言的世界,如果它是被语言所指示的话”。语言使人居住于天地人神的四元之中成为可能,是语言把天地人神聚集为一体。为此,必须以一种泰然任之(Gelassenheit)的态度去倾听语言的道说。在海德格尔看来,“一种居住之所以可能是非诗意的,只因为它在本性上是诗意的”。(VuA,S.206)在本性上,艺术和美的问题是居住的问题,人应诗意地居住于语言的家园之中。
一、无家可归与返乡
荷尔德林问道:“……在贫乏时代里,诗人何为?”
(H,S.269)这里的“时代”指荷尔德林具有历史经验的时代,我们今天仍然属于这个时代,或者说并未走出这个时代。那么,为何说该时代是一个贫乏的时代呢?在海德格尔看来,荷尔德林和我们这个时代之所以是一个贫乏的时代,在于“上帝之远离,‘上帝的缺席’规定了世界时代”。(H,S.269)这不能简单理解为,否定在个人那里和教会中还有基督教的上帝关系,也不是轻蔑地看待这种上帝关系。在荷尔德林那里,上帝的缺席只是意味着,上帝不再把人和物聚集在其周围,而这种聚集是世界、历史与人嵌合一体的前提。
上帝的缺席更为恶劣的还在于,“不只是诸神和上帝逃遁了,而且神性之光辉也已经在世界历史中黯然熄灭”。
(H,S.269)由此到来的无疑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一个不能觉察到上帝缺席的时代,人们甚至还远未意识到上帝离去的可能恶果。世界由此失去了它赖以建立的基础,一个贫乏的时代由此而开始,同时,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也处于完成之中。“实质上,我们共同处于虚无主义的完成中,上帝死了,每一个神性的时空都被掩遮了。”(R,S.390)欧洲的技术和工业支配与统治了全球,“大地和天空、人和神的无限关联似乎被破坏了”。(EHD,S.176)天地人神的合一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
世界黑暗的贫乏时代很久以前就开始了,上帝的缺席决定了世界的黯淡无光,也由此规定了这个时代的无家可归。“海德格尔在现代世界所经验的,却是无家可归。这种经验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它为那反经验所特有。”无家可归折射出了存在自身的悖论,当海德格尔看到从月球上拍回来的地球照片以后,他大吃一惊,其实人用不着原子弹,已被连根拔起,无家可归已成为世界命运。海德格尔认为:“在人的本性中威胁着人的,是这种意见:技术的制造使世界井然有序,其实恰恰是这种井然有序把任何秩序都拉平为制造的千篇一律,从而自始就把一个可能出现秩序和可能从存在而来的承认的领域破坏了。”(H,S.295)技术遮蔽了存在自身,对人类的无家可归负有根本意义上的责任。
现代科技使人类昧于天命而处于最高的危险之中。一方面,由于人通过技术活动把自然展现为持存物,而身处持存物之中的人也开始把自己当做持存物了;另一方面,受到这种威胁的人类总是拔高自己,力图使自己成为地球上的主宰。现代科技的命运是存在的命运,其危险波及存在自身。最大的危险在于人类对此缺乏深思熟虑,冷漠了沉思。而且,在我们今天的高科技与信息的时代,人类中心论把人类推到了生态毁灭等各种全球性灾难的边缘。
在无家可归的贫乏时代,诗人返乡更具有特别的意义。在荷尔德林看来,“至乐的统一,存在,在这个词的惟一意义上,对于我们已消失,如果我们应该努力争取它,我们必须失去它”。存在被遗忘了,人们已无家可归了。这时,存在和家园的意义,才格外地突显。在海德格尔看来,通过荷尔德林所说的返乡,我们想到了游子到达故乡的土地,与乡亲们会面的情景。荷尔德林从康斯坦茨旁边的图尔高镇,经由博登湖,回到故乡施瓦本。荷尔德林在诗歌中,描写了一次快乐的返乡之经验。返回故里,一直是诗人之梦想,“可是,以‘忧心’一词为基调的最后一节诗,却根本没有透露出这位无忧无虑地回到故乡的人的欢快情调”。(EHD,S.13)这何故如此呢?
虽然,故乡的人和物给人以亲切而熟悉的感觉,但是,“返乡者到达之后,却尚未抵达故乡”。(EHD,S.13)到达者在这里依然是寻求者,尽管他魂牵梦萦,梦寐以求的地方现已与他照面,故乡就在眼前,近在咫尺,但那梦想的东西还没有找到。
怀着强烈返乡愿望的诗人,回到了故乡,却不能把握近在咫尺的神,人与神的距离,不是空间上的。神虽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作为寻求者的返乡人,究竟应如何去寻找故乡的本性的东西呢?“为此,就有必要预先认识故乡最本己的和最美好的东西。”(EHD,S.14)什么是这样的东西呢?
这东西与喜悦相关。喜悦是诗人的诗意创作物,喜悦是令人欢乐者,而“作诗就是一种发现”。(EHD,S.15)海德格尔由此看到了,发现与寻找故乡是与诗意创作以及由此带来的喜悦相关的,在诗意的愉悦之旅中,诗人返回家园。何谓家园呢?
“在这里,‘家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只有在其中才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EHD,S.16-17)也就是说,家园是人的存在的本己相关之处,它既不是一个外在空间,也决非纯精神之物。
有的人拥有各式豪宅,却没有家园;有的人浪迹天涯,但总是在家,因为对于思者来说,道路从来就是家园。海德格尔通过阐释表明,那已经在此照面的东西依然是被寻求的东西。对诗人来说,“至高之物”与“神圣者”是同一东西,即明朗者。
作为一切喜悦之本源,明朗者是“极乐”,而诸神是朗照者,更是祝福者。极乐或至乐相关于存在,至乐与存在的丧失,是重新找回的前提,正因为已经失去,才弥足珍贵。“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一种世界命运。”(W,S.339)上帝缺席的黑暗时代规定了无家可归,技术的肆虐使家园不再存在。
虽然,诗人已返乡至近旁,却仍是家园的寻求者。越是失去了家园,返乡之愿望越是迫切。诗人虽已来到家园,却还在找寻。对此,荷尔德林说道:“神近在咫尺又难以把握。”(EHD,S.21)同时他还说,诗人,“他以此来命名故乡的本性,故乡那最古老的、最本己的、依然隐而不显但原初地已经最有准备的本性”。(EHD,S.22)故乡在近旁,却隐而不露,在海德格尔看来,“返乡就是回到本源近旁”。(EHD,S.23)因为故乡就是本源之处,而返乡却是一条永恒的道路。
返乡就是切近本源,“与本源的切近乃是一种神秘(Geheimnis)”,(EHD,S.24)但这种神秘并不表明我们缺乏认识,而是说切近作为神秘是其自身的本性,“不过,我们决不能通过揭露和分析去知道一种神秘,而是惟当我们把神秘作为神秘来守护,我们才能知道神秘”。(EHD,S.24)在这里,海德格尔否绝了一切逻辑与认知之于神秘的意义,因为逻辑与认知是无助于对神秘的把握的,把神秘作为神秘来守护这就足够了。
在贫乏时代,诗人何为?“作诗乃是对诸神的源始命名。”(EHD,S.45)作为要死者,诗人吟唱酒神,追寻诸神远逝的踪迹,盘桓在神迹处,探寻抵达之道。“在贫乏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之踪迹。”(H,S.272)其实,道路就是家园。诗人不能无视这时代的命运,“诗人思入那由存在之林中空地所规定的处所”。(H,S.273)诗人关切与思存在之命运。
“这种无家可归状态是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的标志。”(W,S.339)存在之被遗忘却是贫乏时代贫乏性的隐含本性。不同于一般的诗人,“荷尔德林是诗人的诗人,并不是因为他缺少创作冲动,而是因为他认识到了把诗人重新带回其源始本质的必要性”。正是像荷尔德林这样的诗人的诗人,才能引导人们对存在的经验,为神(不死者)的重临作准备。
“时代之所以贫乏不仅是因为上帝之死,而且是因为要死者甚至连他们自己的终有一死也不能认识和承受。”(H,S.274)不能正视人自己之死和上帝之死。由此,时代步入了贫乏,也正因为如此,要死者不能把握他们的本性,死亡成为谜,人们已不能辨认神迹了。“时代之所以贫乏乃是由于缺乏有关痛苦、死亡和爱的本性的无蔽。”(H,S.275)这一共属的本性领域之自行隐匿导致了时代之贫乏。
人比其他存在者更深入地切入存在者之存在之中,诗人更是如此,诗人里尔克在途中也体会到了这种时代之贫乏。“里尔克以他自己的方式,诗意地经验并承受了那种由形而上学之完成而形成的存在者之无蔽状态。”(H,S.275-276)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向里尔克显现自身。里尔克称自然为源始基础,这里的自然既不对立于历史,不指涉自然科学之对象领域,也并非艺术之对立面。“‘自然’乃是历史、艺术和狭义的自然的基础。”(H,S.278)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者之存在是冒险”。(H,S.279)里尔克把自然思为冒险,追问存在与寻求自然无疑是一项冒险活动。然而,“哪里有危险,哪里拯救也在生长”。
(EHD,S.21)当海德格尔借用诗人荷尔德林这诗句时,他旨在表明,正是陷入危险之中,才使拯救成为可能。
在无家可归的贫乏时代里,“只要危险同时是拯救的话,那么无家可归将内在性地和家园相联,此家园召唤着返乡”。无家可归是技术时代的根本病症,但其救治之策不是要抛弃技术,而是要克服技术化与技术主义。对海德格尔来说,荷尔德林的重要意义在于,他在古老的诸神已经消失、新的诸神尚未来临之际,为人类经受苦难。在荷尔德林之后,我们当今又进入了一个信息的或网络的时代,在这个“崭新的”时代里,返乡与守护家园仍然是最为迫切的时代任务。“作为美妙事情的歌者,冒险更甚者乃是‘贫乏时代的诗人’。”(H,S.319)诗人们诗意地追踪他们必须道说的东西,荷尔德林是贫乏时代诗人的先行者。无家可归的时代呼唤诗人返回家园,进而召示人们守护好家园。
二、天地人神的合一
天地人神是海德格尔晚期美学思想中极为关注的四元,在本性上,此四元相处一体,不可分离,“这样,在赠物之中存在天、地、诸神、必死者四者。这四者自然结合起来,合为一体”。海德格尔力图揭示这四元各自的存在、运作及其关联,以及这种合一之于人类生存与居住之意义。这四元在这种合一中,各居其位,各得其所,和谐相处。
在四元中,大地是承担者,大地显示自身为万物的载体,入于其法则中被庇护和持久地自行锁闭着的东西,万物处于大地之幽闭之中。大地孕育繁衍生命,产生了植物和动物,植物开花结果,动物嬉戏于其上。大地伸展为石头、水等。海德格尔的“大地”(dieErde)一词受荷尔德林的启发,“很明显,它就是荷尔德林的诗,当时海德格尔带着强烈的热情转向了他,从他的诗中把大地的概念转化为自己的哲学语言”。此时的大地不再是与世界相争执的大地,而是处于世界之中的大地。
天空是太阳之苍穹,也是月亮运行变化之所。在天空中,繁星闪烁,四季更替,白昼之光明与夜晚之黑暗交替变幻,天空有气候的温和与寒冷,也有浮云与湛蓝。鸟类在天空中自由地翱翔。此外,天空充满了风云突变,有时风和日丽,有时却雷电交加。
神圣者是神性召唤的信使,应神之呼唤而出现。但这种关联容易被理性地理解与把握,“由此可见,希腊众神在荷尔德林的时代被再现的危险,发自既是理性关系(ratio)亦为根据的概念,即出于根据。出于怎样的根据?
共同心灵的感觉根据”。如何看待这里的神圣者以及海德格尔思想与神学的关系,有各式不同的观点。把神圣者作为不死者的观点是可取的,“因此海德格尔有关诸神的言谈既非古希腊的诸神,也非中世纪的上帝,而是作为四元之中的不死者”。当然,这不死者也不是诸神和上帝的替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