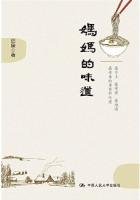平路
幽谷拾光
你的名字,有风呼唤的深情,你的名字,有云低泊的深情。当远山轻吻云的红唇,便化作一只蝴蝶,在情感的世界里飞旋,然后,飘然而逝。
蛟龙出海
雾色的玻璃外面,行人在楼下穿行。玉茹瞪着腕上的表,吸了口咖啡,想着他已经迟到多时了。
每次男人晚来,都是睡过了头,耽误约会时间。玉茹想着要送他个闹钟,但终了没有送,她很珍惜他们的感情,生怕这个“送钟”的谐音不吉利。
而男人总在玉茹下决心离开前匆匆赶到,眼里还有点惺忪。男人是画设计图为生的人,常常晨昏颠倒。他晚上在家工作,因此约会的时间必须是白天。尽管体谅男人睡眠不足的苦衷,玉茹却照例要嘟起嘴,半撒娇半呕气地编派他的不是。这时男人总会懊恼地搔搔头说:
“‘她’忘了叫我起床嘛!”
这个“她”,指的是男人的妻子。
男人说到妻子,总是一声“她”就带了过去。多次之后,这个“她”渐渐变成那个女人的专有名词。玉茹与男人谈话时总特意回避这个字眼,可是“她”好像无所不在,对于已成定局的“她”,玉茹并不嫉恨,倒是敬畏无比的。
这时候,雾色的玻璃里面,玉茹不时抬起头,望望那扇开了又合的自动门。然后玉茹低下头,数着表上的分针一格一格走过去。而男人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究竟他会不会来?
——老实说,玉茹全然没有概念。男人并不是碰到塞车,也不是临时有旁人的电话,更不是被重要的事耽搁了,如果有事情,男人总可以拨通这间餐厅的电话告诉玉茹一声。而男人却是在眠梦中,沉沉地睡下去,如果“她”还没有叫醒他的话。
想着,玉茹仿佛听见男人呼噜噜的鼾声从卧房里传出来,那位妻子安然地在水槽前洗茶杯,往金鱼缸里撒鱼食,朝洗衣机中量着肥皂粉……巷子里的岁月静好,墙上的挂钟仿佛停住了,又好像还在滴答?……只是,妻子忘记了将丈夫唤醒去赴另一个女人的约!
茫然的等待中,玉茹继续想像公寓里的景象:壁上一个挂钟,茶几上该有一台电话,黑色的?绿色的?还是奶油色的?玉茹绝不敢拨电话过去,太启人疑窦了。那位“她”很可能将这通电话与唤醒男人两件事情联想在一块,那可不得了!玉茹知道自己什么也不能做,只有痴痴地继续等待,然而,究竟那个“她”什么时候才会走进屋里,叫醒熟睡的丈夫?
焦躁地坐着,玉茹触摸杯子的指尖渗出了几许汗息。
喔,男人与自己能否如约相见的命运竟然操在“她”手里……难道也象征这份感情——其实——掌握在另一个女人手上?……想着,玉茹不由慌乱了起来。怎么会这般复杂?玉茹不解地自问。自己只是极单纯地爱上了一个男人,想要与他见面,如此而已。
玉茹明白,自己并没有妄想什么,她仿佛也不妒嫉,只是巴望着能够见到自己所爱的男人。但是,真的这么简单吗?
男人哪一件事不与那位妻子的“她”相连在一起?他们是一对夫妻,玉茹的情人是一个家庭的部分,实际上是玉茹在爱那男人的时候,已经介入到他的家庭里。
而那个家,毕竟是别人的家庭!颇知分寸地,玉茹也悄悄地问过那男人:“你们家,少一个闹钟吧?”玉茹凑近了脸来,“听说送人家钟不吉利。”玉茹斜睇着男人说,只希望男人领悟,自己去店里买个闹钟。半晌,男人声调平平地道:“我不喜欢被闹钟惊醒,睡到一半被吓醒,我不舒服嘛!”
这一瞬间,玉茹手里的咖啡杯也微微地颤动起来,想像中仿佛合着男人打鼾的节拍。不喜欢被闹钟惊醒,那么,男人喜欢什么?喜欢被一只温软的手臂轻轻摇醒?玉茹低下头思忖。而深一层的意义上,这正显示男人说不出地依赖着妻子、依靠“她”决定自己的作息吧!想到这,王茹的胸口竟泛出酸酸的气泡,才说过不吃醋的,玉茹恨自己好不争气。
同时,玉茹的鼻腔亦一阵阵地……酸楚。哎,玉茹叹口气,只怪自己竟这么样爱上了这个男人,才会去将就男人的时间,才会坐在这里怔怔地等,才会觑着男人作息的暇隙与男人相见。而尤其令玉茹感到委屈的是,男人的时间表要靠那位妻子的“她”决定,妻子才是男人的闹钟,于是那个“她”,竟然也间接地决定了玉茹的时间……玉茹揉着一方手纸,坐在那里泪眼婆娑起来。
泪光中,玉茹望着喝干的咖啡杯底,黄苦苦地。据说吉普赛人可以从咖啡杯的渣滓卜算人的命运,如今,杯底仿佛写的是一张忧伤的面容,并且正一点点地枯竭下去。而这样地一天一天地等,在虚悬的时间里等待,盼望的男人却老是不来……玉茹想想,又涌出了新的泪水。
王茹也哭得累了,有点瞌睡,仿佛是一场梦。男人来的时候,玉茹在迷糊中好像被闹钟惊醒——
数日后,玉茹作了分手的决定。临到那个时刻,玉茹告诉自己可要坚强些!一如往常地,玉茹在那家餐厅里等待男人,等他下一分钟推门进来。
男人又迟到了。坐在那里,玉茹很有耐性地继续等着。
玉茹小口地吸饮咖啡,再将杯子放回瓷碟内,杯子旁边还搁了一盒包装精美的礼物。
滴答滴答地,礼物正替他们的爱情作最后的读秒……
诗文并茂
一个女人回到自己的居所
一个女人就要从那个臆想的岸边回来
让那些奔跑的思想择一处歇脚的地方
太多的时间都被变幻着心绪挤满了
她必须抽回身来只留一滴泪水
去湿润那个野外的情人
然后回到自己的居所然后
像孩子一样纯净地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