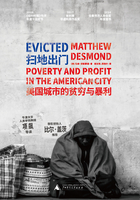陈毓
幽谷拾光
一头乌亮的头发如何能维系两个人的爱情?仅仅靠幻想的美丽如何能适应现实的残酷?爱情呵,靠两颗心相互聆听,靠两双眼相互交融……
蛟龙出海
一切都可能通往爱情。
比如一个人的头发。
赵大卫爱上妮子,就缘于妮子的一头如瀑长发。用大卫的形容,那是一种比黑暗更黑的黑,黑暗在它面前显得灰暗。黑暗是单色的;而妮子的头发却拥有阳光的七彩,那是要让最美丽的鸟羽都要黯然失色的色彩。
大卫第一眼看见妮子长发飘飘地走进自己视野的时候,就把妮子整个地想成了一幅画儿。大卫后来所做的一切是如何把这幅画儿装进自己的镜框。
大卫没料到那幅画儿竟到了自己眼前。妮子就坐大卫前排,妮子的同桌是位黑黑胖胖、慈眉善目的女生。大卫心中装满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窃喜。
在那幅画儿后面坐了四年之后,大卫平常还真把那幅画托了,装框。大卫娶了妮子。
结婚时大卫递妮子一个雪白信笺。妮子打开,就看见一些干的海棠、丁香瓣、花瓣间根根青丝,如醉卧花间的小青蛇。妮子一眼看去,就认出是自己的头发。
那是大卫大学四年里完成的又一项学业:收藏妮子落在他课桌上的每一根头发。妮子看头发,再看大卫,妮子眼里一片缠绵。大卫说,永远都别剪断自己的头发,妮子。看过“百年润发”的广告吗?那是他们百做不厌的一种游戏。那本身也是一幅画儿。一幅运动着的油画儿。想想看吧,一个连自己妻子的头发都爱到极致的男人没理由不去爱自己的妻子。这种力量足以抵挡一切生活的小冲撞。妮子为此感到幸福,并且感到满足。但生活的小碰撞还是说来就来了。如同两根质地很好的绳子,编着、编着,就突然打了个结。
大卫想不明白。妮子想不明白。越是想不明白越是要想明白。结果大卫愤怒地将自己摔向沙发。结果妮子愤怒地将自己关进卧室。妮子看见镜中自己黑色的长发如同黑色的火焰,妮子再看自己愤怒的眼睛,如同火焰中的火焰。仿佛为了制止火焰的进一步上涨,妮子用剪刀轻轻碰触了一下,一缕黑色火焰就悬垂在了妮子苍白的手指间。
“美丽的东西都是脆弱!”妮子想。同时生出一种自虐的心痛。
开始的时候,这种龃龉像夏天的雨,来得快速,去得迅疾,接着是双方争着道歉。是哭,是笑,是笑中的吻……于是他们的亲密又回到了初时的起点上,温度是比开始还要热烈的热烈,是比开始还要甜蜜的甜蜜。大卫说,再不许剪头发了噢?妮子说,我只在乎你。大卫无限爱怜她:你多傻啊!彼此眼神里一片潋滟。更大的风雨到来是在他们没有预料的时候,仍是为着他们后来谁也没记住的原因。那情景很像是两只渴望走近而又彼此伤害的刺猬。妮子只能剪自己的头发。
妮子最初那点自虐的心痛渐被一种“复仇”的快意所代替。
妮子要让大卫也心痛。
果然。当她拎着那缕黑发脚步“得”、“得”地走过仰倒在沙发上的大卫身边时,妮子看见一抹红涨现在大卫脸上。妮于继续前行,把那缕死去的头发从阳台上扬下去,仿佛扔下去的是与他们全然不相干的东西。妮子回过脸来,在大卫的惊愕与愤怒里一脸无故。大卫在一种无对抗的战争中将拳头砸向自己脑袋,摔门出走。争吵到此画下一个暂时的休止。妮子的眼泪悄无声息地落下来。
但那扇被摔上的门注定是要再次打开的。只因为他们彼此相爱。这是惟一的理由。尽管他们对这种分不清谁胜谁负的战争充满了说不清楚的疲倦。包括这种一手握矛一手持盾,渴望战出一片晴明的样子。
妮子的头发现在是短得不能再短。妮子再次晃着个刺猬头冲到大卫跟前时,大卫是比任何一次都重重地把门摔上了。摔上的门静止了很久。
门外的人没有进来,门里的人也懒得出去。
妮子不得不出门的时候,竟意外地看见了大卫。她想喊他,却怔住了。妮子看见一个长发飘飘的女子走在大卫身边,她那美丽的头发照耀着妮子的眼睛,正是大卫曾形容过的那种,比黑暗还黑,又容纳了阳光的七彩的,连最美的鸟羽都要黯然失色的质地。
那个未喊出口的名字进退两难地停驻在妮子嘴边。
妮子忘了出门的初衷。
诗文并茂
黑头发飘起来
黑头发是真实的
是一种比黑暗更黑的黑!
是终极的幻想和诗意的抒情
它在离现实很远的地方
飘起来拨动欲望的大火
越烧越旺
我躲在暗夜的深处一次又一次地
嘲讽着长发的爱情
并竭力拯救那些
落难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