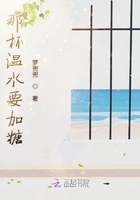沈艾往四王子身后瞥了一眼,果不其然,看到了抱剑端坐的盛。他依然俊朗,但却多了几分消瘦和疲倦,如同一树翠竹,在皑皑秋霜中冻落了几枝。
避开他忧色深沉蓝色眼眸,沈艾扭头,看着一身狼狈的银月,不知为何地,心底莫名泛起了一丝快意。
“昨夜何时祭月?”沈艾问道。
“戌时。”那葛衣侍女低头应喏。
“昨夜安陆先生所奏的,正是《长沙泊》《大禹引》和《平江阴》。”
沈艾立于堂前,白暂纤细的脖颈微微扬起,清澈的明眸磊磊落落。
安陆先生起身,点头应是。
安陆先生爱乐,众人都知道。但他不但爱乐,还善乐,尤擅鼓瑟。
虽然贵为遒正,可却很少请贤士或乐师上门奏乐。往往都是自己动手,架一张古瑟,在院中对月独奏。
遒正府毗邻牧正府,沈艾在东院的小园练剑的时候,时时听得隔壁的高墙内传来琴声。听得久了,慢慢也摸出一些规律来了。
昨夜沈艾哪都没去,专心在屋中修炼内劲,本来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明。但听得大王子质问,想到昨夜正是月圆之夜,她便冒险一试。果不其然,正是这三首。
安陆先生所言完完全全证明了沈艾“清白”,确实如果安陆所言非虚的话,昨夜沈艾是断不可能出现在五里之外的驿馆的。
“慢着,昨日戌时我正在我表兄府上。”
似乎是被沈艾的举动提醒了,银月连忙道。
见众人看来,盛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不管盛的话是真是假,银月毕竟是孔夫人的娘家人,嫡亲表妹,谁也没想要真正处置她。
见寻不着罪魁祸首,大王子出面好好安抚了三公主愉一番,承诺会好好查明。如此一场闹剧,便不了了之。
直到有虞氏的使者归去后,珊瑚钗依然了无踪迹。但很快,各部落的人也无心关注这些了。
春狩过后,又是秋狩——
时下游猎之风盛行,不但大禹喜欢打猎,他的后代太康,更是因为耽于游猎,重用佞臣,被人夺了皇位。现在的大夏虽然还是大夏,却由权臣漪代理,早已不是夏侯氏的天下了。
伯熠自寿辰前偶感风寒,便一病不起。一直到现在已经入秋了,也不见好转。
大王子在朝中势力庞大,早年征战各部,为有仍氏立下赫赫战功,但奈何出身不高;四王子身份高贵,可惜生得太晚,较大王子年幼廿岁,在朝政上处处都输他一截。
如今伯熠病入沉疴,两人暗潮汹涌,朝堂上一片混乱。这个时候,秋狩节的到来,倒不失为一着缓和剂。
车队缓缓前行,像一条长蛇,朝着天际蜿蜒前进。
每隔十丈滚动着一辆车,前后来回梭巡着策马驱驴的护卫。为了显示身份,除了有限几辆贵人的车架套上了马,其余身家不甚丰的勋贵都用上了牛车。
似乎是想证明自己宝刀未老,本应病卧在床的伯熠今年秋狩居然领头出行,大王子和四王子自然更不会放过这个难得可以在首领面前好好表现的机会。
这也是本来就庞大的队伍,一下更为臃肿。行驶了月余,方才到太山脚下。
自古便有“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这样的喟叹。
群峰拱岱,满目苍翠,泰山的雄伟巍峨,即使是在五千年前,也一样有着震撼人心的魅力。
到达目的地,众人欣喜,纷纷解下车架,动手安营扎寨。按照爵位序齿,伯熠居中,从中心往外,依次下来。贵族人家有自己的家奴,手脚利落,很快便弄好了。
接下来的几天,便是自由狩猎。
沈艾这次有幸得到遗君的批准,跟着他一块过来,一开始还很兴奋。
没想到狩猎用的弓箭非常简陋,不过一根勒弯的木头系上兽筋,沈艾不得要领,射起来半分准头也无。再加上在山林中骑马与平地不同,林中枝橫根错,阻碍颇多,每几天她大腿内侧便生生磨掉了一层皮。
于是昨天切切恳求了一番后,今日便得到允许,被留在了营地。
太山的风景虽好,但磨伤了大腿,行动不便,只能呆在营帐之中。百无聊赖,沈艾坐在榻上,取出这两天让她万分头痛的弓箭,细细研究了起来。
沈艾从前在军营里也碰过两下弓箭,虽然没有真正学过,起码也有些了解。后世的复合弓且不说,眼前这张弓从形制上勉强归类的话,更接近小梢弓。
弧形的弓身不过半臂长,中间微微凹陷,缠上藤草,使不至于滑手。箭矢不过是削尖的一根细棍,尾端有一小个身份徽记,也无箭羽,射出去自然既无射程也无准头。
也不知道有仍氏的人是怎么运用这些简陋的工具,捕获到堆积成山的猎物的。
沈艾正自出神,忽闻帐外传来了一点异常的动静,她按着剑鞘,厉声喝道。
“何人!”
帐帘一掀,门外空落落的。
“是我。”
一声可怜巴巴的童音响起,随之一个小脑袋从石后伸了出来,原来是齐。
一贯如常的冲天辫系在头上,但不知道是不是情知主人的心意,有些歪倒,看起来无精打采。总爱骨碌碌的大眼睛也有些黯淡,但傲气的神色可没有变,一见沈艾,就不满地瘪起了嘴。
沈艾自然知道他在不满什么,事实上齐根本就是被无辜牵连的。自戒身死,沈艾就再也不愿见盛,盛屡屡上门,都被她赶了回去,更不用说齐了。
其实不见齐的原因很简单,她怕自己心软——
看沈艾面无表情,白面团也似的小脸渐渐皱成了一团,那双晶亮亮的大眼闪过了一丝受伤的神情,像只垂头丧气的小狗。
“不愿见就不愿见,以后再也别见!给你,臭婆娘!”
齐把一个巴掌大小的白色陶罐砸向沈艾,随后一转身,迈着两条小短腿旋风也似地跑走了。
沈艾低头一看,原来是一个药罐。看着药罐里的墨绿色药膏,不问可知齐因何而来。想起齐受伤的神情,沈艾不由地忆起远在他乡却恐怕永远也无缘得见的弟弟,心里纠成了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