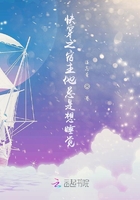五十盾牌手冲将上前,第一队呈一字队列,士卒单膝跪地,将盾牌紧紧相接,在城下排开。第二队五十人迅速跟上,以厚重的铁盾包裹了数层皮革,稳稳架于第一队盾牌之上,形成密不透风的防御之势。
岭山城上箭镞如雨,却几乎被城下的持盾步军格挡了去,加之岭山城少有战事,叛军并无足够的作战经验。第一轮箭雨过后,却未曾伤得城下军士分毫。
趁着楼上弓手喘息之机,二队盾牌手忽然撤下,百余火铳手已经就位,瞄准城楼之上的箭迅猛点火。
只听“嗖”地一声,似有急速飞驰的铁弹擦着侧脸而过,“叮”地一声钉如身后的墙壁之中。宗诏不由侧目,“这是什么东西?”
“此火铳也,乃是为此一战特地研制的器械!”身后那反臣躬身道。
忽然又是“砰”地一声,宗诏只觉双耳若混沌般不辨事物,再看身侧之人,额上竟是生出一个指甲盖大小的血洞,边缘的血肉溃烂漆黑……此人双目空洞,尚未来得及说一个字,忽然倒地身亡。
火铳手弹药射尽,自然需要时间填充枪膛。第一轮火铳手退下的瞬间,百余弓手轮换而上,对着城楼又是一番猛射。
宗诏被众人簇拥着连连躲闪,不曾想到自己离开明城的这些年,兵器也有如此大规模的改良。只是火铳虽然凶悍,遇到雨天则发挥不出任何作用,更何况需要盾牌、弓手的掩护。宗诏躲闪之间,但见弓手退下,铳手再次开始猛地向上射击。
宗诏大呼一声“箭来”,却是执了弓箭向身先士卒那人瞄准。
辅国将军陆景明寒族出身,从小小的步兵营摸爬滚打,一路扶摇直上。人言其勇冠三军,也不过是以不要命的冲锋陷阵换来的。宗诏冷笑一声,不论是弓手、铳手还是盾手,都需要长期的演练配合。可是城下的弓手、盾手配合得当,毫无破绽,火铳手便不那么灵活了。
待到铳手再次退下,弓手上前之时,宗诏猛地松手,破空之箭离弦飞驰,直飞陆景明而去。
陆景明当即侧身躲闪,那箭羽贴着兜鍪而过,不曾伤得他半分。哪知他刚一侧身,又有一箭横飞而来,直射向他面门!他双腿夹紧马腹,却是仰面向后,便又躲过一箭。紧接着又有箭羽疾飞之声,“噗”地一声没入身下的马腹之中,马儿吃痛“聿——”地嘶鸣不休,载着他高高跃起。
古有参连之法,即先放一箭,而后紧紧射出三箭,教对方再无招架之势。陆景明有把握格挡、躲闪直飞而来的箭羽,却不料宗诏阴险,第三箭竟向他的战马瞄准。陆景明一边握紧缰绳,一边躲闪再次袭来的第四箭。
这一箭似是承载了开天辟地之力,又疾又狠又稳,未待陆景明躲闪,箭镞已经刺入他的血肉之中,钉在他右臂之上。长箭入肉,第一反应并不是疼痛,而是彻骨冰凉。
陆景明并未因此停手,未待军士上前查看,却是兀自捉住箭杆,“噗嗤”一声拔出、掷在地上,而后大喝一声,“全军攻城!”
士卒拥着十余攻城车向前冲去,及至岭山城下,杀戮才真正开始。陆景明在马上坐了一会,觉着头晕目眩,再看右臂之上的血洞,却是冒着汩汩黑色。
好霸道的毒!陆景明强撑了一会,终是颤巍巍地坠下马去。
及至傍晚时分,岭山城之下尸横遍野,叛臣宗诏不敌楚军攻势,带着百余叛军自西门奔逃而出,往遥城方向逃窜。黄远率军入城,连忙命医者为辅国将军诊治伤势。而后又根据城中的服役名单,摸清了叛军人数。
陆景明的伤势算不得重,可那箭镞之上淬了毒,军医清洗伤口、解毒诊治之后,便见将军的面色稍有缓和,终于不再是先前的乌青模样。
黄远在他床边站了一会,忽然觉着床架“哗啦啦”地摇晃。他以为突发地动,一时慌了神。再站立片刻,却见那床架依旧摇摆不休。黄远当即单膝跪地,躬身向床下望去……
“我没有同宗诏同流合污,饶命,饶命啊!”
黄远一把将躲在床下之人揪了出来,但见这人不过是个不堪一击的瘦弱书生,竟是连怀里的刀也抱不稳。
“这不是余龙图大人吗?”黄远不由皱眉。余览乃是丞相余尧之子,因在北齐太子赶赴明城之时,对其投毒未遂,又嫁祸给林太傅,故而被流放至此。
“是我,是我!”余览连滚带爬,依旧是瑟瑟发抖、面色惨白。他前半生衣食无忧,乃是明城贵胄之中的翘楚。因为自己写得一手好文章,父亲又是丞相,故而骄纵无理又目中无人。自从被流放到岭山城这穷乡僻壤之地,白日里开山凿路,入了夜饥寒交迫,还哪里有半分贵胄模样?
他总算是明白林馥当年在军中有多么不易,但凡长得周正白皙些的男子,竟然还会时不时的被五大三粗的汉子当作女子调戏!
耻辱啊,耻辱!
正在余览不知所措之时,床上的人忽然睁了眼,而后艰难地张了张口,“黄大人可曾派兵……追击宗诏?”
黄远连忙扶着他起身,“已派一千士卒向西追去。”
余览听到二人谈话,却是惊愕道:“别追了,宗诏不过是一枚弃子,蛮子的目的是宁仓府!”
陆景明微微挑眉,“余公子可否说得详细些?”
岭山城虽是南楚官吏的流放之地,但并非所有人都似宗诏这般一心反叛。余览和宗诏同为明城世家子弟,二人自幼相识,宗诏又比他先流放至此。若非宗诏的照应,他一个文人又岂能在这般恶劣的气候下安然度过寒冬。
可是相处得久了,余览便觉察到了宗诏的秘密。他早就和南夷互通音讯,甚至每年春天,夷人沿城烧杀抢掠,而后四散奔逃难以追击,都少不了宗诏从中出谋划策。
他知晓秘密的当夜,被宗诏扼着咽喉威胁。要么与他一道投了南夷,日后高官厚禄不在话下,要么被他当即捏死,将尸体扔到神岭山的冰川之下。余览乃是余家的唯一男丁,哪里肯大义凛然去赴死,自然是痛哭流涕、请求宗诏庇佑。
及至庆安王南下的消息传来,宗诏与南夷的通信愈发频繁,竟是商议引狼入室,教南夷悍将蒙峰引了士卒北上,直攻遥城而来!
余览自诩是个文人,没有上阵杀敌的本事,也没有运筹帷幄的智慧。可余家世代公卿,他的父亲是当朝丞相,他岂能在此时眼睁睁看着宗诏引狼入室。他一人拿不下宗诏,便偷偷将消息透露给了城守张兴。张兴尚未来得及动作,宗诏已率反叛冲入城守房中,将他擒了出去,于之众目睽睽下削了首级。
余览躲在张兴床下,侥幸躲过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