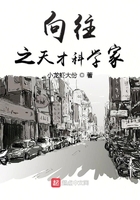陈晓律
现代民族主义是对当今国际政治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欧内斯特·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政治原则,它坚持政治与民族的单位必须一致”。他甚至断言,没有现代的国家政权,就没有民族主义问题。汉斯·科恩则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心理状态,即个人对民族政权的忠诚高于一切。这种心理状态是同生养他的土地、本地的传统以及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权威等等联系在一起的。哈维丁·凯却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创造出来的东西,是现代国家政权在近代初期欧洲西部地区的特殊的环境下长期行使权力而产生的。安东尼·D.史密斯则认为民族主义是欧洲人渴望一个充满自由与正义的王国的产物,与千年王国运动有很密切的关系。著名诗人泰戈尔则认为,冲突与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它的基础不是社会合作,它已经演变成为一种完备的权力组织,而不是一种精神理想,泰戈尔甚至认为民族的概念是人类发明的一种最强烈的麻醉剂。“在这种麻醉剂的作用下,整个民族可以实行一整套最恶毒的利己主义计划,而一点也意识不到他们在道义上的堕落。”与此同时,汉亭·昂格则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民族的概念就如同自由的概念一样,是一个光辉的字眼,并指出那些不合乎自由原则的所谓民族主义根本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虽然民族主义情绪早就存在,但只是到18—19世纪才发展成为要求每个民族都建立本民族的政权的政治原则。海恩斯则从四种含义上来解释民族主义:“第一,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的民族主义,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义成为创建民族主义国家政治联合体的支持力量; 第二,作为一种理论的民族主义,它是提供给实际历史过程的理论、原则或观念; 第三,民族主义包含着一种政治行动,如特定的政治党派的行动; 第四,民族主义是一种情感,意指一个民族的成员对本民族国家有着超越于其他的忠诚。”学者们对民族主义热烈的探讨,反映出民族主义在20世纪以前的政治舞台上所拥有的巨大能量。
在冷战结束后,很多学者曾一度认为民族主义“已经过时”,它应该成为“历史”,但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却往往出人意料,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多年,民族主义不仅依然拒绝退出历史舞台,并且还在各种国际冲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现象迫使已经准备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过去时”对待的学者不得不重新开始了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冷战后出版的几本关于民族主义研究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突破,其使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主要有两点:第一,将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联系起来,即认为现代民族主义是现代化起步的意识形态,是催生现代国家的重要力量,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现代国家。民族主义是构建现代国家的重要工具。因此,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是共生物。第二,将民族主义按照发达国家的特点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不再统一地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类型,而是将民族主义与具体国家的发展历史联系起来分析,从而产生了在世界上不同种类的民族主义。因为各国要解决的现代化问题各不相同,所以,民族主义所要承担的任务自然也不一样。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美国的与俄国的民族主义都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国家传统和现代化历程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复制的。尊重个人自由的传统易于产生民主共和的政权,而强调集体主义的传统则易于产生集权国家。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极端的民族主义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然而,极端民族主义的产生,却有其深厚的社会和历史根源。因为从现代化的角度看,民族主义与一个民族应对现代化的挑战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果一个民族十分容易地进入了现代化的“正常”轨道,那么,这样的国家或许会产生较为强烈的民族主义,但一般不太容易产生极端的民族主义。反之,如果一个民族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总是受挫,那么,不仅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就是其他的极端思潮,也会应运而生。我们应该领悟到的是,一个民族在危难之际,民族主义往往是其坚守一个民族根本的最后的精神领地。在这样的时候,民族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的界限是十分模糊的,两者之间很容易就会形成一股合力,并往往会超出这一民族本来的目标之外,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所以,一个民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民族主义是会很自然地产生的,如果在遇到危机的情况下产生的民族主义,更具有复杂的性质。它一方面可以为这个民族提供最后的精神避难所,另一方面也可能向极端的方向滑行,给这个民族继续前进带来麻烦。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其国内产生的民族主义,就具有这样十分鲜明的特点。
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无论从什么样的角度评估,俄罗斯的民族主义都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因为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不仅具有前面所提到的那些应急的性质,而且俄罗斯民族主义还具有很多自身独有的特点:俄罗斯是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世界第一大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历史上又是一个扩张性的国家,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在这样的扩张中往往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就使得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具有世界其他地方的民族主义都不具有的复杂性。换言之,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不仅对其自身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会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说,冷战结束后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是一个全世界都必须关注的问题。作为俄罗斯的近邻,中国与俄罗斯有着几千公里的边境线,有着十分密切的地缘政治方面的利益,所以,我们对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关注,显然应该超过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世界上有关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研究著述很多,但对于苏联解体后这一特殊时期的民族主义的研究著述似乎还不多见。因此,黎阳同志通过这本专著,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努力就十分值得关注了。
黎阳同志认为,俄罗斯这一阶段的民族主义具有十分独特的性质,它既是俄罗斯传统民族主义的一种复兴,也带有某种“应急”的性质。所以,这样的民族主义产生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时效性。然而,在这样的形势下,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也带有一些极端的性质,并由此产生了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团体。这样一种局面给俄罗斯政府也带来了麻烦。作为缺乏新的意识形态的俄罗斯政府,十分需要利用这种民族主义作为凝聚民心的动力,但也不能让其不受控制地发展,影响俄罗斯现代化目标的达成。从总的情况看,普京政府对俄罗斯民族主义是既要利用又要控制,希望这种民族主义的活力能够为恢复俄罗斯的强国目标服务,但也不至于给自己添乱。应该说,普京政府的措施基本上是成功的,他通过各种法制手段,控制了俄罗斯的极端民族主义,同时也号召人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因此,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的民族主义,具有一种特殊的时代性质,它既为俄罗斯摆脱困境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支撑,也滋生了种种极端的思潮。不过,当俄罗斯终于恢复元气后,极端性质的民族主义就会逐步地淡出历史舞台——因为俄罗斯的进一步发展已经不再需要这种思潮来为自己继续提供动力。这些看法无疑具有相当的见地。
除开思维的敏锐外,作者深厚的外语功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具有很大的优势。黎阳同志是南京大学外院的本科生和保送研究生,精通俄语,熟悉英语,中文根基也很不错,这些条件都为其资料收集和专著的写作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与爱国主义有着密切联系的民族主义,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因为,当一个民族国家需要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的时候,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涵依然会对一个民族提供精神上的支撑。所以,我们既没有必要去倡导民族主义,也没有必要去扼杀正常状态的民族主义,我们需要警惕和反对的,只是种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及在这些思潮影响下产生的组织。
当前,我们依然生活在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组成的国际社会中,民族主义的时代还未过去,关注他国对民族主义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对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从这个角度看,黎阳同志的这本书,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我衷心地祝贺它出版。
2006年9月10日于南京阳光广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