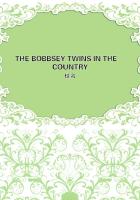半夜,女人守侯在浪三的床边。ICU里死一样的沉寂,各种监控仪闪着灯在“嗡嗡”地叫着,值夜班的护士走进房间寻视着各个病人。
“你可以到外面椅子上躺会儿,他现在挺正常的,没多大事。”护士对女人说。
“我不困。”女人说。
“护士,”浪三叫了一声,“我疼得厉害,浑身都疼,能不能给我开点止疼的药?”浪三有气无力地说着。
“止疼药不能随便吃,再吃就上隐了。”
“你就给我开点吧,不然我受不了了,又不是毒品,止疼药还能上隐?”
“跟毒品差不多,吃完了你该兴奋了,睡不着觉了。”
“求你就给我一粒,我吃完就睡。”浪三哀求道。
“护士,就给他开一粒吧,他不疼了,我也能去休息了。”
“好吧,我找医生问问。”护士说完走了。
浪三和女人对视着,双方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你怎么样?能坚持吗?”女人问。
“没问题,我感觉好多了,身上也有力气了,没有问题,”浪三说着伸出手使劲握了握女人的手,“怎么样,还挺有劲的吧。”
女人没有说话,她双眉紧锁,看着浪三的眼睛发呆。
护士回来了,手里托着一个小药盒走到浪三的床前,“医生同意了,只给了一小片,你吃完赶紧睡吧。”
女人接地药盒说:“谢谢,我来吧。”
此时,躺在里面的一个病人突然呻吟起来,护士赶紧跑过去:“怎么了?怎么了?”
病人一个劲地干咳,像要把肺都给撕裂了一样。护士急忙采取应对措施,慢慢安抚了病人。
这边,浪三迅速拔掉身上的所有管子,从床下拉出一个手提包,一瘸一拐地朝大门去。而女人脱掉外衣,里面露了病号服,学着浪三的样子躺在了病床上,她把被盖住了头。
浪三跑了,他咬紧牙关走出了急诊室,他拐进一个昏暗的卫生间里,从手提包里拿出便装换好。当他站在卫生间的镜子前的时候,他再也认不出自己了。浪三哭了,他基本上已经变形了,像一个从坟墓里跑出来的怪物,他边哭边用冷水把自己的头发捋整齐,又把脸洗了好几遍。他努力睁大眼睛,但畏缩的肌肉已经无法支撑日渐衰老的面皮,他只有拖着身上毫无生命力的一层皮,迈步走出了卫生间。
这是一个死者最后的挣扎,除了一颗心以外,身体上的什么部位都不是他自己的,都难以让他控制,他的双手不加选择地扶住身边的任何东西,有几次还扶住了过往的病人或者家属。他每次看到穿有白大褂的走过来时,他都直挺挺地靠墙站好,生怕引起他们的怀疑。
几次努力之后,浪三终于走出了医院的大门。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用尽力气向一辆依靠在医院大门边的出租车挥了挥手。
车来了,他拉开车门扑进了车里,把司机吓了一跳。
“你没事吧,小心点。”
“没事,不好意思,绊了一下。”
“您去哪?”
“回家。”
“您家在哪?”
“太平街,天地缘小区。”
车启动了,浪三松了一口气,他像一位逃出监狱的犯人,他好奇地看着街景,变化的街灯和匆匆而过的汽车,让他的眼睛有点儿不够使。连风都有人情味,吹散了他身上的来苏水味,他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尽情享受午夜的时光。
浪三回家了,他发觉这个家里充满了心酸。为了这个家,为了能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他和他的父母,还有兄弟姐妹,还有女人,还有与房子有关的所有的人,都撕破了脸上的一层皮,割掉了身上的一块肉。这就是生活,为了房子的生活。如今,他有了一套不大的房子,但他也将与房子阴阳两界。可悲可叹!浪三在屋里走了一遭,伸手摸着房子的每一个角落,他知道这是自己最后一次与这套房子亲密接触。他死后,这套房子不知属于谁?他选择最后时刻与房子告别,这也是出于无奈,他多想在自己离开人世的时候能和最亲的人在一起,但这已经没有了可能,只有这套房子在陪着他走完人生的最后几步。
离早上九点还有几个小时间,他挪到卧室的大床上,他想应该洗洗澡,换一身干净漂亮的衣服。洗澡也需要勇气,因为他很可能摊在卫生间里永远站不起来。
天亮了,浪三活过来了。他再一次洗漱完毕,把自己最好的行套穿戴好,皮鞋领带一样不差,手机、钥匙、钱包一样不能少。他特意把昨晚骗来的小药盒放在外衣口袋里,以防不时之需。女人原本想给他借一个轮椅或一副拐,但被浪三拒绝了,他不想狼狈地去离婚和结婚,他要堂堂正正地走进民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