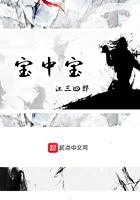王振听朱祁镇一问,便傻了眼,他一个文官出身的太监又有何迎敌之策,心下不断盘算如何应答。原来此次出征乃是王振一手操办,初时朱祁镇问他出征有几成胜算之时,王振与其道以十敌一自有九成胜算,若皇上肯御驾亲征,军心大盛,当是必胜无疑。王振自朱祁镇为皇太子时便伺候在身边,是以朱祁镇十分信任王振,对他的话也是不疑有他,加之他年少气盛,也没问王振有何迎敌之策,便要御驾亲征。王振初时只道这行军打仗,便是敌军一字排开,我军一字排开,大打出手便罢了,是以自觉以二十万大军打区区两万人马还不是易如反掌。但方才入大同府前,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刚刚将此前几日明军与瓦剌军交战大败之事告知王振,又添油加醋一番,说的瓦剌兵士个个刀枪不入,力能扛鼎,如天神下凡一般,别说十个明军将士,便是一百个也敌将不过,又对他说瓦剌军虽然打了几次胜仗,这几日却毫无动静,想是知皇帝携重兵御驾亲征不可力敌,使得诱敌深入之计。这一说当真吓得王振魂不附体,他本想趁此次出征名垂千古,却不想以身殉国,就算没以身殉国,若是那皇上少了一根汗毛,自己也决计活不了了。此刻正在思量如何劝得朱祁镇班师回朝,不想朱祁镇有此一问,便愣在当场。
朱祁镇见王振不说话,便道:“王公公有何良策。”其实朱祁镇对战争的理解与王振当真不相上下,但他欲言班师回朝,却又因御驾亲征乃自己力排众议之举,常言道君无戏言,怎能朝令夕改,是以无法直说,便盼借问策之事引得群臣争论,再求班师之事,自己便顺水推舟成事,岂不妙哉。
王振终是老奸巨猾,沉吟一会,“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声泪聚下,道:“老奴有罪,请皇上责罚。”说着不住磕头。
堂上众人皆暗道,这王振又耍什么花招,都以为是皇上问策,这王振答不上来,是以先发制人用的苦肉计。王振独揽朝政,素与朝臣不睦,众人见他如此狼狈,都暗自好笑。
朱祁镇道:“王公公何出此言。”
王振哭着道:“皇上有所不知,这瓦剌军闻听皇上御驾亲征早就吓跑回漠北了。”
王振闻听明军大败之事后,便吩咐下去此军情不得传出,而此刻堂上之人又都是随朱祁镇从京城而来,除到大同便来了此处议事,更无暇查探军情。想来王振胆子再大也不敢以当地军情欺瞒圣上,但“听闻皇上御驾亲征便吓回漠北”之言自是不信,只道瓦剌人见二十万大军来征,自行撤退了,再者这游击之技本就是游牧民族常用之法,是以不疑有他。
朱祁镇听后一喜,这瓦剌军撤退了仗自然不用打了,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班师回朝了,当下却不露喜色,道:“那当真好得很,王公公又何罪之有,快请起。”
王振听后也不起身,依旧跪在地下,道:“老奴得此消息,本想飞马报于皇上,好让皇上高兴高兴,然老奴一想皇上宅心仁厚,不忍将士们多受离乡之苦,必定即下令可班师回朝。可皇上连日行军,必是辛劳非常,老奴担心皇上龙体不安,想让皇上到大同府歇息两日在回朝,是以想先瞒下不报。但此刻看见皇上龙行虎步,威严更胜,心中便什么也不敢对皇上欺瞒。”说着又哭了起来,连磕几个响头,道:“请皇上治老奴隐瞒军情之罪。”
众人一听王振此言,都在心里暗骂:这狗太监,当真无耻之极。
朱祁镇因王振自小照顾周到,此刻也不作他想,以为王振当真担心他的身体,道:“王公公一片忠心,朕感动的很,罪责之言王公公不可再言,快起来吧。”王振闻言谢恩起身,恭立在一旁。朱祁镇见他起身,对众人道:“此次御驾亲征不战而屈人之兵实非朕之功,乃太祖、成祖及先皇庇佑我大明,不使大明勇士们身赴险境,体恤之情甚重,朕自当承先祖之志,念将士们离乡之苦,本该当即班师。却又不愿负王公公一番美意,今日大军便在大同府休整,明日一早班师回朝。”
众人皆称:“皇上圣明。”
王振道:“老奴还有一事禀奏。”
朱祁镇道:“王公公请讲。”
王振道:“皇上此次亲征,来时路上百姓见之皆如沐天恩,无不额手称庆。老奴斗胆请旨,班师时不走来时之路,皇上可广播皇恩,使更多百姓得睹天颜。”
朱祁镇只道是王振怕自己再重走来时之路,难免厌烦,是以想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改道行之,心下感动。便随了王振的意思。哪知这王振是想由紫荆关退兵,走自己的家乡蔚州回京,乃是衣锦还乡,显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威风。
众人也不知其意,只道王振仍是溜须拍马之言。
王振见群臣皆无异议,甚是高兴,便称早办班师之事,从堂上告退,又怕瓦剌军来攻城,回到自己的驻地便派了多名探子出城打探。自己又沉思若瓦剌军此刻攻城该如何禀报。想了一会毫无思绪,便趴在桌上睡着了。
王振恍惚间跃马持枪来到战场之上,自己身披银甲白袍,好不威风,一摸下巴竟然连胡子都生了出来,回头一看,自己身后乌压压的不知站了多少兵士,王振心中甚是得意。再回过头来,见前方尘土飞扬,杀出一队人马。
王振微微一笑,大喊一声“杀啊”,纵马疾驰,待到了阵中,他挺抢一刺便刺到一人胸口,那人晃了两下倒下马去。正在此时,两侧杀来两人,面目皆是模糊,一人使青龙偃月刀刀迎头劈下,一人使方天画戟照王振肋下搠来,王振丝毫不慌,侧身躲过方天画戟,单手持枪格住青龙偃月刀,另一只手不知从何处抽出一柄宝剑,向那使刀之人腰部一砍,那人登时被拦腰砍成两半,落于马下。这时那方天画戟又向王振背后搠来,王振也不回头枪柄在背后一晃,挡开方天画戟,拍马便走,手中的剑却不知哪去了,王振也不多想,听敌将在后面追的紧,侧过身子,手握长枪末端,枪由背后送出直刺敌将咽喉,那人紧追之下不知王振使出一招“回马枪”,猝不及防,咽喉被刺中,跌落马下,咽喉处却无鲜血流出。
原来这王振平时最爱读的书便是《三国演义》,最敬仰书中的常山赵子龙。常言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王振此刻在梦中竟成了常山赵子龙。手提银枪跨白马,血染白袍握青釭。又梦到自己不出三合连斩三将,当真是喜不自胜。
正当他欢喜之时,背后却传来一阵喊声,初时细不可闻,后来声音便越来越大,王振只听有人叫:王公公、王公公。闻此声甚近,心中一阵厌烦,暗道我乃常山赵子龙,叫什么劳什子王公公,便挥手一打。听得此人“啊的”一声,却将王振惊醒,慌忙站起来道:“谁,谁。”
王振微微定神,看到平时自己身边的一个小太监喜宁倒在地上,知是他扰了自己清梦,恼怒道:“你这臭小子,活得腻歪了?”
喜宁一听吓得魂不附体,赶紧爬到王振脚下道:“王公公、王公公饶命啊,饶命啊。”说着鼻涕一把泪一把哭了起来。
王振思忖,这小子平素就是有一万个胆子也不敢叫我,定是有要事,当下缓和道:“何事叫我,若说不出来,小心你的狗命。”
喜宁连磕三个响头,道:“方才公公派出去的探子回来禀报,不见瓦剌军踪迹。奴才怕延误了军情,才冒死叫醒公公,请公公饶命啊。”
王振闻听此言当真是欣喜若狂,笑道:“你这个臭奴才,却还有点用,你带几个人去皇上身边伺候吧。”随即从桌上拿了个令牌扔在地上,喜宁赶紧拾将起来,如获至宝。
喜宁初时以为自己叫醒了王振,当性命不保,此刻却有封赏。想来全赖着瓦剌军不见行踪,这瓦剌当真厉害,连权倾朝野的王公公都怕的不行,自己若能在瓦剌当差,那才真是威风,又转念一想,此时去了皇上身边伺候,若引得皇上高兴,混个左右少监当当也足以光宗耀祖了。喜道:“谢王公公大恩大德,谢王公公大恩大德。”
王振一挥手,示意让他退下。喜宁拿着王振的令牌,点了几个平时与自己交好的内监宫女退出王振的驻地,到了代王府,拿出令牌对门口的锦衣卫言道自己奉了王公公的命令,伺候皇上起居,锦衣卫各个对王公公怕的要命,见了王公公的令牌,便毕恭毕敬的将喜宁请了进去,喜宁见平时趾高气扬的锦衣卫都对自己如此,更是高兴非常。
喜宁一路小跑来到承运殿外,与殿外侍卫说清来意,侍卫进去进殿通报后出来对喜宁道:“此刻皇上正与那代王爷说话,你进去后可小心伺候。”
喜宁道:“那是,那是,承这位大哥提点。”
言罢喜宁叫一众太监宫女在门外等候,自己躬身入殿,见朱祁镇正坐在大殿中央,下首做着一位身着华服的中年男子,想是那代王爷朱仕壥,跪下行礼道:“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王爷千岁千岁千千岁。”
朱祁镇道:“起来吧。”
喜宁道:“谢皇上。”起身恭立在一侧。
那代王朱仕廛道:“皇上此次亲征何以身边没有人伺候,却是到了大同府才来人伺候起居。”
朱祁镇道笑道:“朕这次出征,本盼着能驰骋疆场,临阵杀敌,创一番大功绩,若事实需人照料又与在宫中何异。”
朱仕廛道“皇上有此番大志,当真是万民之福啊。”心中却暗想,这瓦剌军凶残成性,多次来我大同府侵扰,每次过后都是一片狼藉,这小皇帝在这胡吹大气,若是见了瓦剌军免不了吓得屁滚尿流。
朱祁镇道:“朕久居深宫,有时却对皇叔羡慕的紧啊。”
朱仕廛闻听此言当真吓得腿软脚软,想自己封于此地,虽无兵权,但毕竟处于边塞,难道这小皇帝疑心我与瓦剌人勾结,或是起兵谋反。是故以此试探,若我说此地甚好,那不是说做皇帝还不如我这藩王?不行,不行。若是说此地不好,更是引他生疑。当下道:“皇上何出此言。”
朱祁镇心地纯良,说此话并无他意,那是当真羡慕这代王无拘无束的生活,但他又哪知代王封于边疆,行事处处怕皇帝对自己怀疑,何况藩王之乱自太祖死后便屡见不鲜,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代王虽然并无异心,却天天活得谨小慎微,生怕自己被皇帝怀疑有谋逆之心。是以此次知朱祁镇亲征大同,需居于代王府,便将家里能收的珍玩器物都收了起来,连奴才下人也遣走了不少,更别说那块冠绝华夏的九龙壁,也被他命人用大布罩了起来。朱祁镇见代王府虽大,却如此简朴,心下甚喜,对他这位皇叔也是很有好感。此刻更不知代王心里打鼓,便笑着道:“宫中虽好,却不如皇叔这般自由自在啊。”
朱仕廛见他面无异色,心下稍宽,想道:那你倒是和我换换啊。嘴上却道:“微臣身居要地,时时不敢忘记自己职责,定然替皇上好好守住大同府。”
朱祁镇笑道:“闻皇叔此言,朕心甚慰。”朱祁镇平素居于宫内,事事有人侍奉,虽常常习武,但毕竟娇生惯养,这几日一直马上行军,早有倦意。便对朱仕廛道:“烦请皇叔吩咐下去,安排寝宫,朕有些累了。”
朱仕廛起身鞠躬道:“皇上今日便寝于长寿宫,微臣已安排妥当。”
那长寿宫位于承运殿北面,乃是代王府正宫,朱祁镇一行过崇信门、存心殿,朱祁镇见代王府随不及紫禁城一般气派恢宏,但也不遑多让,心下生疑,但也不好直问朱仕廛,心想,待明日班师之时,便问问英国公,他必定知道。
不消一炷香的功夫,众人到了长寿宫门口,朱祁镇对朱仕廛道:“这里有奴才们伺候着就行了,皇叔回去歇息吧,晚膳皇叔便与朕同在着长寿宫用吧。”
朱仕廛谢了恩,便躬身退去。
朱仕廛走后,朱祁镇便入了长春宫小憩,直到酉时才转醒,吩咐喜宁传代王到长春宫一起用膳。
过了一会朱仕廛便随着喜宁来到长春宫,见厅堂之上除朱祁镇坐于主坐之上,下分有四座,右首座坐了一位老人乃是英国公张辅。左首坐虚席定是为他所备,右次坐之人虬髯满面,状貌甚为,乃是成国公朱勇。左次坐那人却红袍散发,邋遢异常,他不知是何人,但想来能与英国公,成国公二人同席,必也是不凡之人。当下先向朱祁镇行礼。
朱祁镇道:“皇叔快免礼,我与你引荐,这位是英国公,这位是成国公。”
朱仕廛与两人分别寒暄客套一番,便又走向左边。
朱祁镇道:“这位是朕的老师,赵逸赵师傅,赵师傅武功甚高,行走江湖是定也十分有名,皇叔不知听说过没有。”
这大同府乃是边陲重镇,有些江湖上的亡命之徒犯了大罪亦或惹了大仇家便逃往大同,朱仕廛年少时也好交游,也识得一些江湖上的朋友,听过一些江湖之事,但于赵逸这个名字却想不起来。只拱手道:“久仰久仰。”然后落座。
朱祁镇见朱仕廛落座,便对喜宁道:“上膳吧。”
不一会菜品就由内监端上来,分到五张桌上。
朱祁镇见菜品上齐,独缺好酒,他虽不喜多饮,但向来向往“惟有饮者留其名”的气度,是以宫中晚膳时都会饮上几杯。这几日亲征在外,军中素来不得饮酒,本身他贵为天子,不必如此,但他决意与军士同心同德,是以也不饮酒,此刻不在军中,是以也不必遵守。当下对朱仕廛笑道:“皇叔,朕此次亲征,却没带酒,不知这大同府有何好酒可为你我五人助兴。”
朱仕廛道:“微臣平素不好饮酒,是以府上只藏了些低劣的汾酒,不敢在皇上面前献丑。”
众人皆想,大同府与汾阳县同处山西,以代王之贵,那山西布政使还不知送了多少上好的汾酒与他,他此言只怕自谦过了。
朱祁镇道:“不妨、不妨,还请皇叔拿几坛出来助兴吧。”
朱仕廛道:“遵旨。”转头对身后的小厮道:“去酒窖去几坛汾酒来,拿二十年以上的。”
朱祁镇道:“皇叔如此大方,哪能再劳烦皇叔府上。”又对喜宁道:“你跟着去,把酒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