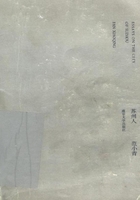被敌人杀死与被信任的人背叛,是截然不同的滋味。更何况,那也许不是背叛,而是深埋心底的阴谋。
“那些事情,是副院长告诉我的。”
即便师九没有直白的表述,另外两人还是明白的。副院长在学院工作了这么多年,多多少少会知道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在苏家这个神秘庞大的家族面前,那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但是,有些事情是带到地狱也不能透露的,他显然忽略了这一点。杀人灭口,最常见的桥段。
白色薄窗纱舞动,月亮瑟缩着躲进了云层,冬夜里,风如同刀子一般割着遇到的一切。沏了一杯浓香的咖啡,白玉回头和苏银月说话:“弟弟,看你穿的不多,会不会很冷?要不要我把窗子关上?诶……想不想喝杯咖啡?”
“我究竟哪里像男孩子?”她不认为白玉一直称呼自己为弟弟仅仅是因为那个舞台剧的角色设定。
“诶,哪里都像,又哪里都不像。我只是在幻想,幻想着你穿着男装行走于形形色色的人之间。”
目光在他身上流转,她细语:“我讨厌咖啡。”
“为什么?”
“苦。”
“诶诶?咖啡原来是苦的吗?我还以为,被同伴怀疑才叫苦呢!”
屏幕里,师九的眼神不带一丝温度。
尽管从未相信过他,也知道对方同样警惕着自己,但当这种猜忌化作实体赤裸裸的展现出来时,她还是抑制不住的心痛。
泪水盈润了眼睛,欲滴未滴,她咬着唇,低下头。
“还有十五分钟。”师九离开墙壁,晃晃悠悠地四处走动。“咱们继续。以蓝讲的学院怪谈有一个最大的漏洞,那就是她是如何得知的。一个在同学们心中如同诅咒一般的故事,很默契地被禁言,没有流传的可能。但结果是,她知道了这件事,并且利用它杀死了张友儿。能把尘封的秘密透露出来的,会是谁呢?”
“自然是……知道这个秘密的人。”琴夙似乎有些冷,她抱紧了自己的身体。
知道这个怪谈的人有很多,但他们都不会说出来,因为畏惧这个诅咒般的事情。毕竟,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更可怕。换个角度,能把怪谈讲出来的,一定是既了解又无所畏惧的人,也就是始作俑者。医院长久以来都是在苏家的掌控之下,要说他们不知情,完全无法服众。同时具备苏家和了解以蓝这两种身份的人,目前看来,只有苏银月。
“废弃医院的时空扭曲也很有意思,不过我坚信那是真的。说起来,可以控制时空,这种异能很厉害呀!”
“不对,师九,你的推测有缺陷。要想这一切都能顺利发展,幕后之人必须知道以蓝和张友儿的过往。银月是上个学期才转来本校的,之前根本不认识以蓝。”现在,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苏银月,钟离醒甚至不明白这样辩解的意义。只是,他不希望那个曾经对自己说“如果,我们都能活着,明年的这个时候,一起去郊游吧”的女孩儿是满腹阴谋的人。
然而,师九平静地看着他,并未回答。
三人心里都明白,这种小事,难不倒神秘而强大的苏家。
“诶,弟弟,他们好过分呦,竟然把张友儿的死都怪罪在你身上。明明一直在帮助他们,保护他们。”
“我不喜欢听拐弯抹角的话。”苏银月靠着椅背,下意识地想去抚摸左手腕上的绸带,却发现双手被缚,无法完成这个动作。
白玉转过头,原本小狐狸般的表情阴沉下来,“你不觉得委屈吗?自私、狡诈、阴险、冷漠,这才是人类的本质,他们高傲的自诩为神明,擅自主宰着世间的一切,无视我们的痛苦、挣扎、哀求。在他们眼中,只有人类才有生存的权利,而与人类如此相似的我们,却要面临被赶尽杀绝的境地。你一次次为他们受伤流血,他们根本不在乎,仅仅是因为,你是异类。”
“你不相信人类,对吗?”
“我不知道该如何说服自己,去相信他们。”
“那,你会信任我吗?”苏银月目光似水,带着不真实的温柔。见白玉黯然神伤,她继续说道:“你说了这么多,无非是因为我是异能者却立场模糊。身为异类却处处帮着人类,很可笑吧。费尽心思让我加入你们,你从哪里获得的自信?”
“苏银月。”这是白玉第一次如此正经的和她说话,“你的异能,真的只是治愈那么简单吗?”
突然,夜风呼啸,好似地狱敞开了大门,席卷着不知何时纷飞的雪花,缭乱了他和她的发。
风声太大,他来不及听到她的回答,只看见樱花般的薄唇轻动。
“你说什么?”
她微笑,身后似有翅膀展开。
躁动,戛然而止。
另一个屏幕上显示,有人闯入了。
白玉瞪大眼睛,“他们怎么会来?”
状似无意地扫过屏幕,苏银月暗暗松了口气:看来,赌赢了。
“苏银月,我可以信任你,是吗?”
凝视着他眼角逐渐明显的晶莹,她点了点头。
他笑了,如释重负。“我们快逃走。”这座房子没有设下任何防卫设施,一旦外人入侵,不多时便会被攻破。
解开她手上的绳子,白玉拉着她迅速撤离。苏银月能感受到,那从手心传来的温度。那样真实,和人类一样的生命。
匆忙中,她拽开了手腕上的绸带。
钟离信带着人仔细搜查着屋子的每一个角落,遗憾的是,他们一无所获。
“不可能呀……仪器上显示就是这里,怎么会一个人都没有呢?”钟离信有些奇怪。难道,上当了?
此时,下属来报,后门外有人走过的痕迹。他闻言果断下令,一半的人留下来继续搜查,另一半人循着痕迹去追。
跑着跑着,苏银月发现有些不对劲儿。白玉越来越慢,甚至与走步速度相差无几。
“白玉?”她冲上前,扶住那即将跌倒的身体。
他抬起头,对上她的眼眸,勉强一笑:“弟弟,终究还是我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