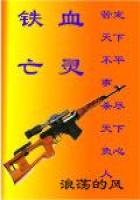时隔二十一天,流萤还是因为一些很复杂的原因同她的心理医生约了时间,后果是依旧身心俱疲。
在此之前,她有些不好的预感。她觉得今天,要发生什么,可是这种念头一闪而过,想抓也抓不住。
今天的天气不错,从医生那里出来,要走十分钟的路程才能到公交站台。流萤抬头,深吸了一口气,在久违的蓝天白云下,就算带着口罩,也知道这新鲜的还带着冷意的空气不带雾霾的味道。
她抬手,取下耳机,挂在脖子上。耳机和大领子相互挤压,叫流萤很不舒服。眉头一蹙,有些不耐烦的将耳机的线头从手机上拽下来,又摘了耳机,团吧团吧就随意的塞进了背包。
她抬头望天,风抚过,吹起几缕散落的发丝,轻叹了口气。复又低头,带上帽子,将双手揣进外套两侧的口袋,抬脚向着远方的站牌走去。
虽无行色匆匆,走的却无慢下来的趋势。
独自一人,在宽阔的马路上,顺着在冬天仍旧绿油油的灌木行走,过往车辆发出的声音嘈杂,也越发显得背影孤单。
她有时候会想休息,然后长眠不醒。不去想周遭一切的一切。
巨大的兜帽和口罩将整张脸遮住,低着头,连眼睛都瞧不到。哪怕在快过年的时日里,这种将自己藏的严严实实的扮相也还是稀奇。惹得周围人多瞧了几眼。
惹得流萤全身紧绷,僵硬的缩在座位上。最后只好又翻出耳机用音乐把自己和世界隔绝。
她总觉得她们在笑话自己。
带了耳机觉得听各种歌远离了世界徒留一人太孤单。
摘了耳机觉得周遭的一切满是恶意徒留一人太可怖。
恐惧感让她缩在车厢最角落,头倚靠这车窗,随着行驶磕磕碰碰。
在这之前的一举一动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唯独到了舅舅家之后和舅舅的对话记忆模糊。流萤只知道自己带了耳机不停的放着可惜没如果来逃避现实。她只知道她不愿意再继续舅舅未来的话题。
呵,她还能怎样,如今,她还有什么路可走。舅舅打电话给他的朋友。问他如果孩子要去他在北京的饭店打工如何如何。
她的眼泪像雨,最开始只有两三滴,然后越来越大,最后倾盆。
时间再次翻过一夜,她觉得昨晚的记忆特别模糊,好像做出种种行为的不是她一样。
她好像冲出了舅舅的家。然后一口气跑到了顶楼天台。爬上了围墙。
也许流萤唯一记得的就是从十八层的地方往下看夜景的心醉,和刺骨寒风刮在身上的生疼。直到她被随后赶到的舅妈拽下来。
疼。
身体的神经末端将痛感传输到大脑,只有这一个字徘徊不去。
她爬起来,试图甩开舅妈离开天台。
她不知道要去哪,只是想要离开。那一刻,她什么都忘了。只有离开让她渴望。
她的声音那样尖锐:“松手!”
“松手!松开!”
“我让你松开你听不到吗!”
眼睛,瞪得那样大,乌黑的眼睛在黑夜里好像也闪着光亮,让人根本无法忽视。她脸上尤是泪水涟涟,面部表情却狰狞无比。
很久之后,舅妈对流萤的妹妹小羽说,她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眼睛,疯狂,偏执,还有浓浓怨恨。那样的顾轻罗,她第一次见,也许,永远都不会忘。
摇摇欲坠的顾妈妈在刚才就已经上了天台。
妈妈也哭,她说,流萤,我们回家吧,回家,好不好。
流萤不听,她的尖啸在黑夜里扩散。
后来,发生了什么,流萤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
她说她回家,让舅妈放手。
舅妈放了。然后她跟她们下了楼。在除了楼道的那一刹那开始奔跑。舅妈却紧追不舍。流萤从不知道舅妈竟然有这样好的体力。
她被堵的无处可逃,是了,她体育一向不好。
后来,她晕倒了。妈妈急得心口痛。舅妈给舅舅打电话,舅舅出门,小羽听到,也急得匆匆跑进电梯。连外套都没有来得及披上。
她觉得自己好混乱,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有人和她说话,就在她耳边,她甚至无暇顾及别的声音。
有人说,虚伪!她们明明就巴不得你跳下去!
有人说,她们都在同情你,可怜你,还在背地里笑话你。
有人说,你这么蠢怎么还不去死。
有人说,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
七嘴八舌。可是流萤不敢说什么。她觉得她们说的对。
她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回的家。
她平躺在床上。思绪却不知道飘去了哪里。
又是未眠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