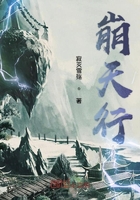柳随风割脉喂血,都是伏在黑龙背上做的,看台上绝大多数人倒是没能看见,也意料不到,只见柳都督身子压得极低,黑马一边飙血,一边越跑越快。
在他们眼里都觉得很可惜,柳都督座下黑马,要是没受如此重的伤,未必会输。
还有个三十多岁的中年武官,满脸不屑,议论柳随风狂妄自大,丢人败兴,简直不通骑术,害了坐骑不说,还凭白让西梁国丢了个大人。
麦铁柱狠狠瞪了那人一眼,看着面熟,似乎是哪个将军手下。
又过了几圈,大黑马逐渐赶上,阅兵台上气氛也热烈起来,没想到好景不长,眼尖的已然发现黑马伤口再次崩裂,片刻之后,只要不瞎,就能发现赛场上留下了长长一圈血渍。
而这时黑龙依旧在狂奔,甚至更快了几分。
“陛下,臣去下令,让柳都督停下吧,那匹马神骏绝不在雪玉马之下,甚至更有过之,折在在这意气之争中实在没有必要。”
大宗伯忍了忍,还是走到萧琮耳边小声请示道。
萧琮不置可否,只是说:“且看看再说,柳家小子今日实在有太多出乎朕意料之事,朕有种感觉,他说不定能给西梁带来惊喜。”
“柳都督这般,是要活活累死那马啊,这小子,心够狠的。”大宗伯在一旁不住暗叹,又想到自己年轻时候,有曾有过心爱良驹伴随纵横的光景,不由的唏嘘起来。
片刻间,八圈已毕,白马领先十丈!
赛场上,已经黑龙和柳随风的鲜血混在一处,留下一道暗红色的痕迹。
人间比斗之外,马心也有一场荡漾。
今日赛场之上,最得意的,不是携带三宝而来,被奉为上宾的大隋双绝尉迟瑶姬,也不是以算神料鬼技惊四座,将破野头一剑洞穿的萧长剑,更不会是西梁帝萧琮,大宗伯等人,甚至不是新官上任便在皇帝面前立下功劳,百官面前扬名的柳随风,而是那匹四蹄如轮,奔似浮云的雪玉白马。
这一人一马,无论到哪里,都是焦点。
无论是俊杰们的热情巴结,还是同类间的争锋相对,这本就是那些靓妞靓马们早已经习惯的日常生活,前者不会让她们感到厌烦,后者也不会真正伤了那颗心。
真正让她们难以接受的,是漠视,是一种骨子里散发出的不在意,尤其当这种漠视和不在意,是来自于她们欣赏的英雄时候,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如同乔峰之于马夫人。
我貌似天仙,世人见我惊为天人,你却在我身边擦肩而过,眼中不曾有我倩影,耳中未听见我软语,心地更不曾哪怕留我一方立足之地。
居然还不如你那群叫花子兄弟,不如那两罐劣酒,不如那栏难以入口的草料!
从初见之时,雪玉马便被那个高出自己许多的黑大个子吓了一跳,再接近些,黑大个身上那股野性不羁的气味让她颇感好奇。
无论是女人还是马,好奇心都是让她们深陷不可自拔的第一步。
一道蜿蜒开去的血迹映入雪玉马的眼里,她才猛然想起,那家伙身上的那些伤口,同为马类,那些伤有多重,该有多疼,她再清楚不过了。
于是乎,赛场上陡然间出现了做梦也想不到的一幕:眼看大黑马离白马不过几丈距离的时候,白马居然放低了速度,原地转了个弯,跑到了黑马身后半个马身处,马头不住的往黑马伤口上蹭。
尉迟瑶姬简直难以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整个人呆呆的坐在雪玉马背上,樱桃小嘴微微张开,满脸不可思议,手中那条从早到晚都把玩不停的马鞭悄然滑落在地。
柳随风倒是认出来这匹白马了,没想到它居然抛下了即将到手的胜利,掉头回来关心黑龙伤势了。
场上的两位主人,都被雪玉马突如其来的异常举动弄的不知所措,柳随风倒还好,终究是两世为人,甚至连穿越也经历过,抗意外能力总是要强过常人不少,他收回了手,颇有意趣的看着白马,眼里除了玩味,还带着几分欣赏之色。
黑龙自己莫名其妙。
白马也随着放慢了脚步,静静的跟在黑龙身后,偶尔偏着脑袋,在黑龙那些卷着淡红色肌肉的伤口上摩挲着,两只大眼睛水汪汪一片,满是心疼。
尉迟瑶姬也有两只大眼睛,勾魂夺魄的大眼睛,不过此时此刻,却是无神呆滞。
感受到身后白马的气息,黑龙猛的想起来了,这白马不就是哪天套近乎的家伙嘛。
那匹无聊的小母马,满身的奇怪味道,一副娇滴滴的样子。原来是她!
黑龙小跑了几步,放慢速度,然胡停下,回过头去,冷冷的看着雪玉,好像在说:你要赛便赛,赶紧跑,我伤的再重,也不占你这便宜。
咱丢不起那马。
雪玉马小心翼翼的跟在黑龙身后半个马身的位置,极为委屈的迈着小碎步,跟在黑龙身后,亦步亦趋,不落后太多,也不敢超过半分。
尉迟瑶姬再傻,也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感情自己的这匹被视为珍宝,高傲异常,从不对其他马加以颜色的雪玉,竟是对这大黑马芳心暗许。
不,这已经不是暗许,而是在大庭广众下赤裸裸的倒贴了。
校场中,如战场,军令大过天,除非有停赛的令,或者胜负已分,否则出了再大的事,也要继续比试下去,不过眼前这幅摸样,是个人都能看出来,已经没有再赛的必要了。
看台上,萧琮摇头哈哈大笑,抚掌对大宗伯道:“你我活了这把年纪,可见过这种奇事?只听说有人热恋中冲昏了头脑,想不到马也如此,倒是新鲜。”
大宗伯一张老脸,肥肉嘟嘟的,甚是喜庆,瞅了瞅在看台上一边气歪了鼻子的尉迟家紫衣武士,小声对萧琮道:“柳都督这事做的漂亮,非但赢了,还不伤和气,让尉迟家无话可说。”
“这话说的,人家白马又不是看上了柳卿。”萧琮难得心情大好,和大宗伯开了个玩笑,又道:“罢了,就算个平手罢,让柳家那小子回来,好好的两匹宝马,一匹失血而死,另一匹在成了花痴,那他们还不得怪死朕。”
大宗伯连连点点头,朝发令官挥手示意停止比赛,边道:“正是正是,算个平手,不伤和气,甚好,甚好啊。”
大宗伯连连挥了几次手,呆在原地的发令官才反应过来,捡起早就吃惊的跌落在地的小旗,僵硬的重重挥动几下,示意比试结束。
“白马啊白马,俗话说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层纱,你年轻貌美,只要能豁的出去,早晚能遂了你的愿。”
柳随风远远得令,转身端坐回马背,带着大黑马一转身便向阅兵台跑去,与雪玉马擦身而过之时,自言自语的说了句,似乎是在鼓励雪玉马继续骚扰黑龙,不要放弃。
不过柳随风坐在马上,高度正好与尉迟瑶姬相当,这话就等于在她耳边响起,像是说给她听的。
尉迟瑶姬原本就是通红一片的脸上,顿时又白了几分,恨恨的咬着嘴唇,在艳红的嘴唇上留下一排清晰的牙印。
大黑马见终于可以离了这腻人的母马,欢愉的叫了一声,撒开四蹄,滴溜溜跑的甚是得意。
跑到一半,马背上的柳随风终于憋不住,爆发出一阵大笑。
看台上,西梁众官,也跟着开怀大笑,看样子,这般扬眉吐气是多年未有的事了。
虽然未取胜,却胜似得胜多亦。
一片笑声中,雪玉马依依不舍的回眸一望,这次却不再跟上,而是低着头朝校场外方向走去,身影颇为落寞孤寂,尉迟瑶姬羞愧难当,任由白马带着走动,眉心的一点朱红几乎都要滴出血来。
眼看离着校场大门还有十余丈,尉迟瑶姬才恨恨的一发力,连人带马又化作一道白影,转眼就奔出校场,不知去向。
“西梁皇帝陛下,外臣告退!”
不等萧琮说话,剩下的紫衣武士已然站起,首领面无表情的朝萧琮行了个礼,鱼贯下了阅兵台,纷纷上马朝尉迟瑶姬走的方向追去。
“随他们去吧,我那表妹没吃过这么大的亏,丢了面子一个人在外面身边没个护卫也不行。”萧琮在御座之上摆摆手,制止了要拦住那群紫衣武士的大宗伯。
“小柳子,还不上来,在下面傻站着作甚!”萧琮心情大好,说话间也就随意了不少,朝下面唤道。
柳随风刚到阅兵台下,下了马,听皇帝叫自己,只是抬头示意知道了,并没有立刻上台回话,而是先吩咐了麦铁柱几句,赶紧带黑龙回去,找几个大夫瞧瞧,别落下什么病根子。
然后才提着外衫前襟,一路小跑上了阅兵台,到了萧琮身前一丈开外,单膝下跪,苦着脸道:“陛下,臣来了。”
“你这小子,好不稳重。”萧琮喝了口茶,没好气的把杯子朝按上一顿,又讥笑道:“有了些功劳,就自大起来,朕唤你还不立刻来,怎么,朕的旨意还比不上你家那匹心肠铁硬的无情马嘛?”
萧琮这么一说,周围众人都跟着笑起来,刚才那场面所有人看得真真切切,雪玉马分明是对黑马百般讨好,黑马却不屑一顾,虽说要是真比,到最后白马也难胜,不过这大黑马满身伤痕是有目共睹的,最后就算赢了,恐怕没个几个月将养也难复原如初。
但今日能到这里的,都是官场上百般历练出来的,哪里会为这些事而笑,这番笑,大多还是看清楚了萧琮的意思,配合一番罢了。
要知道,这位西梁皇帝即位十几年来,对臣下说话,大多中正平和,即未有过雷霆之怒,也未对谁表现出过多的亲近,从未今日这般有如此多的笑意,甚至假装生气的和臣子开起了玩笑。
“陛下可是错怪了臣了。”柳随风叫冤道:“臣听陛下唤,心里着实吓了一跳啊,这才迟迟不敢上来。”
“哦?朕哪里吓着你了,以至于你满脸苦相?”萧琮不解道。
一旁的大宗伯也接口道:“这道是怪了,柳都督年少有为,为国争光,陛下唤你自然是有赏,高兴还来不及,拉着脸怕什么?”
“大人有所不知,下官有两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