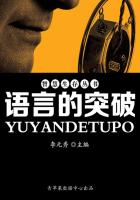远 子
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做过一段时间的婚庆兼职,工作内容很简单,主要就是布置和收拾婚礼现场。
不过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因为有钱人的婚礼是如此的复杂。我们需要去那些五星级酒店布置舞台,铺红地毯,往地毯上撒花瓣,装泡泡机(婚礼过程中不时按一下开关,它就能往外喷五颜六色的气泡),接插线板,往墙上贴喜字(一定不能贴歪了,因为不吉利),系椅背纱(必须系成蝴蝶结状),摆放新人的婚纱照,还要放好盖碗茶杯,假酒(一般是葡萄汁,新人用它去敬酒),抽烟用的火柴,签到用的签字笔等等。婚礼进行中,需要配合音响师傅开关灯,把结婚戒指送到新人手上,把手捧花递给新娘(她会背对观众把花抛出去)。
每次婚礼开始前,婚庆公司的场督都会给我们一人发一张长长的时间表,精确到分钟,我们根据时间表提前做好各项物品的准备。不过还是会有一些突发事件打乱这张时间表上的计划,比如有一次新郎打算送给新娘一个地球仪(婚礼过程中他转动地球仪,让闭上眼睛的新娘随手一指,指到哪里他们就去哪里度蜜月),眼看着婚礼就要开始了,地球仪找不到了,新郎大发雷霆,我们赶紧打车去新华书店买了一个地球仪。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头天晚上彩排结束后新郎自己把地球仪拿回去了。
婚礼的流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先做什么后做什么都严格按照时间表来执行。新郎新娘相互之间的表白基本就是“啊,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的爱人,是我的牵挂”;而主持人的笑点主要集中在“生娃”上,他让新郎把求婚的一幕在舞台上再重演一遍,他总是一再强调说北京有一个习俗,如果左膝跪地就生男孩,右膝跪地就生女孩,双膝跪地生双胞胎,双膝跪地抱大腿则生龙凤胎。主持人还喜欢说:“感谢大家稀稀拉拉的掌声!”宾客们听到这句话会很尴尬地笑,然后紧接着他会说,“让我们再次用掌声祝贺这对新人喜结连理!”大家又鼓起掌来,这回主持人会笑着说,“对嘛,掌声应该热烈一点。”就这么两招,居然每次都能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婚誓的时候,我一直期待着在新郎和新娘说完“我同意”之后,有一个人破门而入大喊一声:“我反对!”然后,像电影《毕业生》的结尾一样,那个人牵着新郎或新娘的手冲了出去。不过这个情节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我们的生活更像是没有最后一个自然段的欧·亨利的小说,几乎没有剧情。
中午他们吃饭的时候,我们站在旁边看着。我们只能吃喜糖,或者背着场督偷偷去吃一块婚礼蛋糕。等他们吃完饭后,我们就去收拾行当,还能顺手拿走搁在盘子里客人没抽的烟。
所以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抽“中华”。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对八〇后新人的婚礼,他们因为年纪小,没那么多扭捏作态。给新娘递手捧花时,她还偷偷问我:
“我是不是看上去很紧张啊?”我急忙对她说,没有没有,挺好的,加油!靠近了仔细一看,我发现她长得跟我的初恋女友有一点神似,尤其是眼睛,都清澈得可以看见自己的投影。当晚婚礼结束后,疲惫不堪的我走在北京深夜的街道上,竟看到天上挂满了星星,在空旷的星河下,我忍不住想起了她。我们虽然有彼此的手机号码,但是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
有一回我到早了,离约好的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便决定去周围转转,结果走到了潘家园旧货市场。我看到有人在摆地摊卖书,便去淘了几本书。出来时在门口遇到一个满头银发的老者,看上去极为眼熟,我在脑海里搜索好一会儿后终于想起来他就是诗人芒克。我犹豫着要不要跟他打声招呼,这时,眼见他抬脚准备要走了,我脱口而出:“芒克!”
他回头了,果然是他!
“您好!”我怯怯地喊了一声,还特意用了“您”。
“你好,”他有些诧异,“你认识我?”
“我读过您的诗,诗集的扉页上有您的照片。”我递给他一根中华烟。
“哈哈,是吗?你现在在做什么呢?”他说他不抽。
“刚毕业,还没有找到工作。”我也把烟收起来了。
“哦,你今天买书来了吧?”他看了看我手上提的书。
“嗯,是的。”我低头看着我提的书。
“我今天来这里见一个朋友,正准备走。”
“好的,再会!”他冲我挥了挥手。
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一个诗人。我抽着中华,怀着激动的心情走向婚庆公司。之后,我就跟着其他兼职一起钻进婚庆公司阴暗的储物间里去了,我们把婚礼上要用的道具一一装进面包车之后,把我们自己也装了进去。因为空间很小,还得避开交警的视线,我们只能把自己藏在红地毯和椅背纱之间,感觉像是在偷渡。
那一刻,我多么希望我真的是在偷渡。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日本文选自远子《十七个远方》,九州出版社二〇一四年一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