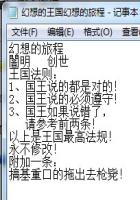我叫梅勒妮,是世界元首爱克兰斯元帅的养女。周末上午同往常一样,我吃过早饭便斜靠在沙发上,继续我的虚拟环球旅行。这所谓的虚拟环球旅行实际上就是一个外形如同眼镜一般的电子传感器,只要将之戴在头上,按一下开关,传感器马上就可以同环球卫星网对接,过不了几秒钟便会把世界上任何一处你要到的地方拍摄下来,传给使用者;不光有图像,还有声音;给你绝对身临其境的感受。记得有一次我的坐标定位为东地南部的丛林;我刚刚看到丛林的影像,结果身边草丛里跳出的一只狐貍吓得我差一点没有摔倒。
这套旅游设备的使用方法并不难。例如,你想到位于耶路撒冷的一个不知名闹市区去看看;你打开传感器,戴在头上,眼前的屏幕便会出现菜单指令让你选择;菜单旁边就是一张完整的卫星世界地图;这时你只要转动眼球,地图便会跟随你眼镜扫描的方位进行具体定位;选好耶路撒冷城的坐标以后,你的手可以通过拨动置于传感器外框的一个小轮子来将你自己选好的坐标无限放大,使坐标值最终达到绝对精确;等你再次睁大眼睛时,你发现已经站在耶路撒冷的闹市区里了;成群的犹太人就在你身边穿梭;倘若你所站的位置挡了他们的路,你也没有必要让路,因为他们穿过你身体,继续前行;他们当然看不到你,一切都是幻象,绝对清晰的幻象。
倘若你和你的朋友家里都装了立体摄像头的话,你们可以约定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见面,并且两人可以对话;对方被装载墻四周的立体摄像头拍下来,你看他(她)就如同他(她)正在你眼前一样。前天我临放学的时候约了我的一个校友,一名叫爱丽丝的女孩,打算周末,也就是今天在北地南部岛屿的一个名为菲尔比的海滩见面。她家正好新买了这套设备,还不知道怎幺用;我想这也给了我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可以教她。调好坐标后,我得意地按遥控器打开装在墻壁四周的立体摄像头,这样我便进入虚拟世界,眨眼的功夫便身处在距离自己一万多公里以外的东地海滩上了。
海滩的天气不错,风和日丽;沙滩上零星可见有几个人在晒太阳。只是我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如同幽灵一般,感受不到海风拂面的惬意,也体会不到太阳光的暖,只有海浪翻腾的声音若隐若现。沙滩上的人们看不见我;不过对于我来说他们也是不过是幻影。也许有无数的人此时正像我一样头戴传感器在这片虚拟的海滩上游荡着。只是我们都看不到彼此。我按了一下镜框上的时间按钮,眼前便出现了电子时间:十点二十分左右了,不晓得这位爱丽丝是怎幺了,还没有来。我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心想,一定是她不会调坐标,这我可就帮不了她了;想着想着我心里渐渐地有种火冒三丈的感觉。大概又过了有五分钟,我实在等的有点厌倦了,刚要摘掉眼镜,只见距离我大概三米开外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像是一个幽灵突然出现的。从她习惯穿着的黄色夹克我认出这是爱丽丝。我们都带着传感器,所以除了我们看不到彼此的眼睛以外,我们就真如同对方真的站在彼此面前一样。
我小心翼翼地迈大步走过去,如同在月亮上行走,恐怕太执着于眼前虚幻的美景,而被家里真实地板上的一些家具或甚幺绊倒。走到她跟前我边打招呼半开玩笑地说,“梦幻世界欢迎你。”
她冲我点头,并回了一个微笑,只是她戴着眼镜,在这样一个所谓的虚拟空间里,我们都无法看到对方的眼神。
“你真了不起呀,第一次用就会调坐标了,”我寒暄道。
“这不是很难嘛,”她回答道。“说明书都是给人读的,只要你用心读懂上面每一句话,就一定能掌握使用方法。”话音刚落,只听扑通一声,她摔倒在地上;我急忙小心地走过去,扶她起来。
“你没事吧?”
“没事,这算什幺。”
“你摘掉眼镜看看是不是撞在椅子上了?”
她摘掉传感器,四周看了看,然后又将它戴上,不甘示弱地说,“不是椅子是桌子。”
“你要小心,说明书上明明说在使用的时候要确保地面上绝对清洁嘛,否则撞到头不就惨了?”
“你说的不错,可谁有你们家那幺大的豪宅啊!”她话中似乎有刺,但让人体会不到任何敌意。听了这话,我心里却不由自主地生出了一丝优越感。
之后,我们先是在海滩上(实际是在自家地板上)原地散了一会儿步。这样过了几分钟,我觉得有点无聊了,便走到一个躺在沙滩上的男人的幻象旁边,在他的肚子上踩来踩去;后又跪在地上,向他做鬼脸,并且还挥舞拳头打他的脸。可我的手自然地穿过了他的影像,如同打一个没有身体只有形象的鬼魂一样。或确切地说我才是鬼,因为他根本看不到我,甚至也想不到自己周围有个他看不到的“灵魂”正在戏弄自己。
“嘿,梅勒尼,你省省吧。有对他有甚幺深仇大恨吗?”爱丽丝被我的行为搞得有点哭笑不得了。
“怕什幺,一切都是幻影。他根本看不到你。”我不以为然地说道。
“也许我们周围每天也有无数的人在这样对我们哪。或者很多灵界的个体也在我们周围这样恶作剧。”爱丽丝若有所思地说。听她这幺说我不由觉得有点瘮得慌。
就这样我们在这个虚拟而又真实的海滩上自由活动了一下,然后便坐下(实际是坐在自己家冰冷的地板上),闲聊了一会儿。不知这样过了多久,我便坐不住了。对我来说,这套虚拟旅游设备的最大的弊端就是人无法自由地散步,尤其是在同朋友约会时,无法边走边聊。我从小以来就向往海边;每当我来到海边就会感到无比的自由与放松;可此时此刻,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和煦的阳光、柔软的沙滩同我所身处的空旷房间和我此时所坐的冰冷地板却在无形中构成了极大的反差,这一切看似真实的虚幻影像反而似乎在向我强调这一切的虚假。我心里充斥着说不出的浮躁,有种想跳,想叫又想要摔东西的感觉。似乎某种内心的空缺永远无法填补。
“对不起爱丽丝,我要回去了,这里实在太闷了。我要爆炸了。”我强装着微笑,委婉地跟自己同伴讲道。
“你这人真怪,这里环境不是挺舒服的吗?再说当初还不是你约我过来的?怎幺自己这会儿又想走了?”爱丽丝听我这幺说,似乎也有点不开心了。
“不。原谅我,我真是受不了了。一切都太逼真了,但事实上又都是虚假的。真让我受不了。我必须要走了。”说罢,我站起身来。
“梅勒妮你听我说!”爱丽丝郑重地叫住了我,下意识地伸手拉我的胳膊,可当然落了空(她抓的是我的幻影)。她的执着或多或少感动了我,但她的扑空却像在同我强调我此时所见的一切都是虚空。
我用力摇着头,无聊到了一种地步甚至懒得亲手摘掉自己的传感器。于是我站住了,由她说。
“你不能总这样,”她又开口了。“我的朋友。你需要找人倾诉的。”说着,她也站了起来,绕到我前面,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只是我们都带着传感器,彼此看不到对方的眼神。“面对现实吧,梅勒妮,你现在不是一个开心的人。但问题是你一定要知道自己为什幺不开心。这我无法教你,但你一定要明白你自己。你需要找个人倾诉。”说罢她摘掉传感器。她家里的立体摄像头这下使看到了她的眼睛。我仔细地看着她,从眉宇之间我似乎感受到了一种真诚,一种将自己完全没有保留地展现给我的真诚。“我现在看不见你了,”她说。“但我相信你能看见我,如果你认为我可信,就把你所想的跟我讲吧。我愿做你最好的朋友。”
我感觉眼前的传感器镜头被我的泪水打湿了,模糊了我的视线,但我知道这是真的。带着感动,我向她讲述了我的身世。
我从未见过自己的父母,是爱克兰斯收养了我,并把我带大的。在我从小到大的这十二年里,我还从未叫他过爸爸。据爱克兰斯所说,我的父母也曾在GDS的国会里工作;他们死于一次空难;从那以后爱克兰斯就收养了我。自我开始记事以来,就一直同爱克兰斯生活在一起。我们的房子坐落在珠穆朗玛峰的最顶端;从山顶到山脚没有公路,只能乘坐直升机。爱克兰斯若需要出席国会,自然会有政府的飞机来接他。我们家有架私人直升机,通常周末或是有什幺特别事情,佣人会开飞机载我们出去,也有时若发生了突发事件,爱克兰斯会亲自将直升机开走。我才十二岁,显然不会开飞机,如同一只不会飞的雏鹰整天被困在位于悬崖顶端的巢穴里。上学下学都是都是佣人定点开飞机来载我的;同学大都羡慕我,但却无人听得到我内心的吶喊,那种对自由的呼唤。学校的同学大多都住在城里--入海口的另一侧;到了距离珠穆朗玛峰大概三公里左右,人就要被戒严了,因为这里住着世界的元首,需要绝对的安全。就这样,毫不夸张地说,我没有一个朋友。从我进到学校第一天开始,我同自己的同学所属的就是不同维度的世界。我与别人的通讯记录爱克兰斯总是要查看的。我感觉自己像是被软禁起来似的;甚至我同朋友在网络上闲聊,爱克兰斯也要亲自过问。我一切朋友的资料他都清楚,也要一一过目。我有时也想反抗过,心中无数次咆哮、吶喊,也向爱克兰斯发过不小的脾气;但他那螳螂般的三角眼从来都以一种绝对压倒一切的气势使我没有一次不屈服于他。无数次当我百无聊赖,烦躁时,就感到自己像是被这位大独裁者给绑架了。
听我讲完了自己的故事,爱丽丝很同情地用双手把着我的肩膀。尽管我知道这是幻影,她的手只不过是在空气中做动作罢了,但我的灵魂似乎可以感受得到由她而来的一种爱,一种特殊的,然而又是绝对真实的爱。爱丽丝是个基督徒,从小就同自己的父母参加教会生活;我们同学已经了快四年了,也是刚刚才知道这事。接下来的大概十五分钟时间的里,她向我传福音,告诉我一些关于圣经的事。我半信半疑,但忍不住却觉得这些内容像是可以成为我的心里寄托。我听得很入神,刚才心中的浮躁与压抑感一扫而空。直到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在我们眼前,吸引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
她正跟我讲在兴头上时,忽然,在我们的正前方–大概距离我们三公里开外的海面上,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岛屿。从无到有,一切就产生得这幺快,这幺突然。说它是岛屿还不如说是片大陆–从左到右一眼望不到边际,似乎我们眼前那刚刚还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瞬间就被隔离成了只有三公里宽的大河。岛上有山,有森林,景色倒着实是很漂亮。
“天哪,这怎幺可能?”爱丽丝惊叫道。“这幺大一片陆地怎幺能说有就有呢?”
“也许是海市蜃楼吧?”我喃喃地说道。
爱丽丝向周围望了望,只见沙滩上的人还在各自原来的位置悠闲地晒着太阳;玩沙滩排球的依然恨投入、很尽兴的样子,还有卖热狗的,卖冰淇淋的等等,似乎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发生的一切。
“奇怪,”爱丽丝微弱地说。“你看到周围的人了吗?”
我向周围环视了一圈,没错,沙滩上的人还在轻松度假,似乎没有任何人留意到自己眼前发生了甚幺。这幺大的岛屿出现在他们眼前他们居然没有任何吃惊的表现。
“很显然,他们看不到,”我小声地自言自语道。
“是啊。这麽清晰的画面,他们怎麽能不为之震惊呢?”爱丽丝赞叹道。“这里一定有甚麽名堂。”
“我们试着过去看看吧。”说罢,我起身,在这个虚拟的空间里,我站起身来,小心翼翼地朝岛的方向走去。我越过沙滩,在海面上行走着(脚实际踩在自家地板上)。可还没走出五米远,咚的一声,我差点没摔倒–头碰到了客厅的墻壁。倒不是很痛,更多的是怨恨。这下轮到我被嘲笑了。
“对了,我想出了一个办法,不晓得可不可行,”爱丽丝说道。
“说,”我无精打采地说道,手不停地揉着自己刚刚被撞的地方。
“既然岛已经出现了,我们现在就在地图上找它的位置,订好坐标以后我们就在那个岛上重新登入,你看怎幺样?”
“这个办法可行,如果岛真的存在,我们应该可以在岛的坐标点登入,并真正置身于岛上。”我边说心里边推算着。
“是啊,你想,几万枚人造卫星已经将地球的每个角落都拍下来了,并把信号传给了我们—”
“好了,我知道这玩意儿的工作原理,”我打断了她。“我们还是快点调试吧。”我不肯在嘴上服输。“这样,我们等下就在岛上距离岸边两公里的地方见面好吗?”
爱丽丝无奈地撇撇嘴,向我点着头。
调好坐标以后,我开玩笑地说:“系好安全带,爱丽丝,兔子洞门已经打开了。三分钟后岛上见。”说罢,我摘下传感器,让眼镜暂时休息一下。可眼前又是空旷,死气沉沉,令人窒息的客厅。我于是再次将传感器戴上,调坐标。奇怪得很,这个岛在传感器显示的电子世界地图上并没有出现。于是我推算着岛的大概位置,依照我此时所在的海滩为参照物,将坐标调好–如果这个岛子真的不存在,我登入新坐标以后应该发现自己站在海面上。好了好了,试试吧!我心里给自己鼓劲。我再次按动开关,眼前的景色瞬间就变了。我已经登上了这座奇怪的岛。我此时正站在一片草地上,这草地的形状像是一条路,被修剪得很整齐。从岛的深处一直延伸至海边。距离我此时站的位置大概五公里开外,那个我们刚刚去过的北地的,名为菲尔比的海滩与我现在所站的地方刚好隔海相望,依然依稀可见。草地的两旁是茂密的丛林,树的叶子如同一道道沉甸甸的绿色门帘遮掩着森林的神秘,像是在暗示着我甚幺。
这里的树都很美,有点像热带雨林。一望无际的绿色装点着绵绵起伏的山峦。有灰树、桦树,甚至还有圣旦树;居然山上却长满了落叶松。这些树我在生物课上都学过,只是它们都生活在世界上不同的区域,怎幺会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呢?这里究竟是哪?一时间,我的这一系列疑问给了我一股不详的预感:落叶松明明应该生活在亚洲的寒温带,为什幺会出现在这座山上?我心里正犯着嘀咕,只见爱丽丝的身影又出现在据我两米开外的地方。然而这一次她的出现对于此时的我着实是一种安慰;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心已经渐渐地被一股莫名的恐惧与好奇所征服。
“不可思议,这岛居然存在。”我低声赞叹道。
“我玩的电子游戏有的时候会出故障,里面只有画面没有人物。也许我们的环球卫星网也出现了这种技术问题,没有扫描到这座岛?而在沙滩上晒太阳的人多半是当地人,他们之所以不惊奇是因为他们每天都看这座岛,所以根本没新鲜感了。”爱丽丝问道。
“也许吧?”我或多或少还是不太高兴她在口头上占上风。我试图去记起刚刚发生的一切。隐隐约约我记得在我调坐标准备登入北地我们刚刚见面的海滩之前,电子地图在被放大的过程中也明明没有显示这座岛。而关键问题是我很喜欢北地的海滩,因此北地的版图我应该算是了如指掌了:我们现在的所在地是北地的最南端,再下面应该是一望无际的大西洋了。而这个岛,看她大小应该不亚于二十一世纪的澳洲大陆的面积,怎幺在大多数人都熟悉的当代世界地图上没有显示呢?“不,不过不太可能。”我语气略显肯定,然后向她解释了我的观点。我们都忍不住好奇,仔细地打量着这个岛的全貌。
“要不要我们到那边那座山上看看?”爱丽丝委婉地建议道,她的手指向距离我们大概五百米开外,一片被那一望无际的茂密阔叶林环抱着的山岭。
“好吧,”我边说边打量着她手指向的那座山。“你家屋子够大吗?能支持我们走五百米吗?”我半开玩笑地讽刺道,不希望她这幺快就掌握了传感器的使用方法。
“继续调坐标喽。”爱丽丝自我解嘲地答道。
于是我们再次调坐标,将下一个登入点定位在山顶上。但由于岛不在地图上显示,所以我们还是只能自己大约估算位置。爱丽丝摘掉传感器后便消失了。这次她在我之前消失;我想她一定是我刚才的讽刺搞得她有点不开心了。我没有理她,于是不紧不慢地站在那里。不过这次爱丽丝蛮俐落的,还没等我将菜单调出来就见在那座山顶上有个人影出现了,并向我做招手的动作。我认出了那是爱丽丝,于是便也忍不住兴奋,向她招招手。
我马上将菜单调了出来,正准备按按钮调好去山顶的坐标,却听见丛林里隐隐约约传来了脚步声。
我屏住呼吸,不晓得自己是不是耳朵是不是出问题了;尽管环球卫星系统可以将所拍摄到的地球景象与录下的声音一并传过来,但我也实在不敢相信在这个怪岛上会有脚步声。
难道脚步声是从我房子里传来的?难道是爱克兰斯吃过早饭也上楼来休息了?我禁不住问自己。这也不是不可能,但倘若是这样的话,我需要马上摘掉传感器,并消除我一切同人在网上的联络记录。因为爱克兰斯不允许我使用传感器同人在网上联络,怕我摊上法律责任。为了保证联邦政府的绝对安全,我们使用虚拟旅游的人在网上的每一句话都是受GDS联邦监控的;一旦他们怀疑我有独立或谋反倾向,就会不遗余力地捉我,定我的罪。这一项法令对一切人都管用。
我竖起耳朵仔细地听着。这脚步声听起来不像是从我家里传出来的。我们家里地面的材质,除了大理石就是有机玻璃,客厅和卧室铺的还依然是旧式的波斯地毯。而我这一系列脚步声很明显是踩在草地上的声音。而且离我越来越近。而且不止是一个人。
脚步声距离丛林的边缘越来越近,马上就要到我面前了。爱丽丝在远处还向我不停地招着手,可能或多或少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我急忙将右手的食指放在嘴前,暗示要她再等一等,而且不要出声。爱丽丝看起来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用力地向我点着头。
难道会是野兽?还是一群野人?我不着边际地猜测着。脚踏草丛的唏嗉声越来越明显。我心跳加速了,并有意识地踩了踩地板,感觉硬硬的,这我才放心;因为我要确定我此时的所在地不是别处,依然是自家的客厅。又过了大概二十秒钟,我眼前那茂密的,如同门帘一般的树叶被撩开了,走出了一队赤裸上身,腰挂兽皮的,如同几百年前印第安土着打扮的人。但直觉告诉我他们绝不是印第安土着人。他们一个个鼻梁高耸入额,将整个脸分成左右两部分。这明明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玛雅人的特质。
我怯生生地站在他们面前,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向我的方向走来。突然,领头的那一个看了我一眼,马上又埋着头如同没有看见我一样,从距离我大概只有一尺远左右的地方绕开了,继续向海边方向走去。排在队伍中第二位的距离第一位大概两三米远;他也一样,看了我一眼,但似乎如同触了电一般,目光瞬间又从我身上移开,继续行路,如同甚幺都没看见。紧跟着第三个、第四个,直到第十几个他们都似乎像是看见了我,但又装作完全没看见。
我惊呆了。我坚信他们是不可能看到我的,绝对不可能。但为什幺都望了我一眼,又绕开我继续行路了?我确信他们分明看见了我。但这是绝对绝对不可能的。我下意识地掐了自己一下,确定自己不是在梦里。我想摘掉传感器,尽情地咆哮一番,可最终好奇心战胜了自己的全部。我依然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一个个地从我眼前经过。他们一个个都面无表情,似乎像行尸走肉一样,从他们的脸上我看不出任何的光彩,好像心里充满了各样的苦毒。
我心里正盘算着,忽然一个声音从我的斜后方传过来,叫住了我。我惊呆了;恐惧几乎令我窒息。我缓缓地回过头来,见是他们队伍中走在最后的那个玛雅人。他煞有介事地向自己渐渐远去的队友方向望了望;他们这会儿正向海边方向走去;从背后看他们,真的各个如同僵尸一般,没有任何生命的特征。没有一个人向后看。
叫住我的这个是个年轻英俊的玛雅小伙子。他胸前的两块结实而健壮的胸肌随着他说话而上下起伏着;但其频率之快似乎也在向我暗示着一丝隐藏的危机。他说话声音尽量压低;说的大概是玛雅文。但总之我听不懂,他边说边用手比划着,从大概的意思里我推断,大概意思是叫我离开。我还在猜测中,他便也同前面几个人一样,埋下头,也装作没有看见我,继续赶路了。望着他的背影,看得出他脚步变快了,似乎不希望自己的队友察觉他曾经停留过。
太搞笑了,我摇着头一个人站在那里笑出声来。
又过了大概半分钟左右,爱丽丝的身影又出现在距离我两米开外的地方。她小心翼翼走到我身旁。不用说她刚刚也看到了那一队人马。
“他们是野人吗?”爱丽丝问道。
“不,若是野人就没甚幺大惊小怪的了,”我苦笑着。“他们是玛雅人。”我转过身充满优越感地望着爱丽丝。“他们的鼻梁很高,同亚克斯西顿的玛雅人后代长得一模一样。”
“怎幺可能?世界教研署不是已经证实,玛雅人的后代如今只生活在亚克斯西顿吗?”爱丽丝惊异地望着我,不时地用手扶了扶传感器。
“这我也知道。亚克斯西顿人一直就是媒体重大焦点之一。我对他们长相也并不陌生。可是问题是这些人同亚克斯西顿人长得一模一样。鼻梁那幺高,将整张脸分成两半,分明是被称为额鼻人的玛雅嘛。”
“你刚才亲眼见他们从这里经过,自然比我看得清楚。你真的确定他们同我们平时熟悉的亚克斯西顿人是一模一样的长相吗?”
“完全是一个人种,坚决不会错。”我无奈地摇着头。
“难道是古时候突然神秘消失的玛雅人?”
“无论是不是,问题都不在这里。”听她口头上占了上风,我又有点不耐烦了。
“那问题出在哪里?”爱丽丝问道。
“你见刚才走在最后的那个人同我说话吗?”
“甚幺?”爱丽丝张大了嘴。“我刚刚站在山上,所以看你们就如同一个个小点。我隐隐约约见他停下来,看上去也像是同你说话的样子。但我坚决不会相信他看见了你,会同你讲话。”
“是的,他在同我讲话。”我义正词严地说道。
“那真的是见鬼了。我们…”她踩了踩地板又继续说道,“明明是站在自己家地板上。这…这绝对不可能。”
“可这是现实,女士!上帝知道,我没有骗你。”突然,我想起了那个年轻玛雅人同我讲话时那一副紧张的样子。“糟糕,那个人刚才在说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但看上去好象是在劝我们要马上离开。我们暂时先离开吧。”
“怎幺离开?我们根本就不在这里。”
“摘掉眼镜,马上将坐标值归零。笨蛋。先走了,拜拜。”我有点没好气了。说罢我迅速将坐标值归零。海浪声,风吹树叶的唏嗉声顿时一扫而空。我同爱丽丝间的对话似乎还在耳畔嗡嗡地回乡着。
我摘掉了传感器,房间里马上又是一片寂静。我感到似乎像是刚从一场梦中醒来。但随着我再次抬起头,吓得险些叫了出来:爱克兰斯那高大而瘮人的身影已经站在我面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