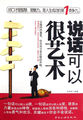笑嫣在君说的****下从自封的革命战友便成了端茶倒水还附带马萨吉功能的贴身女佣。
那之后的七天,她也没有出摊儿,对君说可谓是二十四小时贴身看护,那水准搁现在一天都能拿三百块钱。
“你现在能稍微动一下吗?”第七天夜里,笑嫣按摩完毕后,睁着一双期待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君说白玉般还残留着红色指痕的长颈。
君说坐起来倚在墙上,抬起手抚在颈间来回摇了摇脖子,“差不多了吧。”
笑嫣看着他毫不费力地转动伤处,嘴唇哆嗦地指着他道,“你是不是早就能动了?”
君说偏头想了想,“两日前?三日前?我忘记了!”
“不带你这么耍人玩的!”笑嫣磨着牙根,恨不得冲过去把他掐死,“我知道了,你想报仇是吗!”
她连熬了七天的夜,泥人还有三分火呢,如今知道被君说耍了,新仇加旧恨让她的肝火如置炉鼎。
“我告诉你君说,我……”
“谢了。”
“……”笑嫣的话戛然而止。
君说将头别到一边,又重复了一遍,“谢了……”
笑嫣正欲燃起的怒火被君说不轻不重的两个字瞬间给浇灭了,她的状态有些扭转不过来,半天都没说话。
“你谢谢我?”笑嫣细细咀嚼他这两个字,然后发神经似的上前对他一阵乱拍,“哎呀你突然这么说人家不好意思啦!”
“别拍!”君说嫌恶地打掉她的手,“我谢谢你不是让你得寸进尺!”
笑嫣被他如此对待一点都不生气,伸出指头不怕死活地戳了戳他的脸,“你承认了吧,我们的革命战友关系,别不好意思,我都懂!”
君说因为她的动作僵成了一尊石佛,半饷石佛开口了,声音中充满了威胁,“你再碰我一个试试?”
笑嫣闻言抖了一抖,接着在君说杀人般的目光中,伸出一根指头小兔子般小心翼翼地碰了碰他的衣服。
“这样,如何?”
“……”
癸伊坊风波之后,笑嫣和君说不敢再去西大门摆摊,为了维持生计,他们只得托小刀的父亲刀老爹帮他们在城里的小作坊里觅个职位。临近年末,工作都不好找,刀老爹辗转了好些人才在一个卖猪肉的作坊给他们寻到两个位置。
“一个前院卖肉的,一个后院洗内脏的,你们俩自个儿选吧。”
笑嫣和君说相视一眼,然后各自沉默,他们在等另一方妥协,洗内脏这种活,如果不是神经粗大到可以跳皮筋的程度,应该没有人会喜欢。
“剪子包袱锤,谁输了谁去洗内脏。”
笑嫣一早就教了君说这种全天下最靠运气也是最公平的比赛,两人三局两胜,最终以笑嫣败北告终。
她翻着白眼朝上吹了口气,刘海流水似的掀动。
君说以为她要反悔,只见她把决定败局的拳头含在嘴里,嘴里模糊不清地说些什么。
他听了半天才听明白,洗内脏总比杀猪好。
笑嫣接下了,洗内脏的工作!
君说看着她一脸视死如归的表情,看着她回复刀老爹时的毫不犹豫,竟没有一开始的震惊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习惯了这样的战流戈,这样祈祷着最舒适的生活,却愿意去做最累最脏工作的战流戈。
脏和累其实只是人类十分主观的评判标准,当你习惯于做某件事的时候,它就比任何陌生的工作来得更加得心应手。
笑嫣在猪肉作坊很快地实践了这个真理,一次君说去后院查货,看到某人站在小板凳上一手捞肠子,一手掏心脏,屁股一扭一扭的,嘴里念念有词,半饷猛地一抬头,冲着后院其他工人大吼一声,“赛耶!”
“耶!”十几个工人齐声回应她。
看到那一幕,君说无比庆幸自己赢了决定生死的那场剪子包袱锤。
笑嫣虽说已经习惯了洗内脏的工作,但一天到晚从她过手的猪少说也有十条,卯时干起,申时就累得直不起腰了。她通常借着给前院送货的机会小小的休息一下,时间够得话,还会偷溜出去喝碗茶。
一日,君说从笑嫣手里接过货,大体验了下,就收起来了。
合筐回身的时候看到她不停地敲打肩膀,随口道,“你很累吗?”
笑嫣不答,伸着脖子来回张望,问道,“你这边有能歇着的地方吗,我昨天失眠了,现在头点地儿随时都能睡着。”
君说朝身后轻抬下巴,“帐篷那,将就着吧。”
笑嫣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也不废话,跑过去调整好姿势,眼一闭就睡着了。
君说瞅了她一眼,重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他抄着叉子有一下没一下地钉着案板上的肉。突然,身后传来一阵响动,他的眉不可遏制地抽了起来,正准备回头,眼前走来一位垮着竹篮子的妇人。
只见那妇人目光先是在案板上的猪肉停留了片刻,然后伸着脖子往后面张望,脸上的肉因为高抬的眉毛而绷紧。
“小哥,你们前院还豢着活猪啊?”
君说钉肉的手停下了,整个人浸在一团黑云中,他头也不抬到,几个字似从牙缝里挤出那般,“我兄弟,打鼾呢。”
他还以为自己已经对她的忍耐力晋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没想到,对待她当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一刀磕在案板上,肉末四溅,一股腥臭之味弥漫开来,摊前,捂嘴窃笑的妇人被吓得惊叫不断,连忙揪着裙子跑开了。
“战流戈。”他一字一顿道,“给我起床。”
草棚内,睡得正香的某人完全没有搭理他的意思,君说提着刀走到她跟前,日光斜照,在那磨地锃亮的刀刃上划出一道出即没的银光。
笑嫣感觉眼皮处有光乍现,睁开眼便看到君说杀气腾腾的站在自己面前。
“我的妈哟!”她一个翻身从长板凳下掉下来,在土地上滚了半圈,清醒后指着君说和他手上的刀喊道,“你干什么!大白天的吓唬谁呢!”
君说将刀背到身后,脸依旧阴沉,“我刚才叫你,你没听见吗?”
笑嫣拍拍衣上的土,站了起来,“你刚才叫我了吗?”
“战流戈这三个字我咬得是不准吗?”君说压下,一双眼阴森萧秘,“还是你这耳朵不好使啊?”
笑嫣嘴唇嗫喏两下,眼中恨恨,终是没胆儿反驳他。
君说白了她一眼,转身回去了。
笑嫣看他走远,才敢骂几句,“我当然听不到了,老娘我又不叫战流戈。”淡茶色的眼瞳提溜一转,笑嫣手摸上下巴,自语道,“不行,我得把名字这个事儿好好跟他说说。”
夜,无月照明,整片天空如泼了墨的纸笺,黑湛湛的。
晚饭结束,笑嫣一边收拾碗筷一边用余光偷看君说,窗前,他执笔浅描,拈花扑蝶的仕女图跃然纸上。
君说细细勾勒着仕女的裙摆,白了一眼贼头贼脑的笑嫣,回过神来,朱毫已多划出一寸。
他皱了下眉头,手移向砚台准备补救,正蘸着墨,突然感觉眼前的光瞬息间消匿了,他侧首看去,笑嫣不知什么时候移了过来,正盯着他的画,一脸认真。
“你不觉得你的画少了点什么吗?”
生平第一次有人质疑他的丹青之功,君说放下朱毫,神情严肃道,“少了什么?”
笑嫣抚上白宣,指尖划过那栩栩如生的侍女,唇瓣一挑,“都没有胸,太不写实了。”
君说闻言蹭地一下站了起来,看着面上浅笑的笑嫣,嘴动了又动,半天憋出一句话,“你又想挨打了?”
笑嫣见他如此模样,满脸堆笑地用手肘撞了撞他,“我说笑的,一点都没有幽默感。
君说一如既往地哼了一声,别过头去,决心不再理她。
他重新坐定,拾起朱毫,正准备继续作画,虎口处,笔被闪电般地抽走了,他拧着眉毛地转头看向笑嫣,嫌恶道,“你要作甚?”
笑嫣学着他的语气,“不作甚,不作甚,跟你聊聊天!”说着,她从一便搬了凳子过来,在君说身边坐了下来,“你看咱们俩整天这样,多没意思,我们和好好不好?”
君说见惯了她耍无赖,头转过去推开窗户,呼吸着夜凉之气,也不说话。
笑嫣在心中感叹道,真是个别扭的性格。她挤出一抹灿烂的笑,凑到君说耳边,“给你说哦,我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
君说闻言转头,唇角扯了下,道:“你还给自己起了个名字?”
“嘻嘻。”笑嫣边笑着边点头,“我不能再叫战流戈了,总得有个名字吧。暮、笑、嫣,你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
君说一听,眼露疑惑,问道,“你如何会起这个名字?”
笑嫣想说这名字不是我起的,这是我爸起的,话到嘴边变成,“好听嘛,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
君说面色稍霁,“我一位故友,他的夫人父家姓暮,名笑烟,和你一样的名字。”
“是吗?”笑嫣探过身,眼睛弯成月牙,“她的名字也是取自一笑嫣然之意?
君说学着她的样子笑了一下,趁她不注意从她手中夺过朱毫,顺便讽刺道,“同音不同字,你怎么能和人家比。”
闲时谈论起有关名字的话题,让君说想起了神珏三年结识的那位故友,当时一别,私以为庙堂江湖从此陌路,殊不知不久的将来,两人竟以颠倒的身份重新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