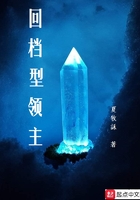事已至此,云天再不拖延,告别了那正激动的抱着两坛美酒狂饮 的白发老者,在众鬼魂神色复杂的目光中缓缓走上通往二重天的阶梯。
云天很快便来到了二楼,这时他才发现,他倒有些小看这刹夜七重楼的内部了。这里根本就还没到那所谓的二重天。出现在他面的前竟是一个极深而且昏暗的长廊,在两边的墙壁之上,血红色的树枝密密麻麻的附着在上面,滚滚的血气从中不断的涌出。
看四下无人,云天急忙将五彩玉牌握在手中,嘴中低声说着诡异的咒语,悄悄的催动了玉牌。这里不比人界,若是有丝毫懈怠,等待他的只能是灰飞烟灭。
云天小心翼翼的向前走着,每当他落脚一步,都会发出极其乱而的鬼叫声。狂乱的血气如同海浪一般不断的拍击着云天的身体,发出啪啪的脆响。云天的右手紧紧握着玉牌,眉头高高的皱起,随时准备催动玉牌。不过还好,那滚滚的血气虽然狂暴有力,不过还是没有穿透老者给他设下的死气防护。
确认自己没事,云天开始加快了速度。由于血气的阻隔,本来只有数十丈远的长廊,云天硬是用了一炷香的世界才堪堪走过。而当他成功走到另一头的时候,他的身体表现竟也是被熏染成殷红之色,如同一个血人一般。
而走过了长廊,他的周围终于宽阔起来,在他的前方,有着一个高大的洞口。而在那洞口的顶端,赫然有着丰都古城四个大字。云天想也没想,既来之则安之,只见他右手紧紧的握住玉牌,大步走了进去。
丰都古城内部死气弥漫,那骇人的更是绵延几千里将整个鬼山完全笼罩着,直到此时此刻的云天才明白。这里如此多的死气恐怕全部都是从远方的鬼山之巅旁的死间冒出的,于是云天没有半点犹豫,直接飞到那死间上方观察起来。
而观察了一会云天发现,里面除了死气极其浓厚以外,其他再无异常,不过出于谨慎,云天还是催动了玉牌。这里的死气太过的狂暴,老者的鬼气防护恐怕很难再起到作用,若是他没有准备,恐怕会瞬间被泄露进来的死气侵蚀。
然而云天进入到山间内部,景象却是另有不同,这里并没有他所想的那样死气弥漫,反而是显得异常安逸。云天走进前方的隧道,黑幽幽的隧道又窄又挤,四周全是凹凸不平的岩石堆砌而成的石壁,上面雕刻着一些奇怪的文字图案。
而这里的光线也是极其的微弱,云天小心的向前缓缓前行,时不时的会有一股股冰冷寒气迎面而来。一股腥臭的血腥味道,刺激著云天的鼻子,刺骨的寒风总是会悄无声息地从身边刮起。不知不觉云天的手掌心也微微冒出了些虚汗,而那玉牌还依然被他紧紧的握在手里。
走到了隧道深处,云天突然被一道数十丈高的石门挡住了去路,上面没有任何可以开启的机关,只有一个刻印在石门上的“两仪四象八卦图”。别无选择,云天只能试着去开启这道石门。说起来,他在妖界的时候,对这四象八卦还是有些了解的。
这四象八卦图看似只是个单一且凹凸有致的圆弧,实则却蕴含天地星辰的高深道意。首先这阴阳两仪位处其最中间,靠外的是四向(东南西北)四方位而借力。而在弧的最外面是上边有坎、坤、震、巽、离、乾、兑、艮八个方位钮;也分别代表著休、生、伤、杜、景、死、惊、开这八门。
休门属离宫、生门属坎宫、伤门属坤艮宫、景门属乾兑宫、死门属坎宫、惊门属震巽宫、开门则属震巽宫。
“还有什么?恩。。。。”云天努力的寻找着记忆,自从被抽离了两魄之后,他不但智力有所下降,即便是有些记忆也是随之消失了。这让他很是头疼,但是眼前却只有这个办法进去了,于是他继续翻阅着脑海中的记忆,经过一番费神,那暗藏的记忆最后还是终于被他给想起来了。
这八卦图的启动在不同的时辰,也有不同的排列方式,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有足够的能量开启才可以。有时生门在艮八的位置,晚两个时辰又出现在坎一的地方。
“额,现在是什么时辰了。地府也有时间吗?不过若是真有时间的话,那么如今这里天空的昏暗程度,和我进塔前的昏暗对比看来,应该就是人界的子时吧。而子时的生门是在这里。”
云天仔细的推算着,不过地府常年都是昏暗无光的,他也只能是大概推算一下。在他确定了时辰之后,当即准备要按下坤三生门上的凸块时,他的手掌忽地停了下来,因为在刚才,他手中的玉牌突然剧烈的晃动了一下,使他的手掌偏离了轨迹。
“不对,诸神令乃是神器,它刚才阻止我触碰凸块,那里应该不是生门,看来这应该是用死门的乾来做为入口启动才是!”
想到这里,云天一阵胆寒。怪不得他们说这七重天内危险重重。今天若不是有玉牌在手,他的小命非得栽在这不可。可想而知,光是在这四象八卦图前,就得有多少自作聪明的鬼魂湮灭啊。
稍作稳定,云天上前直接将乾三生门的凸块用力按住,一股紫金色的元力缓缓的灌入其中。不过要想打开这死门也绝非易事,所以云天直接使出了七层的力量,拼命的将元力灌输进去。
“咔!……”
只听一声脆响,门竟然真的缓缓打开了!刹时间云天松了一口气,暗叹一声好险,如今终于通过二重天了。此时他才发现,他背后的衣衫早已经被冷汗湿透。
然而令云天想不到的是,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他神色呆滞的望着石门内部顶端的牌匾,上面清晰的雕刻着——刹夜二重天,脸上有着尴尬之色。接下来,他才要真正的面对二重天的考验,看来刚才,他只是空欢喜一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