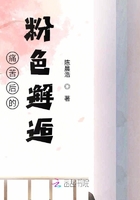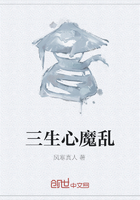淡淡的云遮住了太阳,自己也被太阳烤的发红,阳光费力地从云缝中挣扎出来,带着柔和的氲彩慷慨地洒在大地上。
田地中的麦苗已经开始抽穗,微风吹过,如海上的波涛起伏,让人很自然地想起麦浪这个词,蝈蝈在它们喜爱的麦田中肆意地挥霍着精力,发出求偶的音阶,远处的村子就在麦田的尽头,村中升起了几缕烟雾,不知是炊烟还是驱赶蚊虫点起的火堆。
不时有赶着牛和犁杖的村民冲着两人打着招呼,艾草焚烧出的苦烟随着清风飘荡,静谧的路上不时有几只布谷鸟在欢叫,偶尔村中会传来一阵狗吠和牛的嘶鸣。
“真美啊。”
刘健仔细地嗅着空气中淡淡的花香和艾草的芬芳,仿佛这一切就是一幅画卷,置身其中感受到里面的温馨和恬适,有些醉了。
“你怎么知道她美?看背影还不错,不知道长的什么样,别像王大婶她姑娘似的,后面看真水灵,正面看就……嘿嘿……”
赵玉林此时正用手遮着并不刺眼的阳光朝前观看着,一个女人骑在马上的背影在前面的道路上慢慢地前行着,不时轻轻甩一下鞭子,清脆的响声引起一阵犬吠。
赵玉林显然不知道刘健在感慨正如画一般的景色,以为是在说前面的那个女人。听到赵玉林这么说,刘健才发现前面的道路上的确有一个人骑着一匹黑色的马,在慢慢地朝着村子走着。
“走啊,看看去,这可不是咱们村子的人。”说完,赵玉林用靴子上的铁后跟踢了一下马腹,黑马不满地嘶鸣了一声,朝前奔去。
刘健胯下的马儿看着前面奔跑的同类,不等主人踢它,已经迈开了脚步紧紧跟在后面。
女人似乎听到了后面的声响,一拉缰绳,让马横在了路上。
“你们好啊。”
女人在马背上冲着两人打了声招呼,两人急忙停了下来回了声你好,这才打量起面前的女人。
精致的棉布衬衫包裹着女人的身躯,干净而又整洁,没有一丝褶皱,下身是一条细长的裤子,将女人修长的双腿彰显的淋漓尽致,脚上穿着的是一双男式的马靴,高高的靴筒一直到膝盖的下面,鞋后跟上也有一小块可以当做马刺的铁皮包裹着。
乌黑的长发一直垂到腰身,松散的舒展着,仅仅在肩后用一根小巧的头绳扎住,明亮的眼睛带着淡淡的笑意也在打量着他们两个,洁白的牙齿在微笑的时候总会露出一点。
不知道是因为夕阳还是因为女人的笑容太过耀眼,刘健伸出手遮在了眼睛上,这才注意到女人的肤色并不白,是那种宛如小麦一样的健康颜色,和金色的夕阳融为一体,仿佛抹上了一层釉彩。女人的笑很迷人,让人忍不住就生出一点亲近的感觉,但是仔细看过去却总让人感觉到有种淡淡的嘲弄,不知为什么,刘健忽然想到了很久前在山林中追逐的那只豹子,狂野而又优雅,美丽而又诱惑,似乎在追逐中那只灵动的猫科动物也有过这种貌似嘲弄的表情。
微风袭来,带来一阵淡淡的香味儿,不知道是女人身上的还是山野中的花香。刘健觉得很奇怪,这样的女人不应该穿着衬衫和马靴走在布满林荫的路上,而应该穿着华服和优雅的吴国长裙,轻摇着玻璃杯,杯里面是加了冰块的秦国西域葡萄酒,在摇曳的烛光中和贵妇们谈着诗词……
女人没有介意刘健有些不礼貌的注视,仍旧微微笑着,身下的黑马有些急躁地踢踏着步子。
“前面就是三河村吧?”
女人伸出手用鞭子指了指远处飘着青烟的村庄问道。刘健点点头,女人得到了肯定的回答,笑着回了声谢谢,然后说道:“我叫羊曦,将来就要在你们村子住下了,方便的话可以带我去见一下村长嘛?”
“好啊,正好我们顺便要回村子。”既然要去见村长,那就是顺路了。刘健提了下缰绳,和赵玉林并排走在了前面。
村公所的院子就在集市的前面,一排柳树在晚风中轻轻起舞,院子周围的篱笆并不高,仅仅为了防止鸡鸭钻进去糟蹋才冒出头的菜苗。大门敞开着,但是也挡起了三尺多高的木板,反正这里的人就像是长在马背上一样,这么高的木板根本不是任何障碍。
“喏,那就是,您过去吧。我们还有事,那么再见了,美丽的女士。”
“多谢了。”女人说完,将马鞭插在鞍子上,整理了下已经很整洁的衣衫,让马向后退了几步,猛然一个加速,然后向上一提缰绳,胯下的黑马优雅地张开蹄子跳过了木板……
傍晚的集市很喧闹,干了一整天活的人们聚在一起抽上一支烟,饶有趣味地看着十多岁的孩子们拿着和燧发枪一样长的木棍在老退役军人的督导下练习着队列——女王殿下的军队可是非常严格的,对于从生下来就注定要服役的自由民来说,与其到了军队中吃鞭子枪通条的抽打,还不如从小就开始练习。
几个头发已经灰白的老人蹲在街口抽着烟,一边看着正在练习队列的孩子们,一边吹嘘着他们年轻时和通古斯人的争斗,不时发出一阵阵笑声。
三河村的人大部分都在骑兵部队服役,因为他们基本在燕国的最北部边境了,经常性地和通古斯部落争斗使他们的马术都很优秀,所以征兵的时候基本不会被分配到燧发枪连队。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咱们那时候可是十五岁就要服役,再看看他们,十五岁的时候还那么瘦弱,甩一堆鼻涕就能把他们砸死……”
“是啊,只是咱们自由民在战场上越来越危险了,咱们服役的时候,恶心的燧发枪还没有出现,那时候才是咱们的天下啊,嘿……骑枪准备,慢步跑,加速……自由民,冲锋!就算是现在,一想到这些话,我觉得自己的血都热了起来。冲锋后扔掉骑枪换上马刀,敌人就像秋天田地里的老鼠一样四散逃开,除了秦国的西域游骑兵,谁能挡住自由民的马刀……可是现在呢?如果不是从背后冲锋,跑到一半可就要被打成了筛子……随着枪越来越快,或许骑兵会被淘汰吧……”
“别扯淡了,骑兵永远不会被淘汰的,我问你,快速的机动到侧翼然后发动突袭、或是追击那些逃兵,打一场痛快漓淋的歼灭战而不是击溃战、从中间突破然后向两翼包抄……这些除了骑兵还有谁能做到?就算一千年一万年骑兵也不会被淘汰……”
刘健和赵玉林并排走在宽敞的石子路上,一边礼貌地和老年人打着招呼,一边对他们的言论不屑一顾。
“嘿,老榆树又在那讲他在王启年公爵手下当雇佣兵的故事了,去听一会儿吧?”
前面不远处的石板上坐着一个左臂残废的高大中年人,正在那唾沫横飞地讲着什么,旁边是一群小伙子。刘健很快记起了这个人,在近卫掷弹骑兵团服役八年后放弃了去尉官学校进修的机会,以雇佣兵的身份加入了一支受到华夏各国王室支持的远征殖民军队,在墨西哥掠夺西班牙人银矿的时候被西班牙人的铅弹击中了左臂,对于这样的伤害只能采用截肢,因为从枪口中飞出的铅丸口径很大,击打在人的身上会将骨头和肌肉都打碎,残留在身上的铅也将是致命的伤害,所以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截肢——用麻沸散麻醉后用锯子割下手臂,至于感染与否或是能否活下来,就看个人的造化了。
所幸的是这个人活了下来,并且不久后就乘船从北方冰冷的海上回到了家乡。因为他姓于,年轻人都称其为老于叔,加上他那粗壮的如同榆树一般的体魄和倔强的性格,久而久之老于叔就成了老榆树。
他带回了几百个西班牙银币,还有两套金黄色的、上面绣着巨大十字架的西班牙军服,以及几柄印第安战斧,和一盆村子里的人从未见过的仙人掌。
名义上远征军是去扶桑洲帮助那些受被众人压迫的黄种兄弟、殷商遗民——西夷语中对那些人的叫法是印第安,可不是殷地安否的含义嘛?至于去帮助黄种兄弟反抗白种人压迫的老榆树为什么会带回来印第安战斧,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记忆中刘健听过很多次他讲的故事,只是现在却怎么也不记不起来了,所以看到他在讲故事就像停下来听一会儿。
“我的烟叶可不多了,你知道的,老榆树抽烟可从来都是‘伸手牌’的,而且一会集市就散了。你去听吧,我去把鱼卖掉。晚上别自己回去弄吃的了,来我家,老爷子白天好像去采松茸了,晚上有汤喝。”
赵玉林拍了拍刘健的肩膀,转身离开。刘健下了马,蹲在一排听众的身边,掏出烟叶子和烟纸给众人一人一支,开始支起耳朵听着老榆树讲故事。
刘健并不想服役,因为这个时代的战争是靠绝对的纪律来取胜的,甚至包括将军都需要承受着忽如其来的铅弹,能否活下来只有靠运气,个人的勇武在这个时代在排成线列的燧发枪前面已经不再有任何作用。在他原本生活的那个时代,有人曾形象地称这个时代为排队枪毙的时代。
这个时代是西方第一次可以睥睨东方的时代,是西方人将盎格鲁萨克逊语布满世界的时代,虽然现在看来,这和他所熟知的历史有所不同,但他希望在这个世界的历史中有他的名字——但不希望是被记载在史书中一笔带过的烈士。
历史或许和他熟知的不同,但科学却不会不同。他该为这个正在觉醒和启蒙的民族做些什么,但是一个命不由己的士兵不会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他现在需要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什么办法可以不用去服役。虽然每一个自由民小的时候必须熟读一些书籍,而且必须能够认识一千个字,如果达不到将会每年罚家里十个银币——相当于二百斤小麦,直到达到要求为止,但是静谧的山村挡住了城市中刺鼻的煤烟,却也挡住了时政与科学。
刘健的脑袋里对于外面的世界知道的并不多,王室和贵族也不需要他们自由民知道,自由民存在的价值就是成为忠于王室的士兵,对外扩张的排头兵和革命出现时的刽子手——自由民土地的无税制度决定了他们将是王室最忠心的支持者,他们和南方的那些贫苦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完全不同。
抛却了脑袋中乱七八糟的想法,刘健吸了一口烟听着老榆树讲着在扶桑洲的奇异景色,那时候的美洲对于华夏之地甚至整个世界来说还是一片不可知之地,但是那里的白银和黄金却让无数人踏上甲板,开始一段不知未来的旅行和探险。
“哎,老榆树,你真当过王启年公爵的传令兵?不是吹的吧?”
面对听众的质疑,老榆树呸了一口骂道:“废话,我当然当过他的传令兵。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当年我的马术可是在国王殿下的御前比武中得过奖的,按西夷人的说法,我在扶桑的时候一分钟可以装填新式的燧发枪将近四次,这样的速度就算放在装填速度最快的齐国技击士团也是合格的。
齐国技击士团的装填速度可是最快的,你们在朝鲜和他们打过仗,应该知道那恐怖的排枪速度吧,我可不是吹。
我跟你说件别人不知道的事,你们知道王启年的爵位是世袭的吧?而且是九位选帝侯共同认定的世袭爵位,虽然没有封地,却拥有所有华夏帝国邦国的居住权和海外殖民地开拓权……”
周围人发出一阵不屑的嘘声,喊道:“废话,我当然知道,他这爵位是他祖爷爷传下来的,就是已经陪葬黄帝陵的王直,绕了地球一圈发现世界是圆的那个,你要说的秘密不会就是这事吧?
这事连才学会《三字经》的孩子都知道,前些年新编的《三字经》不就有这句话嘛?什么王直公,御孤帆,向东驶,自西归,绕扶桑,游昆仑,拓四海,终封侯……”
老榆树不屑地呸了一声道:“废话,这些当然都不是秘密,我跟你们说,当年王直公可是在吕宋附近当海盗的,后来有一年他们遇到了几艘没见过的西夷帆船,那还能跟那些西夷人客气?一阵乱打,那些西夷人就死了个七七八八,那些西夷人的首领是葡萄牙人,叫什么麦哲伦也不什么的,王直公这才知道那个叫麦哲伦什么的从西边航行了一圈到了这里。正好那时候越国海军开始剿灭海盗,王直一看这买卖也不好做了,就带了几百个亲近的兄弟,抓了几个葡萄牙的水手当向导,绕了地球一圈,回来不久就被九位选帝侯封为拓海公,之后各国的王室和贵族都纷纷资助他环球航行,每年从扶桑带回来的白银和昆仑洲带回来的昆仑奴,那都是王室共同分成的……这事你们知道?我这胳膊,当年就是给前线传令的时候被铅弹打中的……”
听到这里,刘健惊讶地大大地张开了嘴,看来老榆树说的都是真的,因为麦哲伦这个名字刘健实在是太熟悉了,而这个世界中第一个环球航行的是王直,根本就没出现过麦哲伦的名字,原来是这么回事。
又听了一阵,刘健大概明白了这个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框架,华夏出于类似春秋战国的时代,但是曾经出现过无数次的统一,又无数次分裂,但在名义上还是一个帝国。
车同轨,书同文,每年三月初三各国王室都会去拜祭黄帝陵。各国只能称王而不得称黄帝。
黄帝类似于春秋时的霸主,只有名誉上的称号,并不是完全的皇权。而且是由各大邦国的王室共同推选出来,近百年来,没有一个国王能做到让其余诸邦都信服,因而也就没有皇帝。
齐、楚、燕、韩、赵、魏、齐、汉、吴、越十个大国,韩赵魏仍旧在三晋之地,那里是各个大国间的缓冲,也是关东诸国防备强秦的桥头堡。
汉在川蜀之地,按照老榆树说的,似乎现在已经掠夺到了印度。
燕国占据着辽东和外东北,北部朝鲜和库页岛以及虾夷都是其囊中之物,刘健的父亲就是死在燕国与齐国争夺北部朝鲜的继承权战争中阵亡的。
刘健咬着已经湿润的烟卷,又听了一阵,老榆树再也没说这些邦国的事,而是说起了印第安女人和昆仑洲女人以及西班牙女人的区别……
对于老榆树现在说的这些事,刘健着实没什么兴趣,这些问题他上辈子就研究的很明白了。
夕阳渐渐落下,村中老树的投影渐渐拉长,大约是说的累了,众人都散了。刘健跳上马背,静静地走在宽敞的街道上,然后决定一定要走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
略带苦味的艾草香味在街上飘荡,蚊虫门纷纷逃开,村口的河边传来孩子们的嬉戏声,还有母亲呼唤孩子回家吃饭的喊叫声,学堂中幼童那朗朗的读书声穿越了袅袅的炊烟传到了刘健的耳朵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这是一个最激情的时代,在另一个时空中中华民族被世界整整落下了三百年,而在这个时空却有一个几乎完美的开局。大时代缓缓揭开了帷幕,刘健相信,在这个时代,从西伯利亚的荒原到阿拉斯加的雪地,从非洲的黄金海岸到美洲的五湖之滨,从水肥草美的新西兰到海盗肆虐的加勒比,都将在村落和城市中回荡着抑扬顿挫的读书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