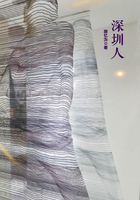我是怎样自杀的
〔土耳其〕阿吉兹·涅辛
报上刊登自杀的消息,通常是被禁止的,然而,下面要谈的是我个人的自杀问题,因此,我希望威严的官府,不仅能高抬贵手,准予报道,甚至还能为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的自杀庆幸。我曾一度得了自杀狂症,心里总想着自杀。我的第一次自杀经过是这样的:“喂,朋友!”我自言自语道,“怎么个死法更好,用手枪,还是用匕首?”死么,都是一样的……但是至少让我死得高雅一些:我决定服毒自杀。我买了剧毒药品,将自己关在屋里,写了一封充满浪漫情调的长信,结尾写道:“永别了,空虚的人生;永别了,变幻莫测的命运;永别了,所有的一切……”然后,我服了一杯毒药就躺倒在地上。现在我的血管就要萎缩了,我的手脚就要抽搐,血液就要凝结。我这样等了又等,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于是,我再喝一杯毒药,接着又是一杯……但是,毫无反应。后来,我恍然大悟:原来,在这个国家里,不仅牛奶掺水,油掺假,干酪掺假,就连毒药也是掺假的。因而,一个人想随心所欲采取一种自杀手段也是做不到的。而我个人,想到就要做到。这一次,我决定朝自己的头砰的来一枪以了却我的残生。我把枪口对准太阳穴,扣动扳机:“咔——嗒!”又扣动了扳机:“咔——嗒!”再扣动了一次扳机:“咔——嗒嗒!”原来,这支枪是某国援助的一批武器中的一支,里面缺少零件。我看用枪弹结束自己生命已经不可能了。于是,我想到了另一种保险的办法——用煤气来窒息自己。据说,煤气中毒致死是富有诗意的。我把煤气开足,并将屋里的所有缝隙都堵住了。我倒在椅子上,摆好了最合适的姿势,以便在人们找到我的尸体时能够保持肃穆的气氛,于是,等待着阿兹拉伊尔来临。中午过去了,夜幕降临,而我的呼吸怎么也不停止。晚上,我的一位朋友来找我。
“不要进来!”我大声嚷道。
“怎么啦?”
“我正在死呢。”
“你没有死,你是在发疯。”他说。
我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我的朋友。他捧腹大笑道:“你真蠢,从煤气阀门出来的不是煤气,而是空气。”
说完,他又问我:“你真想自杀吗?”
“当然是真的。”我答道。
“我愿意助你一臂之力。”他说。
接着,他建议我到制刀匠那里买一把布尔萨刀,然后像勇敢的日本武士那样切腹自尽,并让肚子里的肠子流到自己的手心里。我对我的朋友所表示的友谊和关怀表示感谢,并立即去买了一把布尔萨刀。老实说,用刀子哗的一声地剖开自己的肚子,并不是一件好受的事。而且我觉得,当我的尸体被抬到停尸室里进行检验时,医生如果在我的肚子里看不到有任何食物,那可太难堪了。管它呢,我还是把刀子放进怀里,高高兴兴地跑回家去。正在这时,两个警察向我冲过来。于是,我向警察解释:“先生们,请等一下,先听我说。我老老实实地交纳税金,我从不说政府闲话。像我这样的老实人……”警察打断了我的话,并从我怀里搜出了那把刀子。
“这是什么?”警察吼叫起来了。原来,我正好遇上这两个专管搜捕和制止犯罪活动的警察。
“唉,我的真主啊!”我自言自语道,“我无法在这个国度里活下去,我做出自杀的决定,是最合适的。但是,你看,我也没办法离开这个尘世呵!……难道我总是这样受折磨吗?”我是有决心有意志的人,一旦说要死,我就一定要去死。我从杂货店老板处买了一条粗绳子,还有一块肥皂。我在绳子上涂抹了肥皂,系在天花板上的吊钩上。当时我的心情像是踏进税务局大门一样,把自己的脖子套在涂抹了肥皂的绳子上,接着就一脚踢掉了椅子。可是,我并没有被吊起来,扑通一声,我跌落在地板上了。原来,绳子也是腐朽的。看来,我无法找到结实的绳子了。我得去找那位老板。店主说:“若是好货,我们还卖吗?”我完全明白了,自杀是无指望了。
“算了,就这样活下去吧!”我自言自语道。众所周知,民以食为天。我特别爱吃腊肉煎鸡蛋。我在一家饭馆里,先吃腊肉煎鸡蛋、罐头橄榄油煎白菜卷以及一份通心粉;后到糖果店买四五块甜酥吃了。这时,一个卖报人走过来,喊道:“共十六版。你如不想看,可当包装纸用。”
我没有读官方报纸的习惯,但是,这回,我对报贩说,我要一份。当然,读社论时,我就朦胧地入睡了。突然,我感到腹部剧烈绞痛,似乎有人用刀子在我肚子里搅动。我无法形容疼痛的滋味……我实在受不了了,喊了起来。人们用急救车把我送进急救中心。我已昏过去了。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一个医生站在我的身边,他问道:“你好像中毒了,你不能瞒着医生,你想自杀吧?”
“说到哪里去了?医生,在这幸福的日子里,您说到哪里去了?”
“你是中毒了,你吃了什么?”
“腊肉。”
“什么,吃了腊肉?”医生大声地说,“你疯了,腊肉能吃吗?难道没有看报?医院挤满了腊肉中毒患者。但是,你不像吃腊肉后中毒的人。你还吃了什么东西?”
“我去过饭馆……”
“你大概是疯了。”
“在饭馆里吃了罐头。”
“怪不得,还吃什么了?”
“通心粉、甜酥……”
“你当然要中毒了,罐头、通心粉、甜酥……”医生说。
“除了这些,你还吃了什么?”医生又问。
“我向真主发誓,再没有吃别的东西了,只是在读官方报纸时……”
“啊?”医生惊叫起来,“谢天谢地,你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出院时,我在想:算了吧,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求生不得,欲死不能……我们只能无声无息地苟延残喘地活下去。
田野里出世的婴孩
〔土耳其〕奥尔汉·凯马尔
在一望无际的棉田里,农场工人们十五人或二十人排成一列,一个劲儿在清除秧苗旁的杂草。在骄阳中,气温一直升至一百四十九度,在炫目的、铅灰色的天空下,没有一只鸟儿在飞翔。太阳似乎主宰着一切。农场工人们汗水涔涔,有节奏地不断挥动锄头。锄头的尖端落在焦土上,发出“啦”“啦”的声音;随着锄头均匀的起落声,农场工人们哼着歌,烈日的淫威似乎吞没了这歌声。剩下来的土地里,他们播种小米。播种,收割,然后包装,亲人们给我们送来石榴和香梨。法尔霍·乌扎依尔那双肿胀的手满是汗水,他把汗都揩在那条宽松的黑裤子上,同时掉过头去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瞧着他身旁挥锄的妻子,他用库尔德语问,“怎么?你怎么啦?”
古丽沙是一个肩膀宽宽的结实女人。她干瘪瘪的脸上淌着亮晶晶的汗珠。由于剧痛,脸已经不成样儿,而且露出一道道的皱纹。她没有回答。
法尔霍·乌扎依尔用胳膊狠狠推了她的腰部:“女人,你到底怎么啦?”
古丽沙用疲倦的眼神瞥了丈夫一眼。她的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窝里,怪吓人的。这时锄头忽地从她手中滑落,掉在地上。她用手紧紧按住大肚子,俯下身去,然后在红棕色的土地上跪了下来,由于烈日的曝晒,土地到处裂开。监视他们干活的汉子撑着黑色的太阳伞站在一旁,这时叫了起来:“古丽沙!是这个吗?不要再干了,走开!”
她痛得死去活来。她用枯瘦而依然有力的手指抓住一块干裂的泥土,手指捏得紧紧的。她使出常人罕有的力,咬紧牙关控制着自己。一圈圈漆黑的斑点在她眼前飞舞。她突然呻吟起来,“哎哟哟!”对一个女人来说,劳动时被陌生人听到这种声音真是丢脸。法尔霍·乌扎依尔咒骂起来,飞起大腿朝妻子的腰部狠狠踢了一脚。女人驯服地蹲在地上。她知道这副样子丈夫是不会宽恕的。
当她两手撑着地挣扎着站起来时,监工的又说:“古丽沙!快走!娘们儿!现在你赶快走,快!”她的阵痛遽然停止了,但她感到等一会又会突如其来,而且来势会更加凶猛。她朝离她约莫一千英尺远的沟渠走去,这是农场的边界。
法尔霍·乌扎依尔在他妻子身后咆哮着,他看到九岁的女儿赤脚站在监工的身旁,于是吩咐她说:“你得替妈干活!”
女孩知道现在该轮到她了。她拿起和自己身子一般高的锄头,走到行列里。锄头的柄上还沾满妈妈手上的汗呢。这种事是很平常的。锄头的起落声依旧和农场工人们的歌声相应和。太阳直射在堆满畜肥的沟渠上。草绿色的蜥蜴在红褐色的泥土上悄悄爬过。
古丽沙挺直身子站在沟渠里,她环顾四周,在炙人的热浪中侧耳细听。看不到什么人。空旷的土地上热气逼人,这片土地向远处延伸,似乎没有尽头。伯劳鸟的尖叫声在空中回荡。她把宽大的黑裤子口袋里的物件全部倒空,并取出一些东西。她知道自己分娩期已近,早就张罗好这些东西:缠在一块纸板上的两股长线,一把生锈的刀片,几件颜色不同的衣服,还有破布、盐和柠檬干。这些东西,她是在农场的垃圾桶里找到的。她准备把柠檬汁榨到婴儿的眼睛里,用盐擦孩子的身体。她把衬裤一直褪到腰部下面,将婴儿的裤子折好放在一块大岩石下面,在地上铺好破布,把缠在纸板上的线解开,并把柠檬切成两片。
她不想蹲下身去,忽听到后面有走动声。原来是一只狼狗!她捡起一块石头向它扔去。那只狗吃了一惊逃开了,但没有离开。它等着,润湿的鼻子嗅呀嗅的。古丽沙紧张极了,要是她现在生孩子,昏了过去,那只狼狗就会把孩子活活咬成一块块的!她还记得那位库尔德姑娘菲丽丝。菲丽丝也像她一样在沟渠里分娩,她把孩子抱到身边后,竟昏了过去。
她醒来时向四周一瞧——孩子不见了。她到处找寻……最后,在远处一株矮树下,她发现孩子已被一只狼狗咬得支离破碎!古丽沙又向那只狼狗看了一眼,瞪着眼仔细打量。狼狗在她的目光下退了几步,但还是盯住她。眼睛射出异样的光芒……
“莎弗仑,”她叫,“莎弗仑。”她不懂自己怎么会喊起远在约一千英尺以外的女儿来:“快来揍它!你这只该死的恶狗!”
那只狗勉强退后三十英尺左右,又停下身来蹲着,眼睛闪着蓝幽幽的光,伺机而动。这时古丽沙肚子又痛了起来,这是最厉害的一次阵痛。她裸着膝盖蹲下来,两手撑住地面,呻吟起来。她脖子上静脉粗得像手指一般,颤动着。疼痛一阵接一阵袭来,一次比一次痛得厉害。突然涌出一股热血……她的脸露出惊骇的神情。整个世界在她眼前垮了下来。
“法尔霍,庄稼汉,”监工说,“跑去瞧瞧那个女人……她也许会送命的。”
法尔霍·乌扎依尔朝妻子在苦苦挣扎的那个沟渠望去,摇摇头,恨恨地骂了几声,继续干活。他怒火中烧,怨恨自己的妻子。额上冷汗直冒,汗水从他浓眉下一滴滴淌下来。
“瞧那边,小子,”监工又说,“跑去看一看那女人怎么样了。”
法尔霍·乌扎依尔把锄头扔在一边,往那边跑去。真想一脚接一脚地踢她……这个不中用的女人捣他的鬼,他真受不了。他在沟渠边停住脚,睁大眼睛向下瞧。古丽沙倒在地上的小路旁。在沾满鲜血的一块破布上,浑身上下一片紫红色的婴儿在伸手伸脚地扭动。一只狼狗正扑在婴儿身上。他霍地跳下沟渠。狼舐着血淋淋的嘴,三脚两步逃开了。法尔霍·乌扎依尔把围在婴儿脸上的绿翅苍蝇赶走。婴儿闭着眼睛,手脚还在扭动。法尔霍·乌扎依尔打开布来,原来是一个男孩子!男孩子!法尔霍一下子变了。他仰望天空,严峻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他抱起婴儿,从地上捡起血迹斑斑的破布。
“我的儿子!”他大叫一声。他乐得几乎疯了。养了四个女孩后,居然来了一个男孩!古丽沙感到丈夫就在身边,张开眼来。她不顾自己的身体,挣扎着想站起来。
“这回你挺不错。”法尔霍·乌扎依尔说。
“挺不错的,女人!”他抱着婴儿从沟渠里一跃而出。监工看到他穿过红棕色干裂的土壤跑来。
“那边……那边……”他说,“法尔霍向这边走来了!”大伙儿都停止干活。农场工人们倚着锄头,目不转睛地瞅着。
法尔霍气喘吁吁地走了过来,大声喊道:“我的儿子!我有一个儿子了!”
他把婴儿紧紧抱在胸前,婴儿裹在一块带血的破布里,浑身还是紫红色的。
“嗨,你得小心,庄稼汉,”监工说,“当心,庄稼汉!别抱得这么紧,你会把他闷死的……现在你回农场去吧。告诉厨师,是我派你来叫他给你些油和糖浆,让女人吃一些吧。走吧!”法尔霍·乌扎依尔不再感到疲倦了,炎热他也不在乎。现在他年轻得像二十岁的小伙子,身上轻捷得像小鸟似的。他向农场的小泥屋走去,茅屋顶在他的眼前隐隐闪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