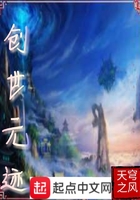不过,萨拉根本没有听进去这番话,当奶妈提到那个年轻的印第安人时,她不再那么心慌意乱了,因为她认为能遇到他,这纯粹是上天的安排,她甚至想回头看看这个年轻人是否会暗中跟踪她。
但萨拉可不是个胆怯的姑娘,她在热带的太阳和植物的刺激下,变得异常泼辣;她自己感觉像西班牙女人一样漂亮,她敢于直视这些男人,是因为每当男人面对她的高傲时,都会自惭形秽;尽管他那么极力地保护她,她也懒得看他一眼。
萨拉既然肯定这个印第安青年注意她,她就大概不会搞错。这个印第安青年名叫马丁·帕兹,他在姑娘危难时挺身而出。危难过后,他估计姑娘肯定已经走了,所以他在暗中尾随着她,因为四周一片漆黑,所以他也不必过分隐藏自己。
马丁·帕兹是一个贵族的后裔,但这个英俊青年却从不穿传统的山地印第安人服装,又黑又亮的头发,暴露在宽沿草帽的外面,富有磁性的嗓音充满了男性的阳刚之气。眼光明亮,永远充满着温和与幸福,让人顿生亲善甜蜜之感;鼻梁高耸挺拔,嘴角荡漾着笑意,这是与他的同一血统的男人截然不同的,他是芒戈-卡帕后裔中的美男子,他身上永远流淌着澎湃的血液,能使其对前程充满信心。
他身上披着一件大红的“捧首”,腰上佩着一把马来匕首,当他一旦把匕首握在手中时,就可能轻易地斩断任何对手的手臂。马丁·帕兹曾是北美洲安大略湖流域游牧部落的一位领袖,曾领导族人多次英勇地反抗英国人的压迫。
马丁·帕兹也很清楚,这个利马城最漂亮的姑娘——萨拉,是犹太富翁萨米埃尔的女儿,而且她已和混血儿安德烈·塞尔塔定了亲;他也知道她的出身是多么的高贵;但他没有想到,自己凭一时冲动产生的念头只是痴心妄想罢了。他只是不顾一切地想看到她,照顾她,今生今世,就像森林眷顾着羊驼,天空包容着飞鹰一般。
马丁·帕兹在迷恋中不能自拔,他紧赶了几步,直到看到姑娘的裙子在门口消失;但是与此同时,萨拉却又回过头来,把面纱拉开一点,向他露出感激的目光,让他如醉如痴。
但这时,他身后来了两个赞柏族印第安人,这是两个强盗。他们靠近了马丁·帕兹。
“马丁·帕兹,”一个说,“我们的兄弟要见你,今晚你必须到山里和他会面!”
“我当然知道该怎么做。”马丁·帕兹傲然答道。
“‘天神报喜’”号纵帆船已经在卡亚俄港海面出现了,不久它就会逆风而上,然后在当局武装的护卫下离开,而且里马克河口是它向陆地靠近时的必经之处。到时我们会用小船来帮他们减轻负担,你到时一定要在场!”
“这机会错过了可就可惜了,而你们也就白费心机了,马丁·帕兹的事不用你们操心,他知道该怎么做。”
“这也是桑伯的意思,我们刚才见过他了。”
“我的意思已经对你们说得很明白了。”
“不用解释,我爱到哪儿去完全是我自己的事。”
“难道你就是为了到这个犹太人的家门前来?”
“一直讨厌他的兄弟们,我今夜会到山里去的。”
三个人无言地对视了片刻,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赞柏人又返回里马克河口去了,他们迅速消失在黑夜中。
马丁·帕兹也毫不犹豫地走近了萨拉的家,这是一座典型的利马式住宅,只有上下两层,最下层是砖砌的地基,比那由木柱篱笆涂上石灰建成的墙还要高,而这种结构也无疑是为了抵抗地震,在粉刷过的墙面上画上砖砌的方格;争奇斗妍的鲜花长满了方形屋顶,就如同一个布置巧妙的大阳台一般。
宽敞的大门两旁各有一座别致的小亭,从这儿可以进到院子里;不过在利马的风俗中,亭子向街的一面是不开窗子的。
马丁·帕兹走到犹太人屋前时已经11点钟了,周围听不到任何声音了;但从宅内隐隐约约的灯光可以判断,萨米埃尔还没有睡。
马丁·帕兹呆呆地站在墙前,他为什么不在这幽香清凉的空气中散步呢?他为什么无暇去观赏那灿烂的星空和远方广场上方那朦胧的月色呢?
夜色在晶莹剔透的星星点缀下是如此的迷人,大地也温柔地睡去了;但是,他和他的心上人,却只能用心灵来交流,而中间隔了这么远的距离。
后来,在阳台的花丛中出现了一个白色的身影,她在这百花丛中、在这朦胧的夜色衬托下是如此的迷人,花也因此而奉献出它们的芬芳;随着东风的轻轻吹送,大丽菊、薄荷、向日葵那沁人心脾的馨香扑面袭来,而在这个大花篮中,站着那位年轻的漂亮的犹太姑娘,马丁·帕兹的心上人——萨拉。
马丁·帕兹不由自主地举起双手,膜拜似的伸向她。
突然,萨拉惊恐地一下子蹲了下来。
等马丁·帕兹回过身来时,看到安德烈已站在了他的面前。
“谁定的这规矩,黑印第安人深夜还要祈祷?”安德烈恶毒地说。
“印第安人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必须如此。”
“那怎么你的同胞姐妹这时在山那里唱亚拉维歌、跳包列罗舞呢?”
“那是霍拉舞,”马丁·帕兹回敬道,“这种舞必须由两个彼此倾心的人来跳,而印第安人是最忠诚于心灵的。”
安德烈简直要气疯了,他慢慢地逼近这个镇定自若的对手。
“可怜的家伙!莫非给你们的自由太多了?”
“我看是把你们这群杂种惯坏了!”马丁·帕兹怒吼道。
很快两个对手都把匕首握在了手中。
两人身材相当,实力好像也相差无几,眼光在匕首的映衬下变得如此阴森可怖。
安德烈大吼一声,举手向马丁·帕兹刺去。马丁·帕兹不慌不忙,抬手前向一迎,两柄匕首相碰,发出刺耳的声音,迸出耀眼的火花。
马丁·帕兹顺势回手向安德烈头上刺来,安德烈无奈地滚开。但胳膊却被划了一道伤口。
“来人!……救命啊!”他高声叫道。
院子里一阵大乱,几个人打开门冲了出来。其中几个混血儿跑去救助安德烈,另外几个去追马丁·帕兹。但安德烈已经失去了知觉,而马丁·帕兹也已经逃远了,但仍有几个人追了上去。
“这是个什么人?”有人问道,“要是水手的话,最好送到斯皮利图·桑托医院去;要是印第安人,则要送到桑塔-安娜医院去。”
这时有个老人走出了门外,他挤进了人群,看到了昏迷的安德烈,大吃了一惊:
“快把这个年轻人抬到屋里去!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他就是萨米埃尔,因为他已经认出了自己的乘龙快婿,在未达目的之前,安德烈决不可以死去。
马丁·帕兹在夜色中一路狂奔,他想尽快甩掉追赶自己的人;他也只有拼命逃走,因为他已经成了一个谋杀犯!如果能逃到山里去,可能还有活命的机会。但他更清楚,城门在11点已经关闭了,到第二天凌晨4点才会重新开放。
他飞快地穿过了石桥,但是,迎面有几个士兵,向他跑过来,而后面追击的人带着巡逻队也一边叫喊一边向桥上跑来,越来越近了,现在马丁·帕兹已经进退两难了,他容不得细想,一个箭步跨过栏杆,纵身跳进奔腾的河流中,河底的石头碰痛了他。
两队人马在河的两岸追出了好远,想在他上岸时捉住他。
但他们的搜寻是徒劳的,他们始终没看到马丁·帕兹再露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