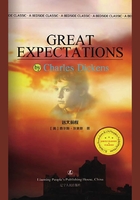第二天摩根到的时候,我还在睡觉。那急促、刺耳的门铃声把我惊醒。我从椅子上抓过一件开襟羊毛衫,披在睡衣上,一边揉着睡眼惺忪的眼睛,一边跌跌撞撞地下楼。
通过前门的玻璃我看到了摩根曼妙的身材。下意识地,我照了下门厅里的镜子。镜中的我头发乱蓬蓬的,昨天的妆容还脏脏地挂在脸上。我犹豫了一下,三心二意地用手指擦了擦脸,然后又用手拢了拢头发,试图将其弄得柔顺一些。
门铃又响了起来。
没有办法了。不管我怎么努力,我永远都没办法跟她一样。我叹了口气,把门打开。
尽管刚从大西洋彼岸飞过来,她看上去还是非常迷人。她身穿一件合体的、镶有真毛皮的黑色外套,脚穿黑色和米色相间的中跟鞋,手拎真皮提包。她那整齐的黑发也是一丝不乱。门前台阶上放着两只巨大的衣箱。
“简,亲爱的。”摩根边说边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你看上去真美。”
她并不善于撒谎。说这话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的眼睛因为我的形象而睁得大大的、充满恐惧。这就是摩根。她总是会流露出自己的优越感,即便她想努力地表现得友好和热情。这种个性让人不安,我想我能部分地解释这个年近四十二岁的女人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男朋友能交往三个月以上。
“我刚醒来,昨晚睡得不太好。”我解释道。
“哦,不。”摩根的声音柔和,充满关爱。“我很抱歉,但是我确实告诉过你我到达的时间……”她看了看自己精致的镶钻手表,“是十点以后。”
“我知道。”我说着,把开襟羊毛衫裹得更紧了一点。衣领上还有小块鸡蛋的污渍。哦,上帝!
“晚会的事情准备得怎样了?”摩根愉快地说着,走进门厅。她往后看了看自己的衣箱,还摆在台阶上。
在摩根爱丁堡的家、或者是玛莎的葡萄园、或者是托斯卡纳、或者其他任何一家她常去的高级宾馆,总是会有人帮她运行李的。
“晚会计划得很顺利。”我跨过门槛,把摩根的两个箱子拖了进来。阿尔特之后会拿上楼的。
整整一天我都觉得胸口郁结,但是我没有时间去想昨晚是什么事情让我整晚都没睡着。摩根说她想帮忙,但是事实上她不停地在提出要求:“你有纯果汁吗?我不想打扰你,但是你真的买了足够多的烤面包吗?我看你冰箱里没有什么冰,需要预订吗?你能告诉我你的毛巾都放在哪里吗?很抱歉我想换一条,我的皮肤非常敏感……”
接下来,电话就一直响个不停。大多数都是朋友打来的,确认晚会的细节,询问到达的时间或者他们是否需要带什么东西。我从厨房来到餐厅,那里的酒瓶从地板一直堆到了天花板,我想知道该做什么、该从何处着手。
大概三点的时候,海恩刚到不久,摩根就上楼了。南森跟朋友在一起玩,因此海恩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帮我准备晚会。我在找去年圣诞节用过的小彩灯,打算挂在客厅的镜子上。而海恩热心地去车库的储藏间取薯片。她没有再回来。十分钟后,我开始担心她是不是被花园里的家具或者是车库里的什么东西绊倒而受伤,于是我开始找她。
还没见到她的人,我就听见了她的声音。她就在杂物间里打电话。她的声音低沉,似乎在预谋什么。
“我知道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她不愿意放手。”我呆住了。海恩的声音带着可惜与恼怒。“我试过要跟她说。”一阵停顿。“不,还没有。”
在我心里,困惑变成了愤怒和羞耻。我再也无法忍受。“海恩?”我大声叫道。
杂物间里的声音听不太清楚了。接着,海恩出来了,“对不起。”她转转眼珠,说,“干了点别的事。”
我张开嘴想要追问什么,但还是忍住了。她在跟谁说话呢?阿尔特吗?我不愿再想。
她走进厨房的时候,我什么也没说。但是海恩一直喋喋不休,轻松愉快,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我们把她从车库里拿来的薯片放到碗里,然后又一起把小彩灯挂起来。之后,我又回到厨房,而海恩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摆放蜡烛,并重新摆放客厅的家具以便有足够的空间“跳舞”。
看着她所做的这些,我忍不住笑了。我告诉她阿尔特讨厌跳舞。
海恩转转眼珠,说:“不要这么消极。”尽管她的声音很轻,但是有些尖刻,“我相信,如果你邀请他的话,他会跳舞的。”
我有些不安。她是不是觉得我对阿尔特有些不公平呢?她刻薄的语气跟我刚刚偷听她讲的“不愿意放手”有关吗?
很明显,海恩看到了我的不安。“对不起,简。”她挥挥手,似乎想把我俩之间紧张的情绪驱赶到另外的房间。“还有什么要我做的吗?”
我看了看四周。现在都快五点了。说实话,我得自己把其余食物整理出来。海恩带了乳蛋饼,其他的客人也会带菜过来。我只需要准备奶油蛋白甜饼和黑森林蛋糕就可以了——看来七十年代的主题还是不可抗拒的。海恩在厨房通常都是帮倒忙。而此刻我还感觉到了我们之间的距离,那种距离感只有在贝丝走后的第一年才有。
“我很好。只有沙拉需要准备了……如果需要的话,摩根会帮我的。”
“对的。”海恩转了转眼珠,“要知道她连碰都不会碰一下。”
“嘘!”我咧嘴而笑。
“哦,要知道我爱摩根。”海恩朝门口走去。似乎为了证明这一点,她朝楼上喊道,“再见,摩根。”但是没有回答。
“我想她应该是在浴室。”我解释说。
“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她会穿什么衣服。”海恩悄悄地低声说道。她指着放在较大箱子上那件镶毛的黑色外套说,“想想看,要做成那件衣服,得死多少动物啊?”
“嘘!”我再次责备她,并把她带到屋外。
我回到厨房,忙着准备蛋糕。不知不觉中就六点了,而我才把火腿和橄榄摆到盘子里。我觉得非常累,急切地希望能好好泡个澡。这时,摩根出现了。她盯着我那粗糙的指甲。我从冰箱门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天啊,这时的我比她刚到时显得更糟糕了。我还穿着早上的运动裤和T恤衫,头发乱糟糟地堆在头顶——脸颊上还沾有樱桃酱。
“最近一次试管授精进展如何?”摩根将手背在身后问道。“我很高兴你愿意重试。”
我感到非常惊讶,但尽量不表现出来。摩根对我的生活知道得比我想象的要多,这并不是第一次。阿尔特总是跟他姐姐讲我俩之间的事情;她肯定是第一个知道的人,而且我知道多年以前他就跟摩根讲过我们的失败经历。刚开始我很介意,后来也就释然了。年龄越大,我越是明白,特别是他的妈妈去世后,家人对阿尔特的重要性,而摩根和他的兄弟们都是阿尔特的家人。不管怎样,尽管摩根对我们之间的事情了解不少,但我肯定阿尔特不会吐露自己的真实感受。
“我们还在考虑这个。”我含糊地说,希望事情就此结束。
“对了。”摩根迟疑了片刻,然后伸出一只手。她的掌心放着一个小小的、银色的盒子。她走过来交给我。“我知道今天是阿尔特的生日,但是我希望把这个给你。”说话的时候,她的脸有点红,往后退的时候还轻微地耸了耸肩。
“呃,谢谢。”我支支吾吾地。这是一个包装非常专业的盒子,上面绑着细细的银丝带。我拉了拉丝带的末端,打开包装。解开盒盖的时候,我看了看摩根。她看上去非常不安,甚至有些焦虑。
盒子里是一只银色的蝴蝶。我把它取出来,简洁而漂亮。字母A和G缠绕在一起,在一个翅膀上熠熠发光。
“这是白金镶钻的。”摩根说,“我特意为你和阿尔特准备的。”
“太可爱了。”看着手镯,我低声说,“哦,摩根。”
我有些不知所措。多好的大姑啊!外表看上去直率而傲慢,但是内心深处却如此体贴入微。我抬起头。摩根的脸又红了,她把脸转向一边。那一刻她显得非常脆弱。
“这只蝴蝶象征着改变。我想它可能会帮助到你……”她停了下来。“我不是想对你施以恩惠,杰妮芙。但是我明白无法摆脱的那种感受。我想这个也许能帮助你,让事情发生些改变。也许即便是重新开始写作。”
平时真的很难感觉到摩根对我生活的关注,但是我真的被感动了,并发自内心地感激她的善意。我冲过去紧紧地拥抱着她。
“谢谢你。”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不用谢。”摩根的声音重新尖刻起来,她那瞬间的脆弱消失了。
她松开我。我往后退了一步,意识到摩根需要重新回到她的盔甲里。我把手镯戴到手腕上,将钻石的A和G朝外。
“我会永远记住的。”我说。
摩根耸耸肩。她的眼睛盯着那些还在厨房柜台上包装盒里的沙拉。我知道冰箱和食品柜里还有一些美味的菜肴,我还是感到无望和慌乱。我甚至有些讨厌自己。
摩根做事总是那么高效,满世界飞来飞去,还总是那么精致。尽管如此,她还能有时间送给我们如此细致周到的礼物。而我呢,从中午开始就在楼下忙着,到现在衣领上还沾着鸡蛋液。看着这间屋子,摩根肯定在想我到底整天都在干什么。
见鬼。
“如果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话,我打算去冲个凉。”她说。
我惊讶极了。如果她还没有冲凉的话,那刚才三个多小时她都在干什么呢?但是摩根已经不见了。等到她再下楼的时候,她穿着绸缎长袍,头发也梳成了大大的精致的卷儿。而我准备的食物也都装盘,放回了冰箱。客厅和厨房看上去相当整洁。我开始准备音乐,并点燃海恩之前准备好的蜡烛。
阿尔特随时会回来,客人们大概在二十分钟左右就会抵达。而我真的迫切地希望上楼洗漱换装了。可妈妈在这个时候不择时机地从澳大利亚打来了电话。
“你好吗,宝贝?”她柔声问道。
“很好,妈妈。你的假期过得还好吧?”
“棒极了,宝贝。”她说,“不过前几天,道格拉斯的肠道综合症又犯了,我的高尔夫比赛也一落千丈。昨天在后九洞的位置,我都快崩溃了……”她就这样东拉西扯地讲了好几分钟。我想要听,但是我的脑子里却在想别的事情。事实上,我和妈妈之间真的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她想的都是高尔夫和桥牌,以及什么颜色的窗帘跟她的新三件套衣服搭配。她从不读书,认为任何谈论与政治、哲学或者宗教相关的事情都是不好的习惯。她不能理解我为什么写小说——以及我为什么不再写小说。
尽管她从来都没有说过什么,但是我很肯定,她一直在私下里认为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阿尔特能如此容忍我。也许如果她有外孙的话,我们之间的关系会有所改变。但是,事实上,我们之间的鸿沟是不可弥补的。
当妈妈还在絮絮叨叨地讲述艾尔斯山以及昨晚与他们一起进餐的那对夫妇的时候,阿尔特回来了。我看到摩根向他飞奔过去。丝质长袍从肩膀滑落下去,露出了内衣窄窄的红色肩带。她打开臂膀让阿尔特拥抱她的样子使人产生一种占有欲。不,不是占有欲。是控制欲。这种感觉来自摩根一点也不足为怪,也许老姐和小弟之间就是这样吧。作为独生女,我对兄弟姊妹间的这种关系感觉既陌生又向往。在我的童年时代,在父亲去世前,我经常在花园里闲逛,幻想着自己的家庭。父亲喜欢听我讲我编造出来的兄弟姐妹。而妈妈总觉得我的想法稀奇古怪。
阿尔特轻吻了一下摩根的脸颊,从她的拥抱中挣脱出来。这是有一定原因的。阿尔特不希望被任何人所拥有。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无法真正理解他和他姐姐之间关系的原因。他们相差不到两岁。每个人都觉得他们之间非常亲密,但是有摩根在场的时候,阿尔特总是小心翼翼。当然他从来都不承认这一点。每次我提到这一点的时候,他总是那样看着我,觉得我不可理喻。摩根就是摩根,简,有一次他这样说,她有些尖刻,但是她的本意是好的。
他们在门厅里小声地说着话。阿尔特抬起头看着我,似笑非笑。那是悲伤的微笑。他看上去非常的疲倦。摩根拍拍他的胳膊,希望能吸引他的注意力。但是阿尔特没有再看她,径直走开了。我没有看见摩根的脸,但能感觉到她的背变得僵硬。她甩了甩她乌黑的头发,趾高气昂地走进客厅。
“阿尔特是不是很期待他的生日晚会呢?”妈妈在电话那头问道。
“是的,我想应该是的。嘿,说到这个,我得去做准备了。”我说。
“好的,你要让自己看起来很棒,能配得上阿尔特。”妈妈意味深长地说,“他工作那么辛苦。你应当更努力一些,亲爱的。这样他感觉会不一样。”
她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失败的妻子,仅能赚点零花钱而已,根本就配不上我的金龟婿?妈妈、摩根和海恩的话,让我觉得不只是一点点受伤;这对于晚会来说并不是最好的开端。
“好的,妈妈。”我真想咬她一口,可惜她在千里之外,而我最不愿的事情就是争吵。因此我挂断电话,朝阿尔特挥了挥手,上楼洗浴。
等我再下楼的时候,我听见摩根和阿尔特在客厅聊天。我不知道他们具体在聊些什么。他们并排坐在沙发上。我走进客厅,他们抬头看我。阿尔特笑着,显得非常放松。相反地,摩根看上去有些恼火。她仍然穿着长袍,手上举着两只看上去几乎一样的黑色鞋子。都是那种窄窄的、看上去非常精致的细高跟鞋。光看着这样的鞋我都觉得脚痛。
“你觉得怎么样,简?”她说,“我无法决定。”
我看了看阿尔特,他非常巧妙地转了转眼珠。我忍住没有笑。
“这两双都很漂亮。”我诚实地说。
“这双是‘玛诺洛斯’。”摩根举起其中的一只。“但是我又考虑是否穿这双。”她又举起另外一只鞋。“这是纽约一个新设计师的作品。你可能没听说过她,但是她在国内真的已经很有名了。”
我仔细地盯着这两只鞋看了看。第二只比第一只圆润一点,鞋头圆一点但鞋跟更细一些。
“正如我所说的,它们都很可爱。”我又看了一眼阿尔特。他正看着我,带着请求援助的眼神。他还穿着上班的服装。
“嘿,亲爱的,你应该去换换衣服了。”我边说边走到他身边,将手放到他的肩上。
“是的。”阿尔特感激地朝我笑了笑,起身离开。
那一刻,摩根看上去有些生气。但我不知道她是在生我的气呢,还是阿尔特或是她自己。然后她又笑了,尾随阿尔特离开客厅。
我深呼吸一口,仔细地端详镜子里的自己。
经过梳理的头发卷曲在肩上。刘海还是太长了一点,都遮住了眼睛。幸好有波比布朗和衰败城市的彩妆,它们让我看上去并没有之前那么憔悴。我上半身穿的衣服较为贴身,跟我的卷发非常搭配。但我相信,摩根肯定会说Gap的牛仔裤并不是最佳的搭配。
我侧过身来,看看自己稍微突出的肚子。怀孕之前,我的小腹非常平坦。我和所有的妈妈一样有妊娠纹,只是我没有孩子。很快这里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妈妈们,开口闭口都在谈论自己的孩子。我可能会跟朋友们讨论下工作;至少他们不会可怜我。我看了看表。晚会前的这个时候总是最糟糕的,因为你没有任何东西需要准备,但是一个客人都还没有到。
来的人够不够多呢?现在,我站在这里,等候朋友们的光临。我下意识地感觉有些紧张。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做了个鬼脸。这次规模并不太大。大约只有三十个人出席,吃些小吃、喝点啤酒。阿尔特在家里跟在工作时一样:他讨厌那些看上去或者感觉像是精英的人。
我听见阿尔特拎摩根的第二个箱子上楼的声音。我在想,摩根到底是如何看待我的呢。表面上,她总是带着微笑并发出赏识的声音,但是我怀疑她打心眼里认为阿尔特应该可以做得更出色。阿尔特在很多方面都再现了他们父亲的职业生涯——但是在女性方面,他的选择截然不同。
布兰登·瑞恩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格拉斯高。他很少在公共场合提及自己的童年,但是从我所读过的文章以及摩根提及的只字片语,可以看出那是相当野蛮的教养方式。小的时候,布兰登经常被父亲打,还经常挨饿。十八岁的时候,他切断了与家庭的一切联系,在20世纪60年代初来到伦敦,决定在这里创业。他是个天生的企业家——五年之内成为百万富翁,去世之前成为亿万富翁。他有三个孩子——摩根和两个弟弟——他的妻子是一位非常漂亮的社会名流,名叫费·莱汉姆。我没有见过费。她和阿尔特相处得不是太好。
孩子还小的时候,布兰登和费举家迁到了爱丁堡,但布兰登的工作时间大多在伦敦。他就是在伦敦遇见了阿尔特的妈妈——安娜。据我所知,布兰登在生意场上相当无情。那时候,摩根还不到两岁,她的第一个小弟弟才刚出生,——据我猜测——他很有可能是感觉在家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他在一家豪华俱乐部遇见了在那里做服务员的安娜。那时,安娜野心勃勃地希望能成为一名演员。据阿尔特所言,那时布兰登曾暗示安娜他可以在事业上给予她帮助。那时的他正处于青年鼎盛期——样貌姣好,眼光犀利。即便在照片里,你也能感受到他散发出的那种力量。脆弱、天真的安娜没有能够幸免。即便二十年后我遇到她时,她的前额上似乎还刻着“俘虏”二字。
安娜怀孕的事最终被费知道了。布兰登给安娜钱去做流产,但是安娜断然拒绝——这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勇敢地面对他人。我想安娜如果能够圆滑地处理这件事的话,她肯定能从布兰登那里拿到一大笔钱。但是最终,整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布兰登什么也没有给她。费支持自己的丈夫,条件是布兰登必须与安娜和孩子断绝一切联系。
十八岁的时候,阿尔特前去找寻他的父亲,但布兰登显得非常冷漠和无情。阿尔特极其不愿意谈论这次见面。事实上我都是从摩根那里听到的有关情况。阿尔特到了门口,布兰登拒绝让他进屋。当时的气氛非常紧张,摩根在平台上目睹了这一切。阿尔特离开了,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摩根跟着他跑出房子,他们在街上交谈了一会儿。我多次问过阿尔特与父亲之间摊牌的事情,但他只跟我讲过一次——那是在我们婚礼的前夕——他告诉我那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刻。
在他们唯一的会面后不久,布兰登就去世了。意料之中,阿尔特根本没有出现在他的遗嘱里。尽管摩根极力恳求,费还是认为不应当给阿尔特一分钱。不过,阿尔特告诉我说,即便他能继承一定的遗产,他也不会要;他“不会让那个冷血的畜生得到满足”。在心理医生看来,显然布兰登的断然拒绝是阿尔特驱动力和野心的根源。但阿尔特拒绝承认这一点。无论如何,他都不愿意承认父亲对他产生过任何的影响。
“简?”阿尔特在楼上喊道,“简,你看到我的黑衬衣了吗?”
我叹了口气,转身离开镜子。这时,门铃响了,我们迎来了第一位客人。摩根的生气与恼怒、阿尔特工作后的疲惫也许就注定了今晚将是一个漫漫长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