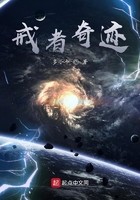档头正颜点点头,在一众牢头引领下来到庭院尽头那扇漆迹斑驳的小门前,小门同样虚掩着,里面传出鬼哭狼嚎凄厉的惨叫声。
档头扭头又瞧了一眼神情有些恍然的朱寿,至于被朱寿搀扶,已没了人色,两腿软的直往下出溜的江禄,压根都不屑于瞧上一眼。
档头嘿嘿笑道:“瞧好汉的神色是猜出来了,不错,门后面就是咱们东厂的点心房,一会儿进去用点心时,好汉可千万别让本官失望哟。”
朱寿淡然一笑,没有说话,手上微使劲将闻言惊吓欲死的江禄提溜了起来。
一名牢头急忙推开小门,满脸谄笑,躬身相请。
档头带着朱寿二人进入门内,门内是呈长方形狭长逼仄的庭院,左右两厢的房子都使用大块青石抹缝建造,由于只有狭长的过道在正午能射下一线阳光,因此青石墙壁和两溜墙角都长得厚厚的苔藓,整个狭长逼仄的庭院内散发着浓烈的霉味和刺鼻的血腥气。
东厂总部没有监牢,他们历来只负责对进到这里的人犯审讯上刑,至于审完人没死,是关刑部大牢还是镇抚司诏狱,他们才懒得cao那份心。
甫一进到院内,两耳就立即被两排房内传出的清晰惨叫哭嚎哀求声灌满了耳朵。朱寿瞧着除了左侧头一二间同样漆迹斑驳的竖棂糊纸房门是敞开的外,其他房间的门都是关闭的。
头一间房内传来牛八愤怒的咆哮声,档头引着朱寿两人向第二间房走去,经过头一间房门,朱寿扭头向里瞧去,浓烈刺鼻的血性臭气席卷而出,剧烈的撞击着朱寿的嗅觉和感官神经,双目随即一眯,吃惊的停住脚步。
房内牛八和他的管家以及护卫都被绑在原木刑具上,三名上身精赤肌肉发达,大汗淋漓的东厂番役,喘着粗气站在三人面前,手里都攥着探着细密倒钩的蟒皮软鞭。
牛八三人身上的锦袍都已经被鞭子抽的破烂,血渍已将锦袍染成了血袍,管家和护卫都低垂着头,似乎是已昏厥过去。
只有牛八依旧有精神高声痛骂着:“张锐你这条没卵子的yan狗,竟敢对本公子动刑,你有种今儿就弄死我,要不然等本公子出去,我他娘的非弄死你!”
朱寿的肩膀被拍了一下,朱寿醒觉扭脸瞧着档头阴森的笑脸。
“别着急,已经到地了,一会儿就给你上点心。”
张禄使劲推开朱寿,扑通跪倒在地,叩头如捣蒜,哀嚎道:“饶命啊大人,小的冤枉啊,小的并不认识他们,都是这人与他们有旧,小人是被他无辜拖到这是非中的,不干小人的事,还请大人明察啊!”
“干不干你的事,进去吃了点心就知晓了,你他娘的给老子进去。”档头狞笑着一把揪起哭的鼻涕眼泪一把的江禄,一脚踹进第二间房内,转而狞笑瞧着朱寿。
朱寿微笑一脸淡然迈步走进房内,可心里却掀起剧烈的狂澜,怎么会这样,他们竟然对牛八动了刑,难道我的判断有误?!
档头狞笑着正要迈步进房,余光一闪,张锐背负着手似笑非笑的站在身旁,脸上瞬间堆满笑意,翻身跪倒:“张串给四叔叩头。”
张锐瞧着一年前从老家跑来投奔自己的这个出了五服的远房侄子,脸上露出满意之色,迈步进了房内,档头张串急忙爬起,快步跟了进去。
张锐扫了一眼跪伏在地那两名事先安排好的番役,瞧向朱寿。
江禄又扑通跪地,叩头如捣蒜,哭嚎道:“厂公大人,小的真是冤枉的,是他,全是他结交匪类,将小的拖下水,今儿的事与小的没有一丝牵扯,小的冤深似海,求厂公爷明察啊!”
张串快步过去,搬着一把圈椅,服侍着张锐坐下,转身快步出去。
张锐从进来瞧都没瞧江禄一眼,面带玩味的笑意看着朱寿,慢条斯理问道:“你叫朱寿?”
朱寿抱拳躬身:“厂公大人,小民朱寿有一事不解,凶徒当街杀人,小民出手阻止,依大明律,小民此举不但无罪,反而有功,不知厂公大人为何要将小民带到这里。”
张锐嘴角那抹玩味笑意越发浓了,淡淡道:“小民?身为保安卫驻东八里堡的小旗,你这样对本督回话很不诚实。”
朱寿一愣,惊疑的看着张锐,耳旁听着隔壁牛八的高声痛骂,难道是他的管家说出的?
张串端着一盏茶快步进房,满脸堆笑奉给张锐,张锐接过茶盏,揭开盖碗,瞧了一眼,脸上露出满意的笑意。
一旁小心察言观色的张串立时眉开眼笑,躬身立在张锐身旁。
张锐轻轻拨动着盖碗,问道:“你进京所为何事?”
朱寿沉默没有说话,脑子飞快地转动,难不成自己和江禄被带到东厂刑房并不是因为棋盘街命案,而是刘瑾让他……
朱寿脸色微变,手慢慢轻碰破长衫内的短刀。
张串谄笑道:“四叔,这瘪三很会装相,你将他交给侄儿,侄儿保证上碟小点心,他立马就会将他祖宗八代惟恐不细的全抖搂出来,甚至他爹娘是否偷人他都会一五一十说个详细。”
盖碗轻落,精美的景德镇官窑白底青花细瓷茶盏发出清脆悦耳的撞击声,张锐眼角轻颤,眼中闪过一丝阴厉和难过,抬眼似笑非笑的瞧了一眼张串,淡淡道:“串子,有多久没往家里捎银子了?”
张串一愣,谄笑道:“上月的月银除了留些零花,都托人捎回去了。”
“你是个孝顺之人,你这就去掌房支五十两银子捎回家去。”
张串惊喜的翻身跪倒:“侄儿替家里的老娘谢四叔。”
“去吧。”张锐揭开盖碗,轻吹着茶汤,张串兴奋的站起身,快步出了牢门。
张锐轻呷了一口茶汤,沉默了片刻,轻叹了口气,莫名其妙的说道:“就是有心抬举,可没这个命也是白搭。”
跪伏一旁鼻涕眼泪一把脸无人色的江禄瞧着刚才一幕,脑子立时一清,急忙伏地说道:“厂公大人,小的江禄是保安卫指挥佥事江彬的亲侄子,求厂公大人看在我叔叔为国守边的微功上,饶过小的吧,小的真是冤枉的。”
张锐恍若未闻,抬眼瞧着微蹙眉沉思的朱寿,淡淡道:“你就是不说,咱家也知晓你进京是干什么来了。你放心,咱家不是因为这事难为你,毕竟刘公公的面子咱家是要给的。”
朱寿一愣,惊愕的抬眼观察张锐那张淡然的脸,揣测他这话的真实性。
张锐一笑:“到了这,你认为咱家有必要戏耍你吗?”
朱寿默然片刻,抱拳道:“以厂公大人的权势地位,确实不需对朱寿说假话,朱寿斗胆敢问,您将我二人带到此处,究竟为何?”
“这事嘛,很简单,咱家也不妨跟你明说,你二人还真是受牛八公子的牵累。”
江禄闻言猛地回头,怨毒无比的瞪着朱寿。
张锐轻蔑的瞟了一眼江禄,微笑道:“牛八公子与咱家有笔钱财上的过往,他借了咱家五千两银子,说好了,一个月内还,可到日子了,咱家却找不到他人了,他家门槛高,咱家不好前去讨要,因此一直打发手下人盯着,可前脚瞧到他出了府,后脚他就没了踪迹,大半年了,他就这么和咱家玩捉迷藏,要不是今儿发生这事,咱家恐怕依旧满世界逮他呢。”
张锐呲牙一笑:“你也都瞧到了,他如今是咬了牙不还咱家的银子,咱家想来想去,只能在你们身上下些功夫了。”
朱寿听着隔壁传来的软鞭噗噗抽打的沉闷声响和牛八声势不减的高声叫骂,隐隐觉着哪里有些不对,可急切间又想不出问题所在。
张锐脸上的淡笑消失了,幽幽的说道:“怎么着,不愿帮咱家这个忙?”
江禄急怒的瞟了一眼微蹙眉沉思的朱寿,你他娘的这时候装的什么傻,还不快回话。转而惊恐的偷瞧了一眼脸色越来越阴沉的张锐,惊骇中也顾不得了,冲着朱寿轻咳了一声。可不曾想,朱寿恍若未闻,依旧沉思着。
张锐嘴角绽起狰狞的冷笑:“既然这么不给面子,那咱家也只好得罪了,来啊,先给那坨鼻涕尝点小点心。”
“厂公爷不要……”
江禄的惊叫被卡在后脖颈如钢钳的大手捏的立时没了音,翻着白眼,如同一条被拽的死狗提溜到挂着血迹斑斑铁环的原木架子刑具前。
两名番役一人将江禄的左脚插进架下角的铁环内,另一只脚则被抬起与肩高,插进右侧架上挂着的铁环内。
另一名番役边将江禄的双手拉直套进铁环内,边满脸诡异阴森的笑道:“小子,知晓要尝的小点心叫什么名字吗?爷告诉你,叫蚂蚁上树。”
瞧了一眼惊骇的已说不出话的江禄,抬手拍了拍江禄的脸颊,从怀里抽出一团满是血污的牛筋,牛筋的一头绑着一根中指长铁针,边弯腰将牛筋的另一头绑在左脚踝处的铁环上,边嘿嘿笑道:“什么叫蚂蚁上树呢,就是将绑在你脚踝铁环上的这根牛筋从你的一颗蛋穿过,再绑在你高举的右腿上,然后再这么轻轻弹拨这根牛筋,那滋味就如有一群蚂蚁上下爬动,麻酥酥,实在是神仙的感觉,这滋味你这辈子都会回味无穷的,嘿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