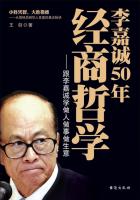“你看!”鼹鼠说,“他们会说话。有谁听说过会说话的莴苣?”“也许他们是第二个笑话。”寒鸦提议说。
一头本来正在洗脸的美洲豹,暂时停下爪子,说道:“好吧,就算他们是,也没有第一个笑话那么好笑。至少,我可没看出来他们有什么可笑之处。”它打了个哈欠,又接着洗脸。
“哦,拜托了。”迪戈里说道,“我有急事,想要见那头狮子。”与此同时,车夫一直在努力地吸引草莓的目光。现在他做到了。“嗨,草莓,老顽童。”他说,“你认识我的。你不会站在那儿,说你不知道我是谁吧。”
“马儿,那个东西在说些什么?”几个声音一起问道。“哦,”草莓非常缓慢地说,“我也不太清楚。我想,我们大多数对一切事物都是一知半解。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我从前见过这样的东西。我觉得,自己曾经住在另一个地方..或者曾经是别的什么东西..那是刚才阿斯兰把我们全都唤醒之前。一切都混在了一起,就像是一个梦。但是在梦中,有一些和这三个家伙相似的东西。”
“什么?”车夫惊诧地说,“不认识我啦?一天晚上,当你身体不舒服时,难道不是我给你端来热土豆泥?难道不是我为你进行彻底的刷洗?当你站在严寒之中,难道不是我记着给你盖上一块布?我没有想到你会这样,草莓。”
“我确实开始想起一些什么。”那匹马沉思着说,“是的。让我想一下,让我想想。不错,你过去总把一个可怕的黑东西拴在我的身后,拿鞭子抽我,逼着我跑快,不管我跑多远,这个黑东西总是嘎嘎响着紧跟在我后面。”“我们必须赚钱来谋生,明白吗?”马夫说,“我们俩的命运息息相关。如果没有工作和皮鞭,就不会有马厩、干草、土豆泥和燕麦。当我买得起燕麦的时候,你确实吃到过燕麦。没有人能否定这一点。”
“燕麦?”马竖起了耳朵说道,“是的,我想起了关于燕麦的一些事情。的确,我回忆起越来越多的事情。你总是坐在后面,而我总是在前面奔跑,拉着你和那个黑色的东西。我知道是我干了所有的活儿。”
“在夏天,你说的没错,”车夫说,“你顶着烈日干活,而我却坐在阴凉的座位上。但是冬天呢?老顽童,你能奔跑使自己暖和,而我却要坐在那里,两只脚冻得像冰块,寒风几乎要把我的鼻子冻掉,我的手冻僵了,几乎握不住缰绳。”
“那是一个艰难而又残酷的国家。”草莓说,“那里没有草。到处都是坚硬的石头。”
“太对了,伙计,太对了!”车夫表示赞同,“那是一个艰难的世界。我总是说,那些铺路石对马儿太不公平了。那是伦敦,就是那个地方。我跟你一样不喜欢它。你是一匹乡下的马,我是一个乡下人。在家乡时,我还在教堂的唱诗班唱过歌。但是在那里我无法维持生计。”
“哦,拜托了,拜托了,”迪戈里说,“我们能继续往前走吗?狮子越来越远了。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同他说话。”
“听着,草莓。”车夫说,“这位年轻绅士有点儿心事,想跟狮子谈谈,就是你们称为阿斯兰的那头狮子。希望你能让他骑在你的背上(能这样做他会很开心的),驮着他跑到狮子那里去。我和小女孩在后面跟着。”
“骑?”草莓说,“哦,我想起来了。那是要坐在我的背上。我记得,很久以前有一个两条腿的小家伙这么做过。他经常给我吃一些硬硬的白色小方块,尝起来..哦,很美妙,比草甜多了。”
“啊,那一定是糖块。”车夫说。“拜托了,草莓,”迪戈里乞求道,“求你,求你让我骑上去,把我带去见阿斯兰。”“好吧,我并不介意。”马儿说,“偶尔骑一下没有关系。上来吧。”“好心的老草莓。”车夫说,“来吧,年轻人,让我来帮你一把。”迪戈里很快就骑到了草莓的背上,感到非常舒适,因为以前他骑自己的小马驹时从未用过马鞍。
“好了,出发吧,草莓。”他说。“你身上是否碰巧也带了几块那种白色的东西,我想知道?”马儿问。“不,我恐怕没有。”迪戈里说。“好吧,那也没有办法。”草莓说道。于是他们就出发了。一条大看家狗一直在嗅来嗅去,此刻它瞪大眼睛说道:“看了!那儿不是还有一只这种奇怪的动物..就在那里,在河边那棵树底下吗?”
所有的动物都朝那边望去,看到了安德鲁舅舅。他正一动不动地站在杜鹃花丛中,希望不要引起大家的注意。
“来吧!”几个声音同时嚷道,“让我们去看个究竟。”当草莓驮着迪戈里,轻快地向东方跑去的时候(波利和车夫徒步在后面跟随),大多数动物朝着安德鲁舅舅冲了过去,嘴里发出咆哮、吠叫、哼哼声,以及各种表示快活与兴奋的声音。
现在我们必须返回头去,解释一下安德鲁舅舅是如何看待这一切的。所发生的事情给安德鲁舅舅留下的印象,与车夫和孩子们的印象截然不同。因为你的所见所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立场,还取决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自打动物们从土里钻出来,安德鲁舅舅就一步步地退缩,一直退到远处的灌木丛中。当然他也在竭力地观察它们,对于它们在做些什么,他丝毫也不感兴趣。他只是关注着它们是否会朝他冲过来。像那个女巫一样,他也非常实际。他根本没有注意到阿斯兰从每一种动物中拣选了一对。他所看到的,或者说他自以为看到的,只是一大群危险的野兽茫然地走来走去。他始终困惑不解:为什么其他动物不逃离那头大狮子呢?
在动物们开始说话的伟大时刻,他根本就无法理解,这是出于一个相当有趣的原因。一开始,当这里还是漆黑一团的时候,狮子开始唱歌。他意识到这声音是一首歌。他非常厌恶这首歌。这歌声使他想起了一些自己不愿意回想的事物,感受到了一些自己不愿意感受的东西。后来,旭日东升,他看出来歌者是头狮子(“只是一头狮子。”他自言自语道),他更加努力地使自己相信,狮子并不是在唱歌,并且从来都没有唱过..它只是像我们的世界里动物园的狮子那样在咆哮。“当然它不会真的是在唱歌。”他想,“那一定是我的幻想。我肯定是神经错乱了。有谁听说过狮子会唱歌呢?”狮子唱得越久,越是动听,安德鲁舅舅就越发努力地使自己相信,除了咆哮之外,他什么都没有听到。问题是,当你尽力使自己变得更加愚蠢的时候,你往往可以成功。安德鲁舅舅就做到了。很快,他从阿斯兰的歌声中听到的只有咆哮声,即便他愿意,他也无法再听出别的声音了。最后,当狮子呼喊“纳尼亚,醒来吧”的时候,他一个字儿也没有听到,只是听到了一声低吼。当动物们回应时,他听到的只是狺狺声、咆哮声、低吼声以及嗥叫声。当动物们哄堂大笑时..好吧,你可以想象一下,对于安德鲁舅舅来说,这简直是糟糕透顶。他这一辈子从未听到过饥饿和愤怒的野兽发出如此恐怖而嗜血的喧闹声。令他感到极大的愤怒和恐惧的是,那三个人居然走向草地,去见那些动物。
“傻帽!”他自言自语道,“那些野兽会把孩子们连同戒指一起吃下去,我再也无法回家了。迪戈里真是个自私的孩子!那两个人也一样坏。如果他们不要命,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可是我该怎么办呢?他们似乎没有想到这一点。没有一个人为我着想。”
最后,当成群的动物朝他冲过来时,他转身就逃。这会儿,任何人都能看得出来,这个年轻世界的空气对老先生真的大有益处。在伦敦,他原本衰老得跑不动路。此刻,他奔跑的速度能使他成为英国任何私立小学的百米跑冠军。他身后飞舞的上衣后摆是一道不错的风景。当然他的逃跑是徒劳的,在后边追赶的动物大都身手敏捷。这是它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赛跑,都渴望能够用上自己全新的肌肉。“追上他!追上他!”它们大喊大叫,“也许他就是那个鞋领!嗬.嗬!跑快点!拦住他!围住他!加油!好哇!”
没用几分钟,有一些动物就超过了他。它们排成一排,挡住了他的去路。其他动物从后面将他包围起来。不管往哪儿看,他看到的都是恐怖景象。高大麋鹿的鹿角和大象的巨大面庞高耸在他的面前;笨重迟钝的熊神色专注;野猪在他背后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镇静自若的花豹和黑豹带着嘲讽的表情(他是这么认为的)盯着他,摇着尾巴。最令他恐惧的是无数大张着的嘴巴。其实,动物们只是在张着嘴巴喘气,他却以为它们张开血盆大口要来吞吃他。安德鲁舅舅站在那里,浑身颤抖,摇来摇去。即使在身心状态极佳时,他也从来没有喜欢过动物,通常都很怕它们。这些年来,在动物身上进行的残酷实验,使他对它们的憎恨和恐惧有增无减。
“喂,先生,”看家犬用公事公办的口气说道,“你到底是动物,蔬菜,还是矿石?”对于它所说的话,安德鲁舅舅听到的只是“呜..哇..啊..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