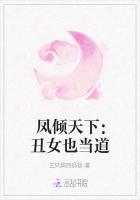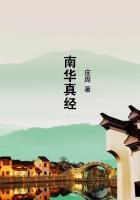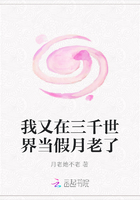去冬,寻访中轴线。穿过小街深巷,在地安门,我忍不住停下。有一年,也是冬天,也在这里,我采访过一家人。
“你好!”那天,衰老的男主人米勒靠在沙发里,对我微笑。他很虚弱,话语含混不清。可他淡蓝色的眸子闪烁着热情的光。
1933年,18岁的德国犹太人米勒为躲避纳粹追杀,出走瑞士,在那里,修完医学博士学位。1939年,他作为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成员,肩背药箱,转战大半个中国,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了无数中国战士的性命。
“抗战八年,他打了六年!”米夫人笑吟吟地端来茶。
我知道,米夫人是中医师,日本血统,名叫中村京子。1944年,中村正在日本念中学,为战争来到中国锦州满铁护士学校学习。结果,赶上抗战胜利,八路军接管了满铁学校。正直的中村毅然参加了八路军。
我看着体态轻盈的米夫人,惊异于她的年轻。她伸出五个指头,翻了几番,满自豪:“我都55岁啦。”
有会没吭声的米先生得意起来,讲了一串话,可惜含混不清。米夫人赶紧翻译:“他是说,我年轻,是他管得好!”米勒顿时开怀大笑。
那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一次采访。也许因为我和他们儿女的年龄相近,我感觉无拘无束。
“我不明白,”我对米先生说,“您为什么不选择德国或日本,这两个毕竟有一方是你们故乡的地方,而留在中国呢?”
我想说,这里毕竟还穷还落后嘛。
米勒淡蓝色的眸子始终在微笑。中村则掰着指头数开了,一口汉话十分流利:“我们家人复杂呦,有德国血统、日本血统、瑞士籍、美国籍,还有香港人,总得有个根,有个大本营嘛,只有北京才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哪里离得开呢!”
于是,他们为我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米勒的确很想返回梦思萦绕的故乡。那是1945年,抗战胜利时。没想到,中国内战爆发了,交通封锁了,米勒只好留下来继续打解放战争。
刚巧,活泼漂亮的中村京子分到他的手术队当助手。米勒33岁人的心里一下子泛起了爱的涟漪,于是,他问中村:“咱们能不能……‘合’在一起?”17岁的日本女孩涨红着脸反对:“我还得回家呢!”米博士为此郁郁寡欢。
骨节儿上,组织帮了米勒的忙。那时的组织特别关注老干部的婚事,尤其关心白求恩式的洋大夫米勒的生活,中国人民的医疗事业需要米博士。
对日本女孩中村京子来说,后来的事情简直是设套。当中村领命赶往另一所医院报到时,正“巧”碰上了蓝眼睛米博士!
后来,他们有了一双儿女,迁进了北京城;再后来,儿女长大了。
女儿在大学工作期间,与一位瑞士籍教师相爱,嫁往瑞士;儿子则在美国留学期间,加入美国籍,娶了香港太太,成为英国公司驻京代表。
是啊,这一家人的根,茎蔓错落,生机盎盎,不留在北京的原土里,又移向哪儿去呢。
我在这座紧闭的绿漆大门院落外伫立。我知道,那位有着淡蓝色微笑的老人,那位在北京医学院辛勤工作了数十年的华籍德国人,已经辞世。
我没有勇气扣响那扇绿漆木门,心里一阵悲哀。
如今,那颗伟大的灵魂,就安睡在我们京城的土地下。他把他的生命,才华,他的妻儿,全都留给他挚爱的这片异族大地。
我突然记起,几十年前,清末皇帝溥仪的英语教师庄士敦,也曾经在这座绿漆大门院落内居住。
是的,外来文化早以各种形式,以傲慢的强暴、以雪中送炭的援助、以文雅的交流,走进京城,我们的故乡早成了一座东西文化交汇的现代城市。
我骑上车,重奔中轴路。
我想,东西南北,总还有个“中”吧,这中,是中轴线,是北京,是民族的魂。即使米先生的儿女,还有亿万客居他乡的同胞,又有哪位忘得了这个“中”?然而,沧海桑田,世事轮回,大千世界,哪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中”?我崇尚米勒,敬重所有像米先生伉俪那样以一己血肉之躯繁荣我们这座世界古城和整个民族的他乡客人。
我替我所在的这个老城祝愿,盼望上苍善待米先生,好人走后亦该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