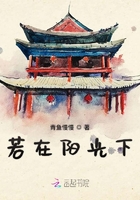穿越第五守则,亲们,要穿越得趁早,要不然,仙草级的男人被抢光了,神仙姐姐也在家奶娃了。
“我明明做的好事,凭什么说我错了。”崔云舒心里憋屈得慌,“我没罪我没罪。”她本觉得自己一个人被孤零零地扔到了这个与她格格格不入的世界,偏偏又事事不顺心,刚刚调整了心态,做了件融入这个村子的好事,就被这当权者一口否了,还判定为有罪,她需要发泄,不禁有些歇斯底里,她转了几圈,看到边上还空着两张椅子,上前操起来就砸到地上,“来,抓我呀,把我关监狱里去,这什么世界呀。抓我呀,这破地方我还不呆了,早死早回去。”
门口两个衙役听见动静,抽出腰刀就冲了进去。
“坏了。”远远看着的程夫人提溜起裙角,跟着跑了进去。看到崔云舒还要去拿另一张椅子,忙上前一把搂过她,死死抱住她。“云舒,云舒,别怕,莫姨在呢。”
那两个衙役横着刀护在县太爷和师爷身前,只等县太爷一声令下,怕是要提刀拿人了,
“大人,这娃儿在市集上遇上了坏胚子,受了惊吓。望大人恕罪。”程夫人边拍着崔云舒的背安慰着,边解释道。“哇”,崔云舒大声哭了出来。自父母出车祸去世后,她再也没有在别人怀里哭过。那县太爷虽然爱在老百姓头上摆谱,倒也没坏到骨子里,不耐烦地挥挥手,算是让她们退下了。
程夫人搂着崔云舒出来,崔云舒也哭够了,倒有几分不好意思,“莫姨,谢谢您,我先去洗把脸。等下我一定把场子给圆回来,不给您惹祸。”
程夫人点点头,“你去吧,别担心,我自有法子。”
那师爷看他们前脚刚出门口,便低声道:“大人,这大不敬之罪您就这么轻轻揭过了?”
县太爷怡然地靠在椅子上,摸着他的尖下巴,“回头让他家多交些税也就是了,总不过是个乡下小女子罢了。”
听得脚步声,县太爷抬了一眼,却见程夫人端庄大方地走了进来,与先前那胆小谦恭,唯唯诺诺的乡下妇人判若两人,与师爷对望一眼,这妇人好似不简单。
程夫人上前浅浅地敛了一礼,便于下首一把椅子上坐下,“袁大人,令尊的老寒腿可大好了?”
县令闻言暗惊,坐直了身子,肃然道:“家父安好,下雨时偶有不适。夫人与家父有故?”
“先夫曾与令尊是旧故同僚。”程夫人轻叹一声,“已然近二十年了,物是人非呀。”
“哦,未曾请教先生尊号?”县令说得恭敬,口气却是淡然。
“先夫程娄。”程娄原是北齐济州大中正,程夫人看了一眼那县令,似笑非笑地站起身,“民妇去备些酒菜,大人宽坐。”走到门口,程夫人回转身,笑道,“听闻御史道推荐孙道祖出任山东府台。”说罢,轻弹衣袖,施施然出了门去。
“哎呀,大人,那御史大夫可是程家子侄。”那师爷在一旁提醒道。
“你这狗脑子,不早说。”县令斥喝道。世族大家自可以打杀了被逐出家族的族人,但却绝不容许外姓之人欺凌。何况这程氏母子未必是被逐出来的,或许只是家道中落而已。
县令很是懊悔。程夫人先与他攀交情,是自己太过倨傲了。
午饭席间,崔云舒上前陪罪,那县令自是宽言安慰,宾主相谈甚欢。这才知道,原来自从引水之事传开,倒有许多地方竞相效仿,有些富豪为显其豪阔,也不顾路途远近,也搭台引水,一时间各处支架林立,有碍观瞻不说,有些地方把路都堵了。崔云舒想了想,便提议县里统一规划,烧瓷管代竹管,埋地底引水,还可以收取一定水费。不愿出钱的还跟从前一样去井里打水或去河里打水。县令听了大喜。崔云舒负责画图和规划,因程夫人关系,袁县令为崔云舒出具官凭,可在此村落户。这几日,崔云舒用炭画好图,请程夫人帮忙写了细节,没办法,好多繁体字不会写,毛笔字本也写得不好。今天,她去县衙交了图纸,剩下具体执行师爷自会领着人去干,有油水可捞的事自然用不着她一个外人了。她领了县里的赏钱,高兴地坐着雇来的驴车往回走。走到半路,找了处草深林密的地方方便了下,正要走到路口,突然不知从哪蹿出个人来,一把尖刀抵住她的脖子,崔云舒吓坏了,从没遇到过绑匪的她只觉得两腿发软,要不是那匪徒拖着她,她早软倒在地了。
“放开她。”低沉的声音有些清冷,似远远传来,但眨眼间,那人已到跟前。那人穿着捕快的衣服,手拿着一柄普通的长刀,整个人却如一杆长枪,挺然而立,长得极为英俊,长眉入鬓,眼若寒星,鼻如悬胆,棱角分明,嘴角微微翘起,似乎总带着温和的笑意,使得整张脸也柔和起来。
那匪徒整个人躲在崔云舒后面,刀却不离半分,显见他对来人很是忌惮。“秦捕头,你已追了我三天三夜,我已无力再逃,你若不放过我,我不介意手上再添一条人命。”
那捕快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崔云舒望着他平静的神情,心也是安定了下来,她悄悄地把手伸进衣袖里,朝秦捕头眨了眨眼。“好,我可以让你先走两个时辰。”
崔云舒心下一紧,这个笨蛋,怎么不答应放了他,这下他还不拼个鱼死网破。却不料,那人听他如此一说,立即放开了她,收刀就向后退去。崔云舒抽出电棍,按下电源开关,向他身上胡乱挥去,那人见是棍子,伸手来挡,浑身一颤,倒在地上,还全身抽抽,已经晕过去了。这下用了最大电流,心疼死了,崔云舒心下愤愤,这电是用一次少一次呀。看来得学几招防身术。
那捕快看了眼地上的匪徒,又看了下她,似有些奇怪,又看了下她手中的棍子,才温和地笑笑:“多谢姑娘援手。”
那一笑,如春风吹拂了心田。崔云舒脸霎时红了,手心竟有些细汗,“不用谢,不用谢,不,不,我该谢谢你的。”
“此人很是凶狠狡诈,我得先把他送交官府收监才好,就此别过,姑娘一路好走。”拱手施了一礼,提起那匪徒,转身便去了。
崔云舒怔怔地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下自嘲道:“崔云舒呀崔云舒,春天虽然来了,你竟连话也说不利索了,丢人呀。亏你还是个现代人,连个名字也没问出来。”慢吞吞地朝远处的驴车走去。
第二日,神情萎靡的崔云舒很晚才走出房门,有气无力地唤了声,。“早啊,程大哥。”
“俺正要去叫你吃午饭呢。崔家妹子,身上可好些了?”程咬金随口问了声,并不等她回答,高兴地接着道,“俺家来客人了,你猜是谁?是俺兄弟。俺们打小一起玩的,有好多年没见了。”
“哦,”崔云舒淡淡地应着。说话间,便来到正堂。却听得一个声音温和而恭敬,“回程姨,小侄不能多呆,母亲身子不大好,我想着赶回去带母亲去京城瞧瞧名医。”
崔云舒一愣,伸头往里看了一眼,真是他,那个秦捕快。程咬金在身后轻推了她一下,“进去呀。”
崔云舒一把抓住他,把他拖到院子里,“快说,那人是谁?”
“你说俺兄弟?”程咬金看着面色潮红,眼冒星星的崔云舒,不禁有些担心,“你没事吧,看你脸通红通红的,莫要烧糊涂了。”
“快说呀。”崔云舒急了。
程咬金看着她急切的神情,有些奇怪,“他叫秦琼,字叔宝。你认得他?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秦琼,秦叔宝,难怪……”崔云舒拍拍胸口,镇定下情绪,“他有老婆吗?”
“啥?你说啥?”程咬金更不理解了,“你真认识叔宝?”
“他娶妻了吗?”崔云舒打马虎眼,“我好象认识他。”
“娶了,娃娃都生了。”
崔云舒只觉眼前一暗,咯嘣一声,心轻轻地裂开,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