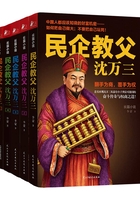然而正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他静静地盘腿坐在我的阳台上,衣衫褴褛,也许是不知哪儿来的流浪汉,借这个地方过夜。我不太高兴地走过去气冲冲地告诉他:“喂,是我先来的。”他对于站在他面前的我无动于衷,反而气定神闲地说:“这是我家。”我恼怒却又不知道怎么把他赶走,推也不是,拖也不是,我就这么着急地来回踱步,“你凭什么说这是你家呢!”“那你凭什么说不是呢?”我被他问得无话可说。在我之前,有很多建筑工待在这里,这里大概是他们的家;再之前,在楼还没开始建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个什么鬼地方。等它变成了一栋无名之楼,谁都可以来这里认领一寸空间,我凭什么而你又凭的是什么呢?其实所有的凭证都是虚幻的,这个世界似乎就是这样,所有的空间,包括土地、房屋,等等,尽管人们用尽方法满足并强调自己的拥有感,但实际上从来没有哪怕一寸是完全属于一个人的。
我环顾四周,在他与我所占据的房间中央用修正液从地上一直到墙上,甚至我还想一直到天花板——可惜我不够高——画了一条界线。我用这种方式强调了地盘的划分,强调了这种拥有感,却也同时觉得若有所失。我把怅惘挥散,重新摇了摇修正液,用这支本应用来修正和覆盖的东西来书写与创造我幻想中的家。
“我的修正液呢?”几天之后豆芽找我要回她的修正液,我才发现我把它落在了烂尾楼里,“我重新给你买一支吧,你的被我弄丢了。”“好吧,过几天考完试就放假了,你要不要回家?”“要啊,但是我不能跟你一起坐车。”要是被我妈撞见了,我大概就要编一个类似“豆芽来机场接我了”的破借口。
我一推门就听见客厅里我妈跟另一些女人的笑声。我放寒假回家没有跟我妈说是哪一天,免得她自作主张跑到机场来接我。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恰好碰上有客人来访的时候。我妈看见我回来了赶紧迎上来,我把行李箱抬进来,示意不用帮忙。经过客厅的时候我仔细看清了其中一个女人。她应该比我妈年长几年,不知是不是因为有点儿发胖的原因,她的皮肤充满了光泽,我注意到她微卷的短发下面,有一对非常宽而厚的耳垂儿。她一开口就把我震住了——她有一把非常洪亮的嗓门儿,“哟,面条儿,回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