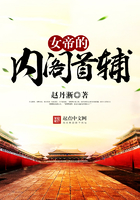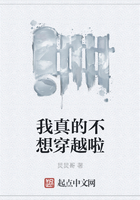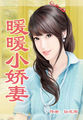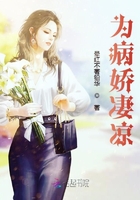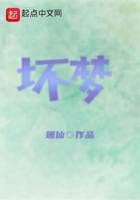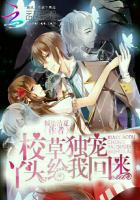扬雄一生淡泊名利,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他在辞赋、儒学等方面都取得了极高成就,学问渊博为西汉一代之冠。仕途淹滞司马相如之后,西汉一代在辞赋上成就最高的就是扬雄。扬雄字子云,和司马相如一样也是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在武帝元朔年间(前128~前123),扬雄的祖上由江州溯江而上迁往成都时,司马相如已经死去,但这并没影响青年时代的扬雄将司马相如作为学习榜样。他认为司马相如的赋华丽温雅,每次作赋,常常模拟相如的名篇。
但和弱冠之年就入仕为官的司马相如相比,家世清寒的扬雄的仕途要艰难得多,但他并不以此为忧。扬雄口吃不善交谈,平日里只是研究经籍自娱,并没将学问作为功名富贵的敲门砖。直到40岁时,扬雄才游学长安,这时他的辞赋成就在汉朝士人中已经可称独步,大司马大将军王音读了扬雄的赋后,认为扬雄的才华可与司马相如媲美。后来经王音推荐,扬雄待诏承明殿,成了官秩不低的文职官员。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扬雄模拟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接连作《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对成帝进行讽谏。这四篇赋在意气风发、雄伟恢弘的气势上略逊司马相如一筹,但它们打破了赋为主客问答的陈套文体而自成一格,因此深为成帝欣赏,于是成帝封授扬雄为黄门郎。
潜心著述
这时的西汉朝廷暮气已现,大部分官员都把功夫用在交结权贵、钻营奉承之上,口吃的扬雄自然不会像他们一样指望靠阿谀奉承出头,置身事外成了扬雄唯一的选择。扬雄刚当上黄门郎的时候,正好与权贵王莽、董贤是同事。在此后时间里,先是王莽进位三公,然后王莽退而董贤进,最后王莽复起而董贤被彻底打倒。从成帝到哀帝再到平帝,几十年时间里,西汉朝廷犹如马戏团走场子一般来来去去地换,一大群人跟着王莽、董贤上上下下,而扬雄始终还是一个黄门郎,没有得到任何升迁。
经过几十年的官场经历,扬雄已经不再相信辞赋对君王有什么讽谏效果,他把自己前半辈子苦心作的赋统统丢掉,专力研究儒学。扬雄仿照《论语》作《法言》,仿照《周易》作《太玄》。当时学者桓谭看了他的著作后感叹道:“你这是白辛苦了,《五经》精通后可以获取功名利禄,现在的读书人尚且不愿用功研读,更何况你的这些东西!我只怕你的书将来只能被人家拿来盖酱缸子呀。”扬雄却笑而不答。
失节投新
王莽篡汉建新后,扬雄长期呆在寂寞冷清的天禄阁中校书,依然不主动接近政治。但以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即使本人无心政治,政治还是会找上门来的。这时王莽已经容不得扬雄依然作逍遥派了,扬雄无奈,只好作了一篇叫《剧秦美新论》的马屁文章,颂扬新朝功德。这篇文章因为辞藻华美被收入《文选》流传了下来,后来竟因此落下了“失节”的把柄,深受后世一些提倡节气的士人的诟病。南宋时朱熹曾作《资治通鉴纲目》,就严厉地将扬雄写作“莽大夫扬雄”,用以彰显扬雄叛汉投新。现在看来,对于失节的批判,扬雄自己大约也是无从开解的。但试想一个处在社会大变动的狂风巨流中任由政客摆布来摆布去的文人,要做到言行无污,真是谈何容易。
“失节”还是不能避免无妄之灾降落到扬雄头上。王莽代汉之初曾造了不少符命给自己造舆论,但他成功地当了皇帝后却害怕别人将来也如法炮制,因此下诏禁断符命。刘歆的儿子刘因为造作符命下狱,扬雄也因为当过刘的老师被牵连。在看到前来抓捕的官吏后,扬雄从天禄阁上跳下自尽,却还是没有摔死。最后还是王莽知道扬雄是个书呆子,不会参与这种事情,赦免了他,只罢免了他的官职。新朝天凤五年(18),扬雄去世,终年71岁。和扬雄同时的学者刘歆、桓谭等人都非常推重扬雄,桓谭说扬雄“能入圣道,卓绝于众,汉兴以来未有此人”。扬雄死后,有人问桓谭说:“你一生推崇扬雄,不知道他著的书能否流传下来呢?”桓谭回答说:“一定能流传,普通人贱近贵远,亲眼见扬雄一生禄位不能过人,自然不重视他,后世人必将更关注他的著作。”果然,《法言》大行于东汉,成为一代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