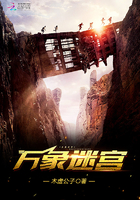也许我早该写点什么了,但也许是还没到该写什么的时间。当宣泄一通之后,这便也是该我的垃圾桶,但我是不愿意处理掉这些垃圾的,因为此时此刻的心情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在我未完成“此”前尚无定论,我不得而知。
时间过得很快,将它比作金钱的是那些有着大志大愿的人;将它比作利剑的是那些虚度了年华的人;将它比作流水的是那些感慨人生短暂的哲思者;而对于我,时间只是证明我还活着,证明我还在一天天的活着的工具,而它,不留情面,没有温存,总是沉默着,一日日,一时时,记述着属于你我的过往,直到永恒,冰封在过去。永远不能拿回,永远不能后悔,它是一个高利贷者,让你为你所付出的的承担着高昂的利息。而我们也许仅仅只是一部分人,却仍旧欣然借贷,直到有一天,突然之间发现,也许你因借贷而提前的幸福同时占领了你还债的比例,然后......我不知道然后将是什么样子。
今天的现在的是已经拥有的;而明天的未来的仍旧是个未知的问号。世界如此,人生如此,你也该如此,带着一肚子的问号继续借贷,直到有一天,在死神面前,将自己透支而来的幸福还给时间,带着他们追求的未来的渴求离开,终是没有得到什么啊!
说到这,可能有人觉得是无病**不知所云了,只是因为已经说得太多太多了。对于时间,我终究是无力的,不能做上些什么。而时间却可以将我们毫不费力地伸的很长很远。
我想我是忘不了那一天的,那也是我如今想来依旧心寒胆裂的一天,六年前的那个夏天,于我,一个极爱我的人离开了。第一次踏进殡仪馆,踏进告别厅,踏进火葬场,然后看着那个熟悉的陪我的人由早已经僵直的躯体最后化为母亲手中的那个盒子里仅剩的粉末,再到最后连盒子也放在野外墓地,只剩下一张相片。人都是自私的,呢时候的想法便是:再也不会有姥爷陪我。看吧,人就连伤心也是自私的,哭泣也不过是因为再也看不到姥爷,他再也不会在阳台上、厨房窗口伫立遥望离家的子女们......
而不得不提,时间很厉害,慢慢的将这一切都化作很淡很淡,是剩下偶尔的想起,模糊的记忆。
而两个多月前,时隔六年,我又一次重复了之前的经历,同样的步骤,同样的仪式,同样的地点,除了躺在那里的冰凉的人......
不得不提,心情,甚至是哭泣的原因也有了变化。这次,我很近距离的看着她,亲手触碰了那冰冷下的面容与身体,我身旁有很多的人,但我还是忍不住的害怕;身旁的人哭了,我也哭,那天我站在第一排,拉着母亲的手。当人们大踏步的离开告别厅的时候,我们将母亲拉了出来,最后母亲静静地看着她化为白烟消散在天空,消散在人间......
对着那个方盒,我问自己,为什么。
司仪主持行礼,我诚心诚意三个头磕下去,以头触地,然后我一边又一遍的哭,有人看我奇怪,我不理会。回来的路上,我还是一遍又一遍的问自己,为什么。
最后的答案仍旧是自私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的接近死亡,姥姨还很年轻,比母亲小一岁。六年前,姥爷离开,我没有畏惧死亡,而如今,我怕了。为什么一直在哭?不只是因为姥姨的离开,更多的是因为对死亡的恐惧,闭上眼睛,不自觉的想到,若是躺在那里的变成了母亲,我该怎么办?也许我会发疯。然后越来越害怕,一直哭泣。人都是自私的,母亲说,除了至亲任何人都是无法理解亲人离开的那种入骨的疼痛,而我,终究是和她隔了层血缘,终究不是至亲啊......
近三个月过去后,逝去的伤感消磨了,可当日的担忧仍在。那****上车去学校后,楼上的窗户打开,有人伸头张望,车驶过很远,母亲仍旧在张望,直到我视线看不到她。我没有把头伸出窗外,我知道每次我离家去学校她都是如此,一如多年前站在阳台上看着我和母亲离开的姥爷。我微微闭了闭眼睛,车子已驶远......
人是自私的,无论什么时候,哪怕是亲人离去的伤感,可心不知是什么时候,已经变了。
母亲说,到了那一天,她不要经历那些过程,不愿被人摆布,不愿睡在窄小的陵地,她要飞,飞到天涯海角,随心所欲。
我说,如果到了那一天,我也要这样,飞离这个世界,随着心性,越走越远。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个世界是人们可以肆意逍遥的,但我只愿不要再被这种世界所透支,湖边的那片叶子飘到海中沉底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澄清透明,与现实完全相同却又完全相反的世界。也许,直到人们离开后才是真正的解脱。
对于死或生,又常常是因为活着所以才活着。人们想离开时,也许不能离开,而大多数人又偏偏是不想离开却又不得不离开,在一个矛盾体的世态,也许离开的人将会开启一种新的生命。
我们,仍将沉浮于这个世界,而愿已经离开的亲人们,在另一个世界得到干净纯粹的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