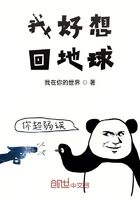流苏在一阵颠簸中醒来,马车车轴吱呀吱呀艰难地推着轮子向前滚动,连着车上的人也随着那单调的声音一荡一荡的。
流苏还未完全醒透,那迷药药性极强,她到现在仍是有些晕晕乎乎,头也疼得厉害。
眼前一片藏蓝灰蒙,看不清楚,她轻轻呻吟一声,却发现竟发不出声音来,嘴巴上被粗布堵住了,双手也被绑在身后,她全身蜷缩在一起,连脚也动弹不得,这一路过来,早已失去了知觉。
流苏一阵迷茫,之后猛地想起,她被人算计了!
香穗联合外人算计了她!
她想起当时香穗以小姐的名义将她骗到侧门,而后一名中年妇女将她迷昏,之后的事。。。流苏使劲甩了甩头,她想不起了。
马车仍在前行,流苏知道自己这是被绑架了,只是不知前路是哪里。
她现在无心去想香穗为何要害她,设法逃出去才是最要紧的。
她试着挪动身子,却无奈全身发麻,一动就疼得厉害,那绳子又绑得紧,稍一扭转就陷进肉里去,磨得她的手腕红肿破皮,却还是没有松动分毫。而且不知马车已经出发多久,她现在又饿又渴,全身无力,实在没有精力挣脱束缚。
此时旁边传来一阵响动,流苏登时绷紧身体,她方才只顾着想方设法解开绳子,竟不料马车里还有别人。是谁?她脑子里浮出之前那个强壮的中年妇女。
果然,一阵泛哑的女音响起,那声音又粗又糙,好像锯子划过木头沙沙响。
“小娘子醒了,婆子劝你还是安分着点好,不然你受罪我也受累,你说是吧。”
流苏“呜呜”两声,蹬了蹬腿。
那妇女想了想,问:“你想说话?”
流苏使劲点头。
“那可不行。你不能把我当了傻子,谁不知道你只要能说话必定是要先喊救命的,婆子做这活计真么多年,这种事见得可多了。”
流苏呜呜着摇头。
那妇女道:“你也别费劲了,到你这地步的,无非就想着两件事,一是如何逃出去,二就是为何落到这种地步。第一个婆子自然不能由着你,只是你若想知道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我倒还能告诉你一二。”
她说完捏住流苏的下巴左右瞧了几眼,天色还早,马车里也并不昏暗,流苏眼前蒙了布,才看不见。此时那妇女仔细瞧了流苏几眼,啧啧有声:“女人呐,命好好在一张脸上,命坏也坏在一张脸上。你说你若长得丑些,也不至于碍了主子的眼不是?”
流苏原本还挣扎着要将下巴上的手甩开,听了这话,渐渐冷静下来,她原就聪明,很快便想明白这是何意,也就安静了,只是脸色苍白得厉害。
她没料到,竟是小姐要害她。吴双儿虽讨厌她,却也从来没有下过这样的狠手。流苏略一寻思,便都明白了。这一切,皆因韩子厚而起。可笑她自问对吴双儿无二心,对韩子厚更是没有非分之想,却不想落得这样的下场。
那妇女见她安静下来,便拍了拍她的脸颊,“想明白了?明白了就安分些,这路上还有一两天要走,你若闹腾起来,少不得要给你些教训的。”而后她又喃喃自语:“若不是你主子非要将你送得远远的,我也不至于这样辛苦,找个窑子将你卖了,就你这脸蛋身段,至少也能得个三四十两,哪至于如今这般劳累,还未必能得个好价钱。”
流苏听了,只觉得好似寒冬时节落入冰窟窿里,全身发凉。
妇女见她面色如纸,心中恶意更起,嘻嘻笑道:“你也不必担心,婆子必定帮你找个好婆家。你不知,这苏州城千里外有连绵群山,山里人穷得叮当响,什么都缺,只不缺没婆娘的汉子,你若一去,这皮娇肉嫩的,定要给人好好疼爱一番。嘻嘻嘻嘻。。。”
她笑得下流猥琐,这番话,若是寻常闺女听了,只怕要羞愧死,流苏却只觉得眼前阵阵发黑,不若就此死去,好过受那般侮辱。
那妇女却好似知道她在想什么,“这便想死了?果然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就连个小丫鬟也这样娇气,轻易便要寻死觅活,也难怪你命贱不值钱。婆子明白告诉你,你若要死最好能干脆些,若是咬舌碰墙弄得个半死不活,我定要助你一力,让你生不如死!或者你再忍两日,等婆子将你卖了得了钱,你想怎么死我都管不着。”说完,又嗤嗤出笑。
她一路过来不给流苏吃饭便是为了这个,让她全身发软,连死的力气都没有,这真是逃不得又死不得。
马车依旧颠簸前行,原先还能在车外听到人声,后来渐渐稀疏,最后只剩下车轮轱辘了。
流苏的心也随着慢慢消失的声音沉到谷底,她这次,怕是在劫难逃了。
她想起她母亲。六岁那年,母亲刚去世,还未下葬,她就被她爹一路拽进苏州城,卖给吴府,不管她如何哭闹嘶喊,都不曾再回头看她一眼。
在她隐约记得一些的幼年里,并没有多少欢乐,大多是母亲的眼泪和父亲的咒骂。她那时不懂,那样婉约美丽的母亲为何要受这样的苦,直到大了,知道父亲时常咒骂的“破鞋”是何意,再联想其他,才逐渐将事情原委前后因果梳理出来。
她母亲原是大户人家丫鬟,或许还颇受主人家喜爱,那个留下来的梅花匣子便是个好证据。后来主人家娶了夫人,她这样没名没分却偏偏受宠的丫鬟自然成了新夫人的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主人家的宠保不了母亲,美丽又娇弱的她终究被卖给粗俗的市井小民为妻,又因不是完璧之身,遭人唾弃,日子哪能好过,最后只能终日以泪洗面,芳华早逝。
流苏勾起一个苦涩的笑,她母亲芳华早逝,却偏偏要留下她,接着受那些未完的罪。
天色渐渐昏暗,流苏原本还能朦胧察觉眼前藏蓝色粗布,后来就只剩一片黑暗了。
马车夜里停在小树林中,妇女和赶车的活计两人拿了干粮当晚饭,却只给流苏嘴上的粗布润了一点水,铁了心要饿着她。
流苏如今也没那心思吃饭,落到这样的田地,谁还能有胃口。
那两人怕她在车里耍什么动作,吃饭的时候便把她赶下车,放在眼前看管。
那个赶车活计大概三十来岁,长得尖嘴猴腮,一双小眼睛细长微迷,眼角下垂,显出几分猥琐。他看流苏面色苍白,浑身乏力靠在车轮边上,分外惹人怜爱,眼里便泛出光来,心里不知轮转着什么心思。就见他搓搓手,诞着笑道:“贺嫂子,这单货成色不错啊。”
被唤作贺嫂子的妇女瞪他一眼,“收起你的狗眼!别以为老娘不知道你在想什么,门都没有!”
那伙计恬着脸笑道:“别呀嫂子,总不过是要卖的,不如便宜了我——”
“放屁!你什么德行我还不清楚,若是以往那些让你玩玩也就算了,这个不一样,还是个干净的,我还指着她卖个好价钱,若被你糟蹋了,你愿意付那钱?你若愿意,看在你我相识情分上,我倒能给你点便宜。”她伸出两个粗短的手指:“收你二十两便好。”
那伙计看着眼前两个指头,终于讪讪着坐回去。
贺嫂子冷哼一声,嘴里嘀咕了几句。
夜间流苏和贺嫂子在车里休息,流苏全身无力,上不了车,那伙计或许还未死心,要来抱她上去,被那名妇女一瞪,抹着鼻子退到一边去了。贺嫂子人长得结实,身上更是有劲,只见她上了车,转身弯腰右手一拽,便将流苏拽了上去。
那个活计在离车不远处烧起一个火堆,夜里就在火堆旁守夜,防着些夜间活动的蛇虫鸟兽。
这一夜倒也安静,只除了流苏一夜未眠,辗转难安。
她的人生从来不由她决定,如今更不知要通往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