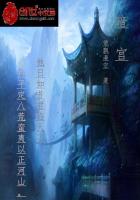莫少英似乎根本不关心这个问题,只是御动流渊频频来攻,一时间剑气匹练、削山切雪;黑芒疾舞,雪粉漫天。若不是莫仲卿念动陌离飞剑来挡,怕不是要将二人当场削成肉糜。
叮当看着青黑二色剑气在自己与莫仲卿周间交击不断,一时吓得娇躯瑟瑟发抖,已是隐带哭腔道:“少英哥这是怎么了,他、他真要杀了我们?”
莫仲卿没有回答,也不愿相信,可眼前情形不得不叫人揪心。难道传闻没有错,难道那臭名昭著的恶人真是二师兄,难道他已经完全变了副模样!?他突然大喝一声,身子高腾而起一跃三丈,于半空中五指戟张向后猛拉又瞬间收握成拳朝着那莫少英递上了质问的一击。
而电光石火间莫少英也已稳稳地接住了这一拳。
“为什么!”
短短三字却饱含千言万语,短短三字却能直叩心扉,可回应他的却是冰冷的铁拳。
“噗!”
迅猛无俦的一击直击在莫仲卿的胸口上,使他骤然生闷,一股火辣的疼痛未及蔓延就听那耳边拳风呼啸犹如狂风骤雨般再次直泻而来。身后的叮当怔住了身形,似乎这一刻连呼吸都已浑忘,那满脸惊诧的眼神,仿佛再说:“还手啊,快不还手!”
莫仲卿当然也已还手。
只瞧他面色一怒,气随意走,体内昆仑决顺势而发于周遭半丈之内形成一道无形的气场,罩在其内的莫少英身形立遭滞阻,出拳犹如龟速,然而仅仅是一个停顿间,只瞧那拳风中显出一小撮黑焰,拳风速度又极快地恢复正常,“砰”地一声砸在了雪地之上,激起一片碎玉乱珠。
这一拳当然是落空了,莫仲卿趁那停顿之际的功夫已抽身远离,旋即一个跨步,又再度黏住了莫少英,几乎贴着脸喝问道:
“你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回答?是不是你已经变了?那些事情真是你做的!”
高手生死对决本就是毫厘之差,莫仲卿此举未免有些托大,可他明知如此却不得不问,因为此刻心里早已是疑浪翻腾。可要命的是,他根本看不见那冰冷的面具后是副怎样的神色,也根本听不见哪怕一个字的解释,难道二师兄已打算全部默认,难道他真想赶尽杀绝?
莫仲卿彻底怒了,双拳频频交互格挡进攻的同时,已将体内昆仑决催逼至极致,这使得莫少英的身形明显慢了下来,他似乎也感到了哪里不对,一掌按来,借助二人双掌交击之力又抽身而退,旋即那远处流渊竟无声无息地向着莫仲卿后心袭来。
“铛”!
莫仲卿当然早已察觉到了异样,只是他未曾想到二师兄竟真于暗中偷袭,这使得他一颗心更为愤懑难解,猛地收剑在手,面上已满是坚毅之色,此刻任谁都可看出他是要动真格了。
“二师兄,你我十五一同习剑、情同手足朝夕相处,可不想才一年不见再见竟是这等局面!既然你不肯多说,好、我便打的你说!”
莫少英笑了,他挺直身形一抖流渊,竟是带着七分讥诮,三分玩味之意道:“行,我给你这个机会。”
莫仲卿没有再回话,他知道二师兄随意摆了个剑招往那一站,看似空门大露、破绽极多,实则这正是以不变应不变,以一临万的绝妙之势,这就好比一句话若只说了开头第一个字,你就永远不知道这句话到底会说些什么,更何况他知道二师兄总是奇招百出,妙到毫颠的。
既然不能在招式上以奇取胜,也同样看不出他的破绽,那只能以力破之了。可自己有什么剑招能在瞬间取得致胜点呢?莫仲卿忖了忖,忽然闭起了双眼,此时的他已想起了在地界中昆仑派掌门正一真人与那孟婆对战的一幕,自然也就想起了那惊天动地的一剑!
而对面的莫少英始终是笑着的,可片刻之后,他突然笑了不起来了,他惊异地察觉师弟莫仲卿的情绪正情逐渐趋于平稳,而令他更觉意外的是就连师弟这个人也正从他的气机感应中慢慢消失,若不是自己尚能以眼瞧见师弟,都要误以为师弟并不存在过。而他的剑,嗯?
“这是……!”
莫少英一惊却在瞬间捏紧了剑柄,他知道不能再等,若让师弟使出这一剑,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决不允许自己失败!瞬间,莫少英动了,动如脱兔,快若惊鸿已不能形容其万一,一阵风刚起,流渊剑尖已点到了莫仲卿眉心前!
然而若想再进一寸已是难上加难,他就如被人点穴般定格在了当场,而这时师弟莫仲卿已睁开了双眼,那双眸子清澈见底,隐隐生光,看不出喜怒,瞧不见悲苦,仿佛亘古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波动。也正因如此,这双目光看起来不会执着于一物,也就不会对万物无情,这乍听起来有些矛盾晦涩,但这岂不正是习剑者梦寐以求的境界?
“无我无剑,太上忘情!”
尽管莫少英没有系统学习过昆仑派剑仙之术,但这些神话传说早就听师父莫行则和祁彦之说熟道烂了。
“这是要败了、呵!”
莫少英脸上戴着那块青铜面具,所以瞧不出他此刻是何神色,不过想来落败的滋味一定不好受,而这种身形被剑意锁定,任人宰割的情形,换做是谁都不会甘心的。
而就在此时,一段凄美悲凉的埙音传入莫少英心头,这让他猛然想起了死去的牡丹,青青,九儿!这使得他莫名感到愤怒,体内煞气也跟着澎湃汹涌了起来,而眼前的莫仲卿自然也听到了这苍凉的埙音,不同的是他想起的是白素衣,而一想到素衣,这眼神中忽然就有了感情——凡人的私情。
“嗯?”
突然,周遭无形之中竟是“咔嚓”裂响,仿佛什么东西深深崩裂了一般。莫少英自然知道这是游离在四周的剑意,是剑意在不断的悲鸣,只要这剑意一破便是自己绝佳的反击之际。
果然,再听到第二声裂响刚起,莫少英陡然展动身形,近在咫尺的莫仲卿一怔之下便觉眼前一花,后颈跟着一痛,意识旋即远去。而令他惶惑不解,不敢相信的是,叮当为什么要帮二师兄?难道这一切都是二师兄和叮当事先布置好的?
叮当见莫少英将莫仲卿一剑敲晕在地,旋即飞快地抢过莫仲卿背上以建木之枝所铸的剑匣,那剑匣之中还有一幅早已损毁的须弥图。而这似乎就是叮当本来的目的。
“喂,你这样用力做什么,万一敲坏仲卿哥怎么办?”
此时的叮当早已没了先前那畏惧之态,将那等身长的剑匣抱在胸前气哼哼道。那莫少英冷哼,突然右手轻抖,一道肉眼可见的黑色剑气猛然向叮当疾扫而去。后者一惊,刚及躲开便娇吒道:“好你个莫少英,想过河拆桥?!”
莫少英冷笑:“我们从来都不是朋友,只是各取所需而已,所以趁我还未改变主意之前,还不快滚!”
叮当一怔,刚想怒叱奚落几句,可看了看剑匣终是忍不住跺了跺脚道:“好,你莫要后悔!”
“后悔?”
莫少英笑了笑,他早已不打算回头。
……
阴湿的潮气,刺鼻的霉味,房间中四处昏暗不明,唯有中间的石桌上一灯如豆。盈盈光火之下是半副面具,佩戴面具之人的整具身形都隐没于阴影之中,仿佛是在刻意凸显这副面具是何等的狰狞森冷。
而借着朦胧光亮,还可以大体判断出这是所地牢,但其简陋程度令人啼笑皆非,四壁莫说是挂些像样的刑具,就连四周墙壁都是不规则的泥木堆砌而成,所以与其说是座关人的地牢,不如是说土窑更为确切些。
而土窑之中也仅有一副十字木架和镣铐,镣铐崭新分明不似这所土窑应有之物。其上也正铐着一个人,而当那佩戴面具之人将旧盏之中添上新油时,那被铐之人才堪堪转醒。
随着一声无意识的低吟,莫仲卿将将醒来。尽管后颈还有些隐痛,但已不妨碍他逐渐明白一个事情,自己还没有死,但离死似乎并不遥远,他晃了晃有些微沉的脑袋,微微一动双手便如约地听见了一连串金属声响。
“醒了?想不到一年不见,你竟变得如此不堪一击!”
莫仲卿面色一怔,这才望见了正前方那具寒气森森的面具,他当然认得这副面具,也熟悉这股略带玩味的奚落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