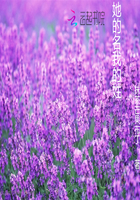大厅里一片寂静。所有的人的目光都焦距在管择的身上。管择露出了前所未有的狼狈表情,他似乎被十字先生刚才的气势吓到,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有气无力地看着我们。他有些哀怨又带着一丝请求的眼神,很可惜,这个地方并没有谁同情这位蜡像般的瘦医生。
“管医生,请说吧。还是说,您希望我替您说出来?”十字先生仰着下巴,盛气凌人的架势。我想这个时候没有谁该站出来和他抗衡,毕竟即使刚刚那样修罗场面都被他轻松拿下,现在所有人,包括阿薄也已经有了自知之明,不要和眼前这个华丽的男人作对。正常人的理论对这个人是完全行不通的,而在这样的场合下,他的怪异正发挥了压阵全场的作用。
管择不安分地转着眼珠,他的鬓角有几滴汗水谌了出来,但他并不介意。看来他是非说不可了,他薄薄的嘴像鱼一样一张一合了几下,喃喃地说:“槐绢。果然是个祸害。”
朝明皱紧了眉头,他刚毅的面容变得有些凶恶。他用低沉的声音质问道,“你是什么意思。”
“哼,就是字面的意思。”
这个男人——不正常。我内心深处有个声音这样说。他看似无表情却又想要做出些表情来,声音像留声机一样机械没有起伏。真的是个蜡像,但蜡像不会说话。那就是蜡像活了过来——啊啊,好可怕。我不自觉地占到了十字先生的右后方,管择瞠着浮肿的眼睛环视了厅里的每一个人。
“是她诱惑我的。那个女人天生就有勾引男人的魔性。”管择歪着嘴,发黄的牙齿在上下唇之间的缝隙若隐若现。
“我还在念书的时候就认识槐绢了,都二十几年了。虽说我和槐绢的家只隔了一条街,但是我们的身份却是天差地别。她是照相馆的老板的掌上明珠,每天都打扮的像个公主一样在大街上来回晃悠。而我呢,是穷铁匠的儿子,天天就只能在漆黑的作坊里面看着光鲜亮丽的大小姐搔首弄姿。槐绢简直就是漂亮的不像个人,人家是尊贵大小姐,自然对我这种人是看不上眼的。有时候我多瞄她几眼,呵,她就像是看到什么脏东西一样扭过头。我当时那个不服啊,发誓总有一天让她在我面前抬不起头。”
他自嘲地哼笑了一声,不理会四处投来的鄙夷眼光。
“不过她爸倒是还挺照顾我的,有段时间槐绢被一些不良的男人跟踪,我在那段时间就充当她的保镖,每天护送她上下学。为此我也被人找了不少麻烦,有一次还被一群人给围攻,差点没把我的两颗肺打透。我那时候差点连命都没了,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不过在我很没出息地挨了一顿打之后,槐绢对我的态度就来了个大转变。她经常来探望我,有时候还会亲手做写东西拿给我吃。我一下子就把她以前对我的种种给忘得一干二净,这样一个大美人儿来找我,那医院里的人给羡慕的,我就有些飘飘然了。有的时候真觉得她就是我的女人,晚上一个人的时候通过幻想她来度过寂寞,嘿嘿。”
“真是恶心。”十字先生唾弃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