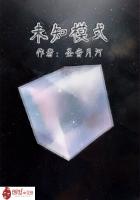走在小道上,新月端详着易安,之前太激动,看到易安和家萱一样的面孔,她便失去了辨别力,现在细细打量,发现易安和家萱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除去不一样的打扮,易安比家萱瘦一些,眉宇间少了家萱的那份可爱,但却多些清丽。她的个头较家萱高,看样貌似乎也比家萱年长一些。在新月脑海里,家萱最后的模样永远是二年前她们最后在槐树下看书时的样子。
“家……嗯,易安,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新月问她。
“我与爹娘转道回汴京,途中遇金兵突袭,加上难民过多,我和爹娘在慌乱中走散了。”易安说。
金兵?新月恍然想起,这是宋朝。她在书中看过那段历史,从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到后来君主无能南宋灭亡,宋朝一共经历了320年,其中以靖康之变为转折点,分为北宋和南宋。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都与大金有着无尽的关联,从最初的斡旋言和、联合灭辽,到后来的金兵南下攻宋、宋朝皇室被掳,北宋在屈辱中灭亡。南宋虽不是被金所灭,但宋室南渡后与金兵的无数次交锋以及岳飞抗金的典故,依旧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你还有亲人吗?”易安的提问打断了新月的思索。
“嗯…没有了,你是我在这里唯一认识的人。”新月答道。
“那……你可有什么打算?”
新月摇了摇头。
易安看她半晌,后来牵起她的手微笑道:“既然你无处可去,不如随我去汴京吧。”
新月不知道说什么好,唯有对她投去感激的目光。易安微微一笑,眼底尽是温柔。
积雪很深,她俩沿着路人留下的脚印往前走,三个多小时后,新月终于看到了她在这个年代见到的第二个、第三个以及更多人的面孔─—都是些衣衫褴褛而又筋疲力尽的难民的面孔,他们三三俩俩、搀老扶幼、步履蹒跚地走在小路上,所有人都是同一种因为极度苦难而漠然的表情。越往前走,难民越多,小道变得拥挤不堪。
新月只在书中见过那样的描绘,当真实的场景摆在眼前时,她被一种巨大的心酸震撼了。易安叹了一口气,“天寒地冻,四处饥荒,又加金兵肆虐,百姓苦啊!”
道路渐渐变宽,前方传来嘈杂之声。新月抬头望去,只见远方的雾霭中隐约伫立着一座类似城门的建筑。
新月突然发现自己和易安在人流中很突出,和周围褴褛单薄的难民相比,她们穿得太温暖、太奢侈了!显然易安也发现了,不禁牵着她加快了步伐。
但新月又发现,人群中有着这样突出装扮的并不只有她和易安,那从她们身边矫健地穿梭而过的几名男子更让人觉得他们是来错了地方。他们的身材较一般人高大,着统一黑色劲装,背后斜挎长剑,体态轻盈,显然不受饥困之苦,他们打量和审视着人流中每一个难民的面孔,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错漏的机会。
易安轻拉新月:“不要盯着他们看。”
新月回过神来,“他们是什么人?”
易安摇头道:“兵荒马乱,什么人都有可能,天快黑了,我们得赶在城门关闭之前进城去。”
接近城门口时,雪花如飞絮般飘飘洒洒地落了下来。漫天白雪中,新月看到了更多蜷缩在城墙下的难民身影,一无所有的他们将城墙当靠山,就地安营扎寨。
那之前的几名男子又折了回来,他们逆着人流,再次将目光从每个人的脸上扫过,似乎依旧一无所获,不禁露出了焦虑之色。
新月看得出,他们是在找人,但又不想引人注意,从他们的表情来看,他们要找人的并不在这人群之中。
几个光着脚的小孩围上来,拉着新月和易安的衣襟要吃的,新月和易安拿出所有的衣物分发给他们,马上又有几个老妇领着更多的小孩颤微微地围上来,已经一无所有的新月看着老人苍桑的面容,伸手去解脖子上的玉坠。
易安对她微微摇头,取下自己头上的碧簪和腰襟上的佩玉,递给了一位老妇人,那老妇人连连鞠躬道谢。后来新月和易安又将身上的袄子脱下来,送给了另外两位瑟瑟发抖的老妇人。
片刻之后,小孩和老妇人散去,余下两手空空、衣衫单薄的新月和易安站在原地相视而笑。雪花落在易安脸上,化开来后像汗水一样流下来,她打了个喷嚏。
城楼上有襟旗在风雪中翻动,上面写着斗大的“宋”字。城头上和城门口有卫兵把守。城墙正中央的门楣上刻着两个苍劲的隶书——河间。
新月和易安从城门下走过,看到卫兵百无聊奈、表情漠然─—他们除了着装和城外的难民不一样,其它并没有什么不同。
穿过城门,里面的世界顿时不一样了。新月看到了这个古老年代的街市,华灯初上的夜色中,古香古色的酒肆店铺临街而立,密密麻麻的招牌旗帜插满墙头。门前高挂的灯笼散发着柔和的橘黄色的光,漫天飞舞的雪花在那光线的笼罩中无声辗转而下。街道两旁摆满各式摊挡,小贩们并不吆喝,三三俩俩聚在一起怡然自得地聊着天,不时有路人撑着油纸伞从摊前流连而过。
“现在我们身无分文,今晚只好露宿街头了。”易安微笑道,新月有些过意不去,自己帮助人连累她跟着吃苦,易安仿佛明了她的心思,对她微笑摇头,任是一句话也无,新月也完全懂得了她的心意,她对她回笑,在那一刻,俩人竟是在无声中心意相通。新月眼眶湿润,她努力克制着,始终保持微笑,但是一个声音却在心里汹涌回响:曾经的家萱,回来了。
等天色完全暗下来的时候,她们街角找到了个安身的位置。那是一个露天的转角,墙内小楼露出来的屋檐刚好遮挡住了转角上方的风雪。只是那里已经被人提前占据了,那是一个少年,估摸年纪在十六七岁上下。借着楼阁中散发出来的微弱烛光,新月看到他头发凌乱,穿戴和城外的难民并无两样,甚至更为脏乱,也不知多久没洗过脸了,整个面孔灰朴朴的,双眼倒还晶亮,只是透着一股子冰凉。他一直懒懒地靠在墙角斜睨徐徐而落的雪花,慵散的神态冰冷至极。
新月不禁朝他多看了几眼,因为他的气场和装扮相去甚远。他的外表似难民,但骨子里却透着某种慑人的刚毅。要怎么说呢?反正他和新月在城外见到的所有难民都不一样。
易安不停地打着喷嚏,新月扶着她,问那少年:“请问我们可以在这里过夜吗?”那少年扫了她们一眼,将身子往一旁挪了挪,新月便扶着易安坐了下去。
雪像飞絮漫天洒落,街面和屋顶很快积起厚厚一层。新月和易安在野地中走了大半天,在寒冷和饥饿的侵袭中她们被更大的疲倦感打败了,很快,她们相偎着沉沉睡了过去。
半夜,新月在睡梦中听到一阵剧烈的咳嗽声,仿佛又看到了堆积于地的带血的海棠花,她一阵惊悚,在梦中大叫:“家萱!”
易安努力止住咳嗽,拍了拍她的肩,她惊醒过来,恍然想起这是在另一个世界,见易安喘息不止,她伸手在她额上试探,只觉得火热异常。
“你在发烧!这么烫,大概有四十度了!”新月又惊又急。
易安喘着粗气笑问:“什么四十度?……我只是感染了风寒,不用……太担心。”
新月顾不上解释,只是急道:“要赶紧看医生!”
易安还想说什么,但另一阵更剧烈的咳嗽涌了上来。新月听她咳得声嘶力竭,只觉得心慌无比。
那一旁的少年似乎一直没有睡过,这时他忽然道:“这个时辰哪里还有大夫?”他语气淡薄,眉目低垂,仿佛只是自言自语。
易安的咳嗽渐渐平息下来,像是耗尽了全身力气,她虚弱地闭上眼,缓缓睡了过去,但新月更为她担心了,因为她陷入了晕迷。
新月顾不得多想,试着将她背起来,但她实在太累了,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那少年斜睨新月,轻哼一声,似是嘲弄她的自不量力。新月不理他,拼尽全力再试了一次——这次她站起来了,她将易安往背上送了送,深吸一口气后,朝风雪里走了去。
那少年看着她的背影,表情依旧冰冷,只是没过多久,他看到新月又折了回来。
新月背着易安站在他面前,气喘吁吁地问:“你是这里的人,你知道哪里有医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