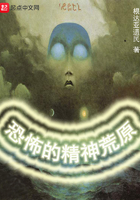我们像苍蝇一样在街上嗡嗡了半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小区。叫“家园红格”,听起来倒是不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对着它我总有种陌生的恐惧感,仿佛一头张着大嘴,露出獠牙的恐怖怪兽,要把我生吞活剥掉似地。我在害怕我付不起这儿的房租。
我们四个在街对面徘徊了足有一百万分钟。小区门口站着一个保安。我们在讨论那混账保安会不会让我们进去,要是不让的话接下来又该怎么办。看来这头杂种怪兽要生吞活剥的远不止我一个。
你要是看到四个老男人站在街上磨磨唧唧,心里准会十分烦腻。尤其天气闷热,像是裹着七八十岁老太太的奶罩。我心里一阵沮丧。我们看上去一定像极了四只站在半空电线上聒噪个不停的大乌鸦,要是那个保安有注意到我们的话,我想。最后我们终于讨论出了结果——随机应变。这办法真是再合适不过。我们一致把小六儿推到了第一的位置,充当挡箭牌。因为他年龄在我们四个当中最小。小弟就应当为大哥们遮风挡雨。所有当大哥的都这么说。
一路诚惶诚恐,可我们担心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发生。我们只是排成队,然后就从保安鼻子底下进入了小区。没有询问,也没有阻拦。突然间我觉得我们几个就像斗败的公鸡。奇怪的是我心里竟然偷偷窃喜。可能我真的要疯了。我有注意到我们走进大门时,那位混账保安左顾右盼一脸不屑,仿佛看到了四只浑身长满绒毛令人生厌的苍蝇。那副德行像极了插在混账稻田里的稻草人,戴着一顶破草帽,下面只有一条腿。亏我们几个还诚惶诚恐的像做贼一样,简直连苍蝇都不如。真******混账。
我们走进小区。那是一个不大的广场,正对着大门。广场上有个精致漂亮的水池,池子上搭有木桥,还有个小亭子。我们就在那里面耍了好一会。只是池子里没有水,不然的话我肯定要跳进去洗个痛快澡。我浑身冒汗,身上像是裹了一层厚厚的鼻涕。我是真想洗个澡来着。天气实在闷热,我的衣服都湿透了已经。我恨不得扒下自己的这身人皮来,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是说。
我们坐在亭子里,一连走了一个小时,脚都要掉了。我甚至已经在怀疑这双脚到底是不是我的,如果有人要我一定十分乐意的送给他。如果他不嫌臭的话。本来我还打算坐在亭子里吹吹风,可周围可怜的一丝风也没有。我记不得大街上有没有风,或许有或许没有,我记不得了。我是想说这里或许本来是应该有风的,只是被高高的楼房围严实了,风进不来。
我们一边休息一边讨论怎么做才能知道这小区里有没有房子出租。总不能挨家挨户的去敲门,这里好像也没有公告栏什么的。我们倒是可以找个住在小区里的人问一下,只是我们进来都快一万年了,除了那个混账保安,好像再没看见任何一个人影。这小区处处透着古怪。其实想找人问一下也简单,只需敲开一户房门。只是我们四个谁也不想这么做,这多少让人有点难为情。商讨了半天,我们又一次达成一致——去问那个该死的保安。这确实该死。
保安四十多岁,长的有点怪。你只要看了他的脸就忍不住想要上去掴他两耳光。世界上这种人多的是。有时候只看一个人的长相你就能判断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要么是欠揍的杂种,要么是不那么欠揍的杂种,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判断。不过不管怎么样,都是杂种。可我现在必须要对一个欠揍的杂种有说有笑,甚至恭敬有加,这真******叫人难受。嘿,说不定混账保安还想上来掴我两个耳光哩!
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或许还算个人吧。我说的可是大实话。
保安一听到我们是大学生,一改淡漠立马热情洋溢起来。那样子就跟他一下子成了天王老子似地。他可真把自己当成根葱了。要命的是这混账保安顶多也就二十七八岁,却要装作如同阅尽了人间沧桑疾苦,站在我们面前指手画脚、夸夸其谈。他说他高中没读完就回家帮父母卖菜,说他一个人只带了两百块钱就到广州打拼,又说后来他母亲如何的不愿意让他再外出,迫不得已只能到这里当个保安,还说他如何如何的还想出去往北京闯荡一番……我的天,简直是没完没了。还不停的问我们“你们学的什么专业”、“你们都找的什么工作”、“你们是一个班的嘛”、“班上多少人”……诸如此类跟他毫无关系的问题,简直让你烦不胜烦。我是真想上去狠狠掴他两耳光,老实跟你说。幸亏有小六在,他在学校当过宣传部部长,应付起来倒是很有一套。我站在最后面,用力搓着双手——我是在努力的让自己保持镇定。嘿,我说,他可真应该在家里给小六儿立个牌位。要不然,保不准脸上已经挨了我两巴掌了这会儿。
保安胡乱扯了足半个小时。最后,我们终于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他不知道。我的天,他怎么不去死。这回我是真的疯了。
可一转眼我又有些想明白了。既然这是我要面对的人生,我面对了又如何。我甘愿接受命运的安排。这下你可以死去了,我亲爱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