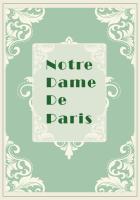从马总的办公室出来,我低头大步,往卫生间急走。好在,一路都没碰到同事。
洗了把脸,觉得自己丢人。
但是,我要的,难道不就是马总的原谅?
我为什么哭?
为什么喜极而泣?
难道是这件事结束得太快了?
难道真的获得了他的原谅?
如果是,这种原谅是否来得太容易了?
我真不敢相信。可是,这一切似乎已真的发生。
卫生间里,偶尔有人进来。
都是熟面孔,我赶紧用水多洗了几把脸,并且故意不擦,使得眼眶四周湿漉漉的,让人看不出任何异样。
低头从卫生间出来,去吸烟室。
里头有几个人在抽烟。
我没和任何人视线接触,故意让自己显得若有所思,好像在思考大事,不希望被人打扰。
静静吸完了两支烟,感觉肺里满是醇香的烟草味,才回办公室。马总的原谅,真是来得太快,这让我很不踏实。
下午的时候,还在回想上午的道歉。一直到快下班,才想起宁靖的事,于是给郭可扬打电话问进度。
接通电话,我还没来得及问,他就飞快说:“正准备给你去电话啦,涨价了,今年得15万。”
我有些意外,但想,毕竟有个答复了,也算进步,就说:“早跟人讲好的12万,这下麻烦了。”
“可不是我要涨。”他提高语气,“就问她要不要吧,给句话就行。”
怎么,转眼就没了昨晚来我家送威士忌酒时的那幅恭敬样?
我有些好笑。
“我得问问小姑娘。”想了想,我提醒他,“虽说小姑娘是SX人,可家里也没什么煤老板啊。”
郭可扬笑了几声,“你还真是……就这点小钱,我这么大一老板,能讹她吗?真是人家单位要涨。”
我也笑:“是吗,这个单位这么肯帮忙,我替人家小姑娘谢谢谢这单位领导的祖宗八代。”
“你******!”他大笑。
我正要挂电话,他又说:“对了,除了户口,如果她还想弄个事业编什么的,55万能搞定。”
我笑道:“咱先把户口办好了再说。”
下班后,我没直接回家,去了昨天才去过的湘菜馆。
点了一小瓶56度的二锅头,再点了辣椒炒肉、剁椒蒸鱼头和湘西腊牛肉。
菜还没上,我先把二锅头开了。倒转瓶盖,扯出里边的皮垫圈,把酒倒进瓶盖,先喝了一盅。喉咙瞬间热辣辣的,非常舒服。
心里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可我就是忍不住一番欣喜。不一会,把小瓶酒全部喝光了,又加了一瓶。
吃完饭,买单的时候,我更想不到,端着移动POS来服务我刷卡的,竟是昨晚那位一路道歉的领班。
他的记性也很好,当即认出我,马上说:“大哥,您又来啦。”
人家一天得跟多少客人打交道啦,想到这,我真是心花怒放。今天真是完美的一天。
酒精把我烧得暖暖的,站在路旁等的士,觉得浑身冒热气。
忽然想起,该给宁靖回个话,我掏出手机,拨号打过去。
电话铃短暂地响了一声,她就接了。好像她一直在等我的这个电话。
我无意卖关子,笑道:“妥了,明天打钱吧,先付一半,6万。”
听到她在那头几声欢呼。
的士司机开得有点野,车也有了些年纪,避震不好,颠得我胃难受。回到家,有点晕了。
当我清醒时,发现自己端坐在沙发上,手捧着一杯茶,好多片茶叶飘在水面,已经泡开了,形状很像眼泪。
这种形状,让我忽然觉出了几分尴尬。
今天的晚饭,吃得这么欢,究竟是因为帮宁靖办户口的事有眉目了,还是因为别的?
我手一翻,把杯子重重摔在地上,裂做无数的瓷片。
一些热茶水溅到我裤脚上,烫得我条件反射地一跳。
我像梦醒了,却不知自己为何生气。
碎裂的茶杯瓷块,看起来更像眼泪的形状,让我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恨意。恨这些茶叶,似乎也是恨这些碎瓷片,以及不知道还恨些什么。
我弯腰拣起稍大一点的瓷片,用力再摔。
终于,满地都是小碎片,没有哪块再值得我摔了。
我准备笑一笑。但是,白色的地砖上似乎散落着一些异样的颜色。仔细看,是酱黑色,才发现是自己右手食指的第一节与第二节关节之间,肌肉翻裂开了,像极了小鱼的嘴巴。深黑色的血,不断从鱼嘴涌出。
一定是刚才摔得太用力了,破瓷片的边锋把手指划破了。
让我意外的是,我本以为,血是鲜红色,怎么却是酱黑色?
纳闷了好久,才记起血就该是酱黑色。每年集团组织体检,护士从我肘窝血管里抽出血,一小管一小管的,不就是这种黏糊糊的酱黑色?
我这才顾得想,得去趟医院。没感觉到伤口的痛,但是,如果感染了,似乎还不值得。
下楼出了小区,站在门口,伸手拦出租。
终于拦下一辆,司机本来已停车,但没等我走到车跟前,忽然一踩油门开走了。
我失败了好几次,才明白原因所在。于是拦车时不再用右手,背到身后,只伸出左手,才拦到一辆。
赶到医院,急诊室走廊里挤满人。
我挂完号,被护士使唤进了一个小房间,见到一位大夫。中年汉子,矮矮胖胖,神色疲累,应该忙碌了一晚。
他看看我的伤口,“口子这么深,和谁干仗了?”
我虽然感谢他的关心,但不想回答。
他在医疗本上写字,在电脑边操作,安排我去付钱。等我付完钱,被护士安排进了一间治疗室,那位医生进来了。
他开始时一言不发,给我手指消毒,拿起一根粗针,穿针引钱。
我直直地看着他在我的手指上操作针线,忽然想起那只摔坏了的瓷杯。很后悔,明天还得花钱买,真破费。
当我起身离开时,医生忽然笑了,说:“又不是演三国。没给你打麻药,你就是哼一声,难道破坏了光辉形象?你说,你是不是姓关?”
想不到这人是个贫嘴。我没心情跟他开玩笑,可他并不罢休,好像忙碌寂寞的夜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开心的理由,我出门时,他在我身后喊:“哥们你真酷,有空再来啊!”
我回头笑道:“去你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