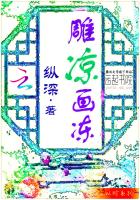中秋过后,天气很快就转为寒冷,阳城的冬天又干又冷,明箬铮除了必要的训练,大半的时间都窝在屋里渡过。很快,日子就平静的过到了三月。
阳城的三月最是春光明媚,明箬铮在房内狠狠的闷了一个冬天,按说天色转暖,本应该心情大好,可这几天,十七却总见到明箬铮紧锁着眉头,似乎有什么心事。
这天傍晚,明箬铮自外面回来,眉头又拧成一团麻花,见到十七,只点点头,便要转身回房。
十七连忙拦下:“这几天心情不好?”
“没有。”
“若有什么为难的事,不妨交给十七。”
明箬铮没有立刻接话,而是仰起头看了十七许久,眉头拧的更紧:“你可去过‘剑舞阁’?”
十七没想到明箬铮突然问出这么一句,原来这剑舞阁名虽为“剑舞”,却是阳城鼎鼎有名的青楼,西漠尚武,阳城这种边境重镇尤甚,而这一间“剑舞阁”正是由于号称阁内姑娘们人人会舞剑而引得阳城的公子哥儿争相追捧。
十七有点窘:“十七对青楼楚馆向来没有兴趣。”
明箬铮低声道:“我不是说你。”眼睛却看着地面,不知心里在想什么。
十七一震,惊道:“难道你?”
“胡说!”明箬铮这才醒过神来,“是南风大哥。”
“歌南风?”十七更是惊讶,以他对明箬铮的了解,跑去青楼胡闹还有可能,若说是歌南风,十七怎么也不会相信。
想到这里,十七正色道:“公子怕是弄错了。我虽然和歌南风向来不和,却也能保证他绝不是流连风月场的浪荡子。”
“我比你还要肯定。”明箬铮没好气的说,“正因为他不是那种人,我才会心生疑惑,担心这当中有什么不妥之处。要知道,司徒靖才能平庸,军中之事主要依靠手下几个校尉。而其中论又以南风大哥为首,是不可多得的将帅之才。所以,对阳城有觊觎之心的人,一定会先挑南风大哥下手。”
“原来是担心这个。”十七笑道,“若是担心,何不直接去跟歌南风说?对你,他一定会坦诚相告。”
“前些天,我也只是在去麒顺行的时候偶然听伙计说的,说他迷上了剑舞阁的头牌绿柔,一直未得实证。刚才我却是亲眼看见他进的剑舞阁。”
“绿柔?此女卖艺不卖身,弹得一手好筝,对其他乐器也多有涉猎。至于来历,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明箬铮眉毛一挑:“你倒查的清楚。”
“阳城有点名气的人我都一一查过。”十七淡淡道,像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见到明箬铮的眉头又慢慢的锁了起来,十七补充道:“你若是不放心,不如我陪你去查查。”
明箬铮跟着十七在夜色的掩映下从剑舞阁的后院越墙而入,准确的找到了绿柔的房间。两人轻轻跃上屋顶,运功收敛气息。
柔和而恬静的筝音从房内传出,明箬铮望向十七,却见十七盯着她,脸上流露出震骇之色,待要询问,却被十七用眼神制止了。
一曲奏毕,一把清澈动听的声音说道:“当日买筝的时候承蒙南风公子割爱,后来遇到奸人纠缠,又劳烦公子仗义相助,绿柔感激不尽。只是近些日子公子一有空便来绿柔处,绿柔乃一风尘女子,让外面的人知道了只恐于公子声名有损。”
“姑娘所奏的乐曲清丽脱俗,当时歌南风也是琴送知音,本就是成就了一桩美事。而这些日子歌南风来此名义上虽全是为姑娘挡那些无聊之人,却也有一半是为了姑娘出众的琴艺。至于其他人怎么想,歌南风既管不了,也不愿管。”说道这里,歌南风话锋一转,“但青楼楚馆到底非终老之所,姑娘可想过赎身?”
绿柔幽幽叹口气,说道:“绿柔自幼孤苦,从懂事一来便在这青楼卖艺为生。我一个弱质女流,肩不能抗手不能提,只有点琴艺还拿的出手,若离开此地,天下又哪有我的容身之所呢?”
听到这里明箬铮在屋顶上对十七连比带画,大致意思说这绿柔对歌南风大有情意,却碍于女子的矜持不肯明言。
十七没好气的瞪了明箬铮一眼,示意她别乱动,免得被房内两人发觉。
房中歌南风沉吟了一会儿,开口道:“在下尚有些人脉,姑娘若不嫌弃,也许在下能帮姑娘找户好人家,也算有个归宿。”
这一句不仅让绿柔大为意外,连屋顶的十七和明箬铮也吃了一惊。他们本以为歌南风时常来此听曲,定是对眼前的女子生了爱慕之心,谁知他竟主动提出要给绿柔找个好归宿,但若说歌南风全为音律而来,似乎也不太能让人信服。
房内绿柔半晌没有接话,再开口时,声音听起来有些颤抖:“敢问一句,这剑舞阁吸引公子的,究竟是绿柔的人,还是绿柔的筝?”
歌南风的声音一如平时的冷静:“姑娘的人才自然是极好的,筝曲更是绕梁三日。只是……”
他尚未说完,便被绿柔打断,语气颇有些忿忿:“绿柔虽是一弱女子,但所幸尚能独立,并不需要别人的同情怜悯。此筝当日便是公子割让的心爱之物,现在绿柔把它还给公子。望公子今后以名誉为重,莫要在留恋烟花之地。绿柔与公子从此便是天涯路人,各不相干。”
绿柔一口气说了这么一大段话,紧接着便听到房门“吱呀”一声,想是歌南风已被绿柔“请”出了房间。
明箬铮将房内动静听的一清二楚,心里暗暗赞了一句:“想不到竟是个烈性女子。”
两人又在屋顶停留了一会儿,房内再无声音传出,明箬铮见十七打出手势,便欲随十七离去,跃下之时忍不住向半掩的窗中望了一眼,只见房内一个清丽脱俗的绿衣女子正坐在桌前,怔怔的盯着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