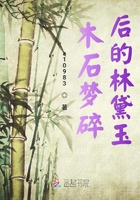在黟县休整了半个多月,剿杀了几家颇有劣迹的土豪,一直到七月上旬,吕蒙才离开黟县,率本部一千六百军,降兵四千三百余人,浩浩荡荡地抵达了泾县南城门外。
仓慈谏言道:“司马,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您身为一军主将,不该亲自赴险。仓慈不才,愿去劝降太史慈。”
吕蒙笑道:“孝仁,这一路上你都说过好几次了,我也回过好几次了。太史慈信义笃烈,乃是当世无双的义士,我去见他,非是诓骗他,非是折辱他,实是敬重他的为人和能力,为他和属下的两千士卒指点一条明路。我以至诚之心去说他,他也会以至诚之心回报我,绝不会戕害我。所以此行,实是无惊无险。”
按吕蒙对太史慈此刻心态的推测,即便是让仓慈去劝说,以仓孝仁的能力也应当可以说服太史慈。但吕蒙还是坚持亲自跑一趟,无他,只为和太史子义结下一个善缘,将来或许能多一分招揽的希望。
“司马,既然如此,让我随身侍卫吧。”徐盛大声道,他相信吕蒙的判断,此行无惊无险,但凡事皆有意外,万一太史慈忽然疯癫了呢,所以徐盛请命随行,即便有个万一,也能舍命护卫。
如今吕蒙军中,论个人武勇,最强的便是吕蒙、谢旌、徐盛、吴硕四人,放到整个时代都可以称得上二流斗将,江东地面上能和他们打平的还有多人,但能明显胜过他们的,也就孙策、太史慈、周泰三位一流斗将了。
以徐盛和吕蒙的关系,拼死护卫时,会比平时更胜一筹,完全有可能短时间内挡住太史慈,确实是此行最佳的保镖人选。但吕蒙还是笑着拒绝了,道:“文向,此行只需诚意即可,无需仰仗武勇,你还是留下统率大军吧。”吕蒙扫过其余诸将,鲜于丹、吴硕、戈定、朱然、樊大将等纷纷昂首挺胸,愿陪主将同行,吕蒙微微一笑,指着戈定道:“当日你曾随太史子义同上神亭岭,今日便随我一行吧。”
戈定躬身应命:“固所愿也。”
吕蒙当即和戈定跃马出阵,直驰到城门下,大声呼喝:“吕蒙吕子明,请太史子义一见。”
泾县守军早已发现吕蒙军踪迹,两千守军,太史慈亲自带了一千守在南门。听到城门外面便是吕蒙,城墙之上顿时有些骚动。如今的吕蒙,已经不再是当初的无名小卒了,在丹阳郡内已是颇有威名的大将,便是在整个扬州,也有不小名声。
新年前后吕蒙在江北历阳县先破庐江兵,后破阜陵兵,两次都是以少胜多,都是大获全胜,这样的战绩如今已经传扬开来了。更不用说从四月份以来,吕蒙连续扫荡于潜、歙县、黟县,听说还分遣部将去了陵阳,所过之处,丹阳郡内赫赫有名的贼帅们全部灰飞烟灭。不仅是贼帅,各县内的土豪、豪商,只要不是第一时间表示向孙策军臣服的,也多半都被抄灭。吕蒙的威名,是踏着丹阳豪强贼帅们的尸骨成就出来的,是用四县无数贼兵的鲜血渲染出来的。
泾县城内的守军,虽然既不是贼军,又不是土豪,严格来说,他们是扬州牧刘繇的军队,是汉朝的正统军队才对,但对于吕蒙军的到来,泾县守军们还是忍不住提心吊胆。虽然太史将军勇猛无敌,轻易击败了祖郎,但吕蒙的战绩看起来更加厉害啊。好在吕蒙只带了一员小将,轻骑出阵,脑子稍微灵活一点的人,便都知道,大概是想来劝降,不少人内心竟然隐隐松了一口气。
“将军,怎么办?”太史慈身边的几个军官忍不住问道,严格来说,太史慈目前并无正式的军职,称其一声将军,完全是这些残兵对太史慈的尊敬和信服。
“是来劝降某的。”太史慈叹息一声,下面的两个人,他还有印象,一个是神亭岭上孙策十三骑将之一,如今太史慈已经知晓这人便是吕蒙了。而另一个,正是当初勇敢地追随他登上神亭岭的骑卒。当日神亭岭一战,太史慈被孙策等人追赶,不得不撤退,那个骑卒没能跟上,太史慈只以为他已经战死,为之垂泪伤心,后来在刘繇军中问了戈定名字,知道竟然还是东莱黄县的同乡,更是唏嘘不已。现在看到他还活着,虽然成了吕蒙部下,太史慈非但没有恼怒,反而有些欣喜。在刘繇军时,戈定不过是个骑卒,如今看其骑着骏马,披着精良铁甲,追随在吕蒙身侧,多半是受到了重用吧?太史慈忍不住看了看自己的铁戟强弓,心中暗道,太史慈啊太史慈,什么时候你才能英雄有用武之地呢?
“将军,不如以你神射,将那吕蒙射杀,吕蒙一死,敌军必溃。”残兵之中,总有一两个刘繇的死忠派,想和孙策军抗争到底。但此人话才出口,周边同袍们却纷纷对他怒目而视,今日射杀了吕蒙,便是和孙策军结下死仇了,孙策定然会亲提大军复仇。大部分残兵早已经想清楚了,跟着刘使君,是没有前途的。
太史慈哂笑一声,如果是交战,他不会迂腐到不用箭术,但吕蒙只是来劝降,直接将其射杀,岂是他堂堂太史子义会做的?
“开城门,放吕蒙进来……不,备马,我亲自出去。”
太史慈匹马而出,径直来到吕蒙、戈定面前,先对戈定道:“戈定,一向可好?”
戈定慨然道:“多谢太史将军挂怀,戈某一切都好,将军,不如你……”
太史慈摇摇手,阻止戈定说下去,道:“某无职无权,称不得将军。”又对吕蒙抱拳一礼,“吕都尉。”
吕蒙朗声大笑,回礼道:“当日神亭岭一见,吕蒙对子义兄的英勇极为敬佩,今日得以再见,不胜欢喜。子义兄,如今刘使君……”
太史慈再次摇摇手,打断了吕蒙的说话,回首望了望城池,直接问道:“吕都尉可是来劝降的?”
“子义兄言重了,良禽择木而栖,如今……”
吕蒙正要滔滔不绝,哪知太史慈又一次摇手,再次打断了吕蒙的说话,说起来颇为无礼,只是吕蒙看着太史慈略带悲伤的神情,却丝毫产生不了怒意。
只听太史慈悠然道:“我来江东,也不过半年有余,本以同郡有旧,想着助刘正礼一臂之力,以中兴大汉,如今想来,却是来错了。刘正礼确实不适合这个乱世啊,倒是你家主公孙伯符,的确英武盖世。而且我在泾县数月,也听说孙伯符在丹阳东部诸县颇有仁政施行,或许孙郎正是江东需要的英主吧?”
“我聚拢残兵,把守泾县,本来也只是坐保一方安宁,为这两千将士找一条出路。你既来劝降,我便应了。这两千将士,经我数月训练,颇有成效,转交孙郎,也有助于更早一日平定江东,还江东四郡安宁。只是其中亦有少数将士,尽忠于刘正礼,或有不服,望能允许其解甲为民。”
无需吕蒙劝说,太史慈自话自说地便同意了。听其不称刘使君、刘扬州,而称呼刘繇表字,也确实放下了君臣名分,只是吕蒙听在耳中,总觉得太史慈交出两千兵,自己却像是另有打算。
果然,只听太史慈道:“三月时,我把刘正礼送往豫章郡,本来已经打算渡江北归了,只是被泾县士卒挽留,不忍弃之,也不愿他们流落为匪,才又留了数月。如今将这两千人托付吕都尉,太史慈职责已去,于江东再无挂念,是回返青州的时候了。我老母幼子尚在家乡,半年未能尽孝母亲,照顾孩儿,如今归心似箭,吕都尉,戈定,我们就此别过。”
吕蒙大吃一惊,这才注意到,太史慈马匹上竟然还挂着一个包裹,大概便是衣物盘缠之类吧。太史慈竟然如此洒脱,直接交出兵权,毫不留恋,便要匹马北归。
“且慢……”吕蒙连忙道,太史慈这样的大将,即使未来不一定归属他,现在也要把他留在江东。
太史慈知道吕蒙想要挽留,再次摇了摇手,想要拒绝。哪知这次吕蒙直接出手,一把将其手臂按住,太史慈臂力一张,便要挣脱,吕蒙却是又搭上一只手,一边说道:“子义兄,请听我一言!”
太史慈当然知道吕蒙想要说些什么,无非是为孙策挽留他,本欲不听,只是看到吕蒙满脸真诚,不由叹息一声,不再抗拒。
“子义兄,你在江东并无大名,但我吕蒙,却是知道你的。”
“我知道你曾为东莱奏曹,为了东莱郡和青州刺史的纠纷,昼夜兼程,千里赶赴洛阳,截下刺史奏章,完成本郡任务。为此得罪刺史,避祸辽东。”
“我知道你事母至孝,因为孔文举在你避乱辽东期间照顾你的母亲,所以不避危险地报答他。出入贼围,求取援军,击破管亥。”
“我知道你虽然不受刘扬州重用,但以同郡之谊,在曲阿之战、在牛渚之战,奋不顾身,救护刘繇。”
“我知道你是为了不负城中两千残兵的期望,才留在泾县。”
“我知道你勇猛无敌,神射无双,是稀世猛将。”
“我知道你自幼好学,熟读兵法,非止于猛将。”
“我知道你贵重然诺,信义笃烈,有古人之风。”
太史慈渐渐激动起来,这个人,吕蒙吕子明,竟然如此了解他!竟然如此推崇他!听说吕蒙是豫州汝南人,怎么会对他如此相知?是戈定说的吗?不,戈定虽然和他同县,但以前并无来往,不可能这么了解他的。听着吕蒙不断说下去,太史慈感慨万分,吕蒙怎么知道他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子义兄,像你这样的大丈夫,好男儿,当提七尺之剑,升天子之阶……”
丈夫生世,当带七尺之剑,以升天子之阶……这正是太史慈临终时的叹息,也是他一生的志向。
“……子义兄,孙郎看重你,但我今日留你,并非是为了得到孙郎的奖赏,而是为了子义兄你本人,江东,正是子义兄你的用武之地啊。”
“子义兄,你若北归,或隐居青州,或出仕刘备,多半便是如此吧。当今天下大乱,英雄岂能独善其身?况且青州也不是安宁之地,袁绍、公孙交战,必然波及青州。届时子义兄虽有武勇,终究不敌大军,如何护佑母亲幼子?如今乱世,子义兄唯有出仕,才能保境安民,并且应当把家人移居到安宁之地,倾力守护。”
“但如果出仕刘玄德……此人遽得徐州,根基不稳,徐州又是四战之地,刘备内忧外患,定然会被逐出徐州。子义兄如果出仕,只能跟随刘备颠沛流离,怎能让你的母亲安居?”
“子义兄,江东虽然还在战乱,但以孙郎之才,一两年内便能彻底平定,到时江东便是和平乐土,才是子义兄你奉养老母之地啊。而且孙郎重视你,定能重用你,将来无论是北伐袁术,还是西征刘表,都有子义兄你的用武之地。”
“护佑家人,一展所长,子义兄,舍此何为?”
“子明。”太史慈没有抽出被吕蒙合住的手,反而将另一只手盖了上去,牢牢合住,也不再客套地称呼吕都尉,“子明,知我者子明也!诚如所言,太史慈敢不从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