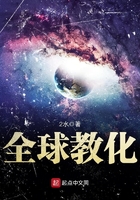独步的作品被介绍过的已经不少,这里所集的只是我个人所翻译的五篇。这五篇在他近百篇的短篇小说中,都是比较有名的杰作。
独步虽作小说,但根底上却是诗人。他是华治华司的崇拜者,爱好自然,努力着眼于自然的玄秘,曾读了屠格涅夫《猎人日记》中的《幽会》,作过一篇描写东京近郊武藏野风景的文字,至今还是风景描写的模范。
独步眼中的自然,不只是幽玄的风景,乃是不可思议的可惊可怖的谜,同时就是人生的谜。他的小说的于诗趣以外具有自然主义的风格,和他的热烈倾心宗教,似都非无故的。《牛肉与马铃薯》中主人公冈本的态度,可以说就是独步自己的态度。《女难》中所充满着的无可奈何的运命思想,也就是这自然观的别一方面。
事实!呜呼,这事实可奈何?
天上的星、月、云、光、风,地上的草、木、花、石,人间的历史、生活、性质、境遇、关系,生、死、情、欲、恨、恋,不幸、灾厄,幸运、荣达,啊!这事实,那事实,人只是盲目地在这错乱混杂的事实中起居着吗?
自然!宇宙固不可思议了。人间!啊,至于人间,不是更不可思议吗?它是爱着自然的法则的东西,所不思议的是它的生活,运命,及其Drama。
日记(明治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非我”的这自然,“别的我”的他人。这是我近来的警句。
啊,人类!看啊看啊,看那许多“别的我”的我的在地上的运命啊!看啊,看啊,俯了仰了,看“非我”的这自然啊!
想啊想啊,把这我与这自然的关系。想得了这我与自然的关系,才可谓受有救世的天命的人。
日记(明治二十七年二月十三日)独步在明治二十六年(二十三岁)至二十九年五年间曾作的日记,其中充满着严肃的怀疑的气氛,象上面所举的文句几乎每页都可看到。他论诗与诗人的目的说:
从习惯的昏睡里唤醒人心,使知道,围着我们的世界之可惊可爱,才是诗的目的。更进一步说,使人在这可惊的世界中发见自己,在神的真理中发明人生的意义,才是诗人的目的。
日记(明治二十六年十月十三日)独步是有这样抱负的人,所以他的作品虽富有清快的诗趣,而内面却潜蓄着严肃真挚的精神,无论哪一篇都如此。
独步的恋爱事件,是日本文学史上有名的史料。中日战争(明治二十八年)起,独步被国民新闻社任为从军记者,入千代四军舰,归东京后,国民新闻社长德富苏峰的友人佐佐城丰寿夫人发起开从军记者招待会。独步那时年二十五岁,席上与夫人之女佐佐城信子相识,由是彼此陷入恋爱。经了许多困难,卒以德富苏峰的媒介,竹越与三郎的保证,在植村正久的司式下结婚。两人结婚后在逗子营了新家庭。独步为欲达其独立独行的壮怀,且思移居北海道躬耕自活,如《牛肉与马铃薯》中冈本所说的样子。
谁知结婚未及一年,恋爱破裂,信子忽弃独步出走了。
独步的恋爱理想,在男女双方继续更新创造。信子出走后,独步给她的书中有一处说:
据有经验的人说:新夫妇的危险起于结婚后的半年间。忍耐经过了这半年,夫妇的真味才生。真的,你在第五个月上,就触了这暗礁了。
原来人无论是谁都是充满着缺点的,到了结婚以后,不能复如结婚前可以空想地满足,实是当然之事。如果因不能空想地满足就离婚,那么天下将没有可以成立的夫妇了。这里须要忍耐,设法,彼此反省,大家奖励。所谓共艰难苦乐者,不只外来的艰苦,并须与从相互间出来的,人性的恶点奋斗。夫妇的真义,不就在此吗?
《夫妇》为独步描写恋爱的作品,亦曾暗示着与上文同样的意见。《第三者》则竟是他的自己告白了。江间就是他自己,鹤姑是信子,大井、武岛则是以当时结婚的周旋者德富苏峰、内村植三、竹越与三郎为模特儿的。
信子一去不返,结果不免离婚。独步的烦闷,真是非同小可,曾好几次想自杀。他的日记中,留着许多血泪的文字。
她竟弃舍我了,寒风一阵,吹入心头,迥环地扰我,我的心已失了色,光,和希望了。信子,信子!你我同在东京市中相隔只里余,你的心为何远隔到如此啊!
啊,恋爱的苦啊!逐着冷却了的恋爱的梦,其苦真难言状。
我永永爱信子,我心愈恋恋于信子。
她已是恋爱的坟墓了吗?那么我将投埋在她里面。
(明治二十九年四月三十日)睡眠亦苦,因为要梦见信子。
我到底不能忘情于信子,即在走路的时候,填充我的爱的空想的,仍是关于信子的事。
自一旦与信子的爱破裂,就感到一生已无幸福可言了,我是因了信子的爱而生存的。
无论怎样的困厄,贫苦,不幸,如果有信子和我在一淘奋斗,就觉得什么都不怕。信子的爱,给我以难以名言的自由。
然而,现在完了,现在,这爱的隐身所倒了!
我好象被裹了体投到世路风雪之中,我的回顾从前之爱,亦非得已。
我真不幸啊!
然而爱不是交换的,是牺牲的,我做了牺牲了,我的爱誓永久不变。
(明治二十九年五月二日)赖了先辈德富苏峰等诸名士的鼓舞,及平日的宗教信仰,独步幸而未曾踏到自杀途上去。可是此后的独步,壮志已灰,豪迈不复如昔,只成了一个恋爱的飘泊者,抑郁以殁。啊《女难》作者的女难!
独步是明治四十一年死的。他虽替日本文坛做了一个自然主义的先驱,但却终身贫困不过。现在全国传诵的他的名作,当时只值五角钱三角钱一页的稿费。《巡查》脱稿,预计可得五元,高兴得了不得邀友聚餐,结果只得三元,餐费超过预计算。这是有名的他的轶事。他的被社会认识,是在明治四十年前后,那时他已无力执笔,以濒死的病躯,奄卧在茅崎的南湖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