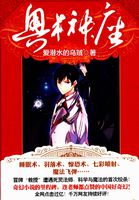却说雪花惊醒,挣出一身冷汗,心中明白,不敢说出。次日起来,便走至庙中间神前叩谢。是时,阿莲亦起来。陈姓女子果然叫了人来挑东西。雪花便将被一条,锅一只,碗三只交与他。那挑的人却只取了破锅,将碗三只丢在天井中,说:“不用带去,小姐处尽有碗用。”雪花便搀了阿莲,跟着那人,叫那人慢慢走,二人跟着。原来就在前面,引入门,雪花二人便进去。那陈小姐便迎出来,送二人进去。雪花看看,亦是高楼大厦。陈小姐道:“此是我娘家,只有我父亲、侄儿二人,并无他人。下人亦有,小姐可放心住下。”阿莲便请太老伯及世兄出来见过了礼,雪花亦参见了。便收拾一间房,令他主仆二人同住。又拿二付被褥并浆洗衣服一大叠,与他二人换。”又说:“小姐,从今以后不必锉弹丸,我家岂在乎你二人吃用?”便着人将搬来的铅丸退至局中交清了。自此雪花二人便在陈家住下了。这日孔先生所遇正是雪花,却不敢明认,只得各走各路。
放过先生不提。且说华如当时逃难,被长毛逼着,当时只有玉山长毛过了身,便有官兵数十个营盘团团圈圈,有四百里路开阔,故华如只得逃玉山是生路。当日走至晚,便同一群逃难的在一个街坊上歇了一夜。次日,便寻了有卖饭的人家。原来华如幸亏雪花将他的东西集了一担挑至山中,不料二人走散,华如便将担内只取了英洋一包,有一百元放在身上,其余尽得送与长毛了。此时只得从身上取出英洋一元换了一碗饭,吃完便问那卖饭的:“你可随便找我几百钱防防身。”卖饭的听说,便找他三百多钱。华如拿了,从村坊口寻着大路又走了一日,便是常山玉山交界处。此处长毛亦过了身,居民都逃回来,仍理旧业。
有一家要请先生,华如想着无处安身,不如自荐,寻个安身处再作道理。那人家姓金,考了一考华如学问,却极佩服,便请定了华如,教他两个儿子。华如本来深于时文,此时仍复用功。心想:“我家闻得人人说西溪村尽被长毛烧去,无家可归。虽有田产,不必问,此时无人耕种,料必荒了。却不知合家大小如何。不如俟长毛退了再议。”因此要想从时文中寻条生路,便埋头用起功来。又想想:“我从前公公交代父亲,曾托梦与他,说时文是件害人的东西,我为何明知故犯?”又想想:“此必父亲因乡试得病回来,恨极了,故造出这些说话来。若说三件内,鸦片、小脚果然害人,我已亲眼见了;若说时文,从明朝至今五六百年,未闻有害人之说,此话是真不信。”因此将他公公与父亲说话一概付之东洋大海去了。却不知华如读了时文,四肢五脏又换了一付,其害处又不与孔先生一般,此是后话。
当日华如不知不觉又堕入时文魔障,日间教书,夜间读文,读得高兴,更不禁开喉朗读,声入云霄,便招了一个故人来。你道是谁?原来便是上海来的孔先生。这先生自路遇雪花便不能细认,便欲在玉山寻寻头路,以后便拿一个小小杂货店记司账。不料先生于时文之外一无所能,见了算盘便头痛,不但大九归不能,即百子算亦不会,并算盘档数,上下档子亦模糊。记了两个月账,东家便说:“这两月折本折得凶,却是为何?若再折两月,便倒糖担了。”有一个伙计说:“新请来的管账先生,我看不会打算盘的。东家不信,看他打算盘会错不会错。”东家道:“胡说!这个先生呱呱叫,是廪生。时文最难做的,尚做得来,算盘叠子算小孩皆会的,而你等如此看轻他,说他算盘总不会打。”心中很不信伙计的话。
不料这一日先生正在打算盘,东家看时,竟先生将当千的一个算盘子当做当十的打。东家说:“完了!完了!难怪我要折本。”自悔不听伙计的话,又被他老婆无日无夜埋怨他,三面夹攻,便登时气得吐血,当时即将先生铺盖丢出来。先生只得拾起铺盖,身上尚有三个月薪俸,就住在饭店里。
这日正闻得华如读文章,便走进来,意欲寻个文士谈谈天,不料即是旧日的学生。彼此相见,各述逃乱的情形。先生便将自己在大营及上海两处不能容身,并现在被店家赶出,家小不知何去,一一告诉了华如。华如便问:“师母既不知信息,先生可曾寻觅否?”先生道:“我从何处寻觅?现在浙东长毛未退,我至此尚然绕道而来。”又问:“西溪遭长毛,你合家大小可知你在此处么?”华如道:“我亦被长毛冲散,逃在这里,他们哪晓得知我在这里。”先生道:“我在玉山城下看见一个人,似像府上的丫头,却不敢认。”华如便问:“是哪一个丫头,脚大脚小?”先生说:“是大脚的。”华如想大脚丫头有两个,不知他看是不是雪花。便问:“先生看见的这个丫头品貌如何?”孔先生道:“是张鹅蛋脸,脸上好像抹粉的一般,其余未曾看清。”华如便知道雪花。心想:“原来雪花亦逃在玉山,当时阿莲亦与雪花同逃,不知可在一处否。”
正在出神,先生便说:“你在此处还要读文章么?我是一身被他误了,并上海****看他不起。劝你不要读为是。”华如聪明人,晓得先生是呆读,不会变化,所以不能中。且于时文外一无所能,因此大营及上海两处不能容身。均不但不容,连谋生亦不能中。却不知读时文的中与不中,却在乎人之聪明,肚里变化。若不能变化,不但不能做时文,亦且不知何者为时务。又性子高傲,脾气狷介,深于理学,此种毛病均属难免。又读时文的人全是抄袭,并无真实学问,而自己却不知。偏说我于古今治乱,历代得失早已洞见曲折,且说书中记载无乎不有,绝不知移步换形。其实明人工时文的如金正希、黄道周诸前辈,均皆留心经济,晓畅时宜,虽工时文,却不像今日工时文的全无用处,反有坏处。此却非孔先生所知,亦非华如所及料。故孔先生劝华如之言,只说自己不中及不合时宜的苦头,却不知不通时务,即中了亦是无用。故华如听了孔先生说话未中要害,便心怪先生不善变化,所以不中。是仍在中不中上头分利害,并无人将时文无用,于国家利弊全无干涉的道理畅论了一番与他二人听。故如孔先生知他无用,仍然不知华如知时文在于变化然后能中,亦仍不知时文的害处。各人得的亦不同,此是后话。
当时华如听了先生言语,便说:“学生习时文另有一种时文,怕他不中了。若是三科后不中,再改业不迟。”先生说:“我看如今谋生,若不反,长毛退了,还是种田好。”华如道:“不中后种田不迟。我家田多得很,哪愁无田种。”欲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