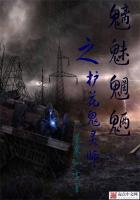宣和二年十一月初三,三河镇大捷。这是开战一年多来栖梧所得最大的胜利,伤亡比降至一比五。慕容流风所骑战马中箭失控,悲鸣一声将其颠下地来,使其被流矢伤了右臂,以至于之后几役均不在阵前。
宣和二年十一月初五。吴鹏进言皇后病愈,众臣连连称善,称其为大吉之兆。凤钦沅微微一笑,封赏甚重,当晚大宴群臣。吴鹏亢奋而归,与妾张氏缠绵卧榻,破晓时分才沉沉睡去。次日久不见醒,张氏小心翼翼近前,却发现人已冰凉。
宣和二年十一月初九,捷报又至。栖梧军心大振,凤钦沅更是龙颜大悦。殊不知曦凰早已兵分两路,大半军队绕道直逼伊歌而来。东粱守军发现端倪,大军已兵临城下,一时间,鼓声震天。
信使轻骑而出,才至城外数里便被埋伏在此的将兵发现了踪迹。正要射杀,却被一人抬手制止。黑暗中的侧颜,缓缓衍生出一个上扬的弧度。
“由他去。”
信使入宫之时,凤钦沅正在午睡,听到奏报,他匆匆起身赶至正殿。
“如此要情,为何迟迟不报?!”
那人忙稽首请罪:“靖宁王夜半突袭,我们根本抵挡不住。先后派出的五个信使,只有小人冒死......”
“你说,来者何人?!”凤钦沅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他最初三字之上。靖宁王,慕容萧!他不是回援了么,为什么会在此处?!
那人不解其意,以为凤钦沅没有听清,于是又提高声音重复了一遍。岂料话音刚落,桌上的纸笔奏章便被扫了一地。那方厚重的端砚,骨碌碌滚了几滚摔至他脚边,黝黑的墨汁狼狈地溅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泛出骇人的冷意。
须臾,又有内监来报。说城中有流言屡禁不止,数月前所谓的疫病根本就是无中生有,而凤钦沅身为一国之君竟自降身份,暗自遣使妄图以金银城池换得一方苟安。
反败为胜的喜悦骤然泯灭,从云端跌落谷底,凤钦沅感到了深重难堪的绝望。
宣和二年十一月初十,慕容萧发布檄文:凤帝逆天篡位,为君数载又德行有亏。然罪不及公卿九族,但凡不助纣为虐者,定既往不咎一应如前。当晚,内阁首府张凌正在桌案上发现了一封密函,之中含有凤钦沅继位前一年与颜氏合谋诬陷太子的证据。
次日早朝,众臣面面相觑,心中动摇者不在少数。且不说今上继位大有蹊跷,单单摆在眼前的内忧外患就够人恼。民心已失,军力不及,勉强抵抗不过是螳臂当车,徒增伤亡。慕容萧虽狂傲,但言出必行,所占城池秋毫无犯。
“皇上......”
“别叫朕皇上,朕马上就不是皇帝了,你们不用叫得这么好听。”凤钦沅冷哼一声,目光一一掠过诸人,似笑非笑,似怒非怒,最后,语气突然变得很倦怠。“你们想怎样就怎样吧,朕管不了,也不想管了......”
众臣不忍,想要说点什么,却被凤钦沅一个怒吼赶了出去。
殿门轻启,很快又再合上。眼中的刺痛尚未消散,黑暗已经悄无声息将他笼罩。昏暗的宫室,寂静如一沟绝望的死水。触目所及,皆是皇家专用的明黄之色。金线银丝密密斜织的龙纹衣袖,勒得他腕口生疼。
他开始回忆往事,回忆所有过去的美好,一桩桩一件件,细细地极认真地想。想自己年少轻狂春风得意,想那日春郊试马他溅了木槿花下的少女一身泥浆,再然后,便是他登基为帝俯瞰天下的那一刻,江山美人,尽入縠中。
他起身去抚殿中每一件摆设器物,最后,他将手放在暖阁柜中一个小木匣上。
“去,传各宫主位和所有年满五岁的公主。”
打开匣子,凤钦沅从中取出一个白底蓝花的小瓷瓶。拔了塞子,他缓缓将透明色的液体倒入酒壶。轻轻一晃,他将羊脂玉的酒杯一字儿排开,然后慢条斯理往里注酒。
半个时辰后,妃嫔公主陆陆续续到了。这是朝臣议事之所,向来不许后妃踏足,所以凤钦沅此举弄得众人一头雾水。
“皇上,人来了。”内监出声提醒。
凤钦沅却是摇头,仍专注于手中物事,对众妃爱女浑然不理。直到殿外几声轻响,这才笑着抬起头来。
明丽的红色,鲜艳如血。颜舜华后冠凤袍,莲步轻移,曼曼婷婷。云鬓黑亮如墨,面容白赛霜雪,步摇璎珞,环佩叮当。
宫中女眷少有见过她的,她们印象里对于皇后的感官全部源于传言,无非一个“怪”字,一个“贵”字,大不了就是很久以前被人嚼烂的那段关乎帝后的佳话。她们同样争宠,但从未把这名义上的后宫之主当回事。岁月是最可怕的毒药,任你花容月貌也终究抵不住似水流年。四十岁的女人,再美就是妖精了。可是颜舜华出现的那一刻,所有人都不由自主为她让出一条道来,看她的裙裾在暗金色的宫殿里勾勒出一朵又一朵怒放的玫瑰。
看惯了她素面朝天的样子,凤钦沅对于她今日的刻意也有片刻的怔忪。光阴荏苒,他却依稀看见了大婚时瑰丽明艳的少女。他伸出手示意她近前:“朕以为你会穿白色。”
“白色是给死人戴孝才穿的,皇上还没断气,臣妾怎好触这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