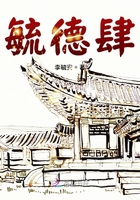曹植的“七步诗”——中国式的人伦压力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这是三国魏诗人曹植《七步诗》的“大众版”。据《世说新语》载,最早的原诗与之有所不同,且多出两句。不过,历经千年诗海之荡涤,却证明仍是这四句最言简意赅,接受了历史之考验。当然,在我们的古典诗歌研究中,甚至也怀疑这首诗是曹植的作品。但是,我们以下所要展开的解读赏析,则并不需要过多地介入这类纠缠不清的考证,本文从来就不是惟一的、永恒的,它本身只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框架,其中留有许多的未定点,期待着我们赋予不同的意义。就是说,这首《七步诗》究竟是不是曹植所作,诗究竟应该是多少句,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在于我们的确在“感受迷误”中重建了“曹植”的感受,也最终是较好地满足了我们自身的心理愿望,这就够了。
进入中国古代诗歌视野的有梅、兰、竹、菊、松,有“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但作为蔬菜的豆类则比较鲜见(王维“红豆生南国”是另一种“豆”),因而咏豆的名篇也就算这《七步诗》了。出现频率虽不相同,但基本思维却很有可通融之处,即都是把人的某些性格、气质、遭遇投射到客观自然的物象中,又在客观自然的物象特征中寻找与自身的相似之处。“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文心雕龙·物色》),如从松柏的遒劲有力、凌寒不凋见出挺拔不屈的品格,“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刘桢《赠从弟》)从荷花荷叶的独立特出见出洁身自好的人生态度,“多少绿荷相倚恨,一时回首背西风”(杜牧《齐安郡中偶题二首》),从汉妇辞宫感叹“士不遇”,“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王安石《明妃曲》),那么,豆与豆萁又让我们产生了什么样的“共鸣”呢?显然,它们既无奇巧的外表,也无让人浮想联翩的特性,真正的朴实无华,它们与人类主要保持着一种“实用”的关系。不过,对于普遍“实用化”的中国古代文化而言,“实用”之中照样可以产生诗意,而这种诗意也倒是更能显示出我们的实际生活状态。于是在曹植那里,或者更准确地讲是在我们理解中的曹植那里,豆与萁和手足相残的悲凉体验相互映射了。
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云云,帝深有惭色。(《世说新语·文学》)
豆与萁连枝同胞,唇齿相依,却如此的欺凌煎迫,这不正似中国传统社会中典型的人伦危机么?在中国封建史上,“三纲五常”的伦常格局带来的是对人性最大的扭曲和人伦关系的深刻异化。兄弟、姊妹、妯娌、婆媳这类人伦关系的生存距离切近,因而碰撞几率也大。“家”是中国文学永恒的话题,永远的原型,绵邈的象征。在家文化的领地上,多少瞬息风云、咫尺天涯,让人目不暇接,让人无可奈何!一段家的公案,引千年唏嘘感叹,乃至椎心泣血。手足恨豆萁怨即是“家”之中最具有悲剧色彩又最牵动人心的一幕。
只有理解作为豆萁故事的“原型”意义,我们才可以解释这样的事实:一首小小的且“出身”不清的古诗在大众传播中竟然是如此执拗地与曹植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是如此坚定地相信这就是曹子建的“七步杰作”;至于这位诗人构思更精彩、文笔更美妙的《七哀》、《白马篇》等反倒不具备如此广泛的大众传播效应。——我们确实在这样的文本阅读中构想出了一幅耳濡目染的兄弟相残的现实画面,我们日常饱受挫击的心灵在这一时刻,在一种有距离的观照中暂时得以解脱,并说服自己相信:我们可以寻找到那么一条解救之路,帝不是“深有惭色”了吗?似乎,超常的才智、一定的真挚可以唤起被扭曲的良知,从而缓解某些人伦的压力。
当然,这依然是幻想。
鲁迅“替豆萁伸冤”——戏拟中的创化
煮豆燃豆萁,
萁在釜下泣——
我烬你熟了,
正好办教席!
这一首诗是鲁迅在1920年6月5日所作。同《七步诗》一样,这首诗具有鲜明的现实讽喻性。抒情总是与一定的具体事件相联系,或者说,少有单纯的抽象的自我抒情。抒情因素容纳在某些现实感受的描述当中,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特征,也影响到现代中国旧体诗的艺术手法。鲁迅这首诗除戏拟《七步诗》外,“教席”一语也饱含着作者人生历程中最重要的感受之一:女师大事件。同年6月1日鲁迅在《语丝》发表《“碰壁”之后》,文章借杨荫榆“学校犹家庭”论提出,在女师大,校长与学生的关系即婆婆与媳妇儿的关系。婆婆“特请全体主任专任教员评议会会员在太平湖饭店开校务紧急会议”,这就是“教席”。鲁迅描述了这场“教席”:
我于是仿佛看见雪白的桌布已经沾了许多酱油渍,男男女女围着桌子都吃冰其淋,而许多媳妇儿,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运命。
除了这一显著的现实指向性外,鲁迅还引人注目地调整了豆与萁的位置。曹植是“豆在釜中泣”,个人感情在“豆”一面,是豆有冤,也是豆有怨;鲁迅是“萁在釜下泣”,个人感情在“萁”一面,是萁有冤,亦是萁有怨。在相同的话题范围内生发艺术原型是中国旧诗的传统。当然,这种生发有不同的方式,或者“正用”,即作为原型,作为相同的文化氛围、心理氛围被接受、被融解、被复活;或者“反用”,即在有意识的“反传统”当中寻求对原有话题的新开拓。鲁迅这一戏拟的“替豆萁伸冤”更像是后者。
但是,这也仅仅是“像”而已。南朝王籍《人若耶溪》云:“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北宋王安石“反用”道:“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钟山即事》)鲁迅“替豆萁伸冤”又分明不是这种刻意的“反传统”,不是这类挖空心思的别出心裁。王安石式的创新也终归只能成为搬弄词语和典故的游戏,测验学问的考题。而这很为鲁迅所不齿。——如果说曹植的《七步诗》本来就真诚地表现了传统中国社会的人伦危机,而历史的幽灵直到今天也仍然在中国的大地上徘徊,如杨荫榆等正是借家文化的人伦道德实现对青年学生的压榨、盘剥,那么又有什么必要来“反其意而为之”呢?艺术的创新一旦落入了逆反心理的窠臼就是最不幸的。
曹植借豆鸣冤,鲁迅替豆萁伸冤,这里丝毫没有逆反心理的作用。曹植以豆自喻,将曹丕喻为豆萁,豆与豆萁同根相生,豆责备豆萁不该如此的手足相残;鲁迅以豆萁喻无辜学生,但没有颠过来说杨荫榆之类是豆,杨荫榆与学生显然不是同根相生,不是手足之情,而是“苦节的婆婆”与“受苦的媳妇儿”的关系,所以鲁迅替豆萁伸冤,却没有硬找一个豆来反骂一通。在鲁迅看来,豆与豆萁既同根相生,那么命运不过伯仲之间!豆固然有被煎迫之苦,但豆萁亦有自焚之难,一烬一熟,最终不过是另一位得势者筵席上的用料。这样,关注中国人伦悲剧的鲁迅又从单纯的人伦搏斗的怪圈里挣脱了出来,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观照人生,他发现,在传统中国的生存方式中,豆与豆萁的“同级斗争”是一回事,但不同等级(阶级)之间利用各自的“地位差”而弱肉强食、恃强凌弱则更残酷,也易被充满奴性的中国人所忽略。被知县打过枷的仍然优哉游哉,被衙役占了妻子的依旧麻木不仁,但独对同级的“狂人”忍无可忍;阿Q对赵太爷、假洋鬼子低眉顺眼,惟视小D、王胡之类为眼中钉。这不正常!中国人要走向幸福的明天,就必须抛弃这类狭隘的、懦夫式的同级斗争,在等级金字塔内展开阶级间的斗争!这或许就是鲁迅接受阶级斗争学说的心理动因吧。
总而言之,鲁迅“替豆萁伸冤”,是在肯定了《七步诗》人伦内涵的基准上,又将中国的这一司空见惯的悲剧作了更深入的开掘,并上升到一个更恢弘更富有理性的层次上来全面把握。这里,与其说是有意替谁伸冤、翻案,还不如说是对自我命运的崭新揭示。如果就诗歌艺术而言,则又是对传统的一次成功的“创造性转化”。古老的家文化的公案,给现代人以新的激情、新的灵感。
郭沫若的“反七步诗”
——反拨中的回归
煮豆燃豆萁,
豆熟萁已灰。
熟者席上珍,
灰作田中肥。
不为同根生,
缘何甘自毁?
这叫《反七步诗》,郭沫若1943年创作。其新意不言而喻,较之曹植和鲁迅,郭沫若这首诗都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如果说在曹植的原诗和鲁迅的创新当中,都还共同持有这样的观念,即豆或豆萁的确蒙受了冤屈,理应有所怨愤;那么郭沫若则完全否认这段公案中有什么冤怨的内涵。“不为同根生,缘何甘自毁?”郭沫若认为:“站在豆的一方面说,固然可以感觉到萁的煎迫未免过火;如果站在萁的一方面说,不又是富于牺牲精神的表现吗?”
从手足无情、兄弟相残的控诉到对自我牺牲精神的赞誉,这个弯子转得颇大,熟稔《七步诗》的读者都不能不暗自惊叹:恐怕只有在现代中国,只有在郭沫若这位思维活跃的诗人笔下才可能出现这类挑战式的创新。
但是,仅仅如此我们就阐释了《反七步诗》的全部内涵,真正揭示了郭沫若诗歌的创作心境了么?我认为依然没有。有一个因素我们尚未破解开,那就是郭沫若的所有锐意创新的“翻案”作品往往并不是单纯文化意义上的冥思,而更具有某种特定的政治背景、政治内涵,不能捕捉这些诗歌中所蕴含的政治信息,我们的解读就终将是隔靴搔痒,未能进入郭沫若诗歌创作的无意识深层。
不妨追忆一下郭沫若这段时间的政治境遇: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匆匆回国,意欲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展雄图。1938年始,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就郭沫若以前的海外漂泊生涯而言,则似由“在野”进入了“执政”,或者说是由“处江湖之远”转为“居庙堂之高”,政治境遇的根本变化极容易在这位冲动型的诗人的精神世界激起层层波澜,重要的是他自己也比较能够迅速地领略这种变化的意义,并努力使自己从精神上调整方向,较顺利地适应环境。于是,《反七步诗》前后,郭沫若所从事的文化活动(艺术创作与历史研究)具有三个新的特征:(一)从早期“反抗不以个性为根的道德”、“反抗盛容那种情趣的奴隶根性的文学”转而强调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二)从早期对下层人士积怨的抒写转而阐发上层统治者的积极因素,甚至为历史上的奸臣暴君大翻其案。(三)个人生存观从早期的狷介、桀骜到呼唤自我牺牲、团结互助。
《反七步诗》是这些转变的艺术表现。在此时此刻的诗人眼中,郁郁不得志的曹植不仅不值得同情,相反,其卓尔不群都是“恃宠骄纵”的表现,后来受人猜忌也纯粹是咎由自取。(相应地,处于统治地位的曹操、曹丕倒“并不如一般所想象的那么可恶”!)《七步诗》显然也就是曹植“个人主义”的牢骚话语。于是,郭沫若决意要反其意而动,是为“反七步诗”,这样,《反七步诗》实际又成了郭沫若跻身政治圈之后对自身现有地位及所从事的社会活动作一“反驳性”的说明——从某种意义上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就是某种抛弃前嫌的兄弟会、将相和么?皖南事变后,周恩来愤而赋诗,也正是以豆萁喻国共两党。
不过,我认为,这仍然只证明了这首诗的独特的时代性和政治价值,并不能完全证明它的文化价值和文学价值。就诗歌艺术自身而论,郭沫若这一“反”虽新,却分明包含着我在前文所述的艺术逆反心理。如此反传统,似乎连艺术创作之源的个性生命也给反掉了,那么艺术、诗的立足之地又何在呢?政治斗争的标准是千变万化的,而艺术一经创立,则确定不移了;政治有可能给艺术、给诗以新的激情,但激情本身却也有可能误入他途。
由此我想到,中国诗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该多么有意义,却又是多么不容易建立起真正新的“意义”呀!一段老祖宗的公案,并非所有的后人都能参透,都能作出完满的破析。
(原载《名作欣赏》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