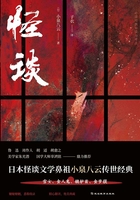——论《百合花》的谱系、技巧与主题
自从1958年3月在《延河》杂志刊发以来,短篇小说《百合花》就一直受到读者的喜爱和专家的好评。尤其是茅盾和侯金镜等权威人士的高度评价,不仅给这篇佳作带来极大的声誉,而且,也使它避免了可能遭遇的严重误读和猛烈批判。茅盾以激赏的语气肯定了茹志鹃这篇小说“清新、俊逸”的风格以及细节描写的成熟技巧。侯金镜也准确地指出了它的整体特点:“色彩柔和而不浓烈、调子优美而不高亢”;“对人物感情的客观描绘和作者注入到作品里的自己的感情,两者统一起来,就形成了委婉柔和、细腻优美的抒情调子”。但是,由于时代的影响,这些批评家在分析《百合花》的时候,既忽略了作家的精神气质和生活境遇与《百合花》的内在关联,“回避了小说家通过作品所要表达的对爱情和人性的理解”,也未能从文学的经验传承的角度,揭示《百合花》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关系。
那么,《百合花》与《红楼梦》的“谱系”关联到底是怎样的?作者的人生体验和精神气质对这篇小说的写作有着怎样的影响?《百合花》的技巧经验的特点到底是什么?在主题上,它是否还蕴蓄着没有被揭示的意义层面,或者说,是否还存在着更大的阐释空间?对于这些问题,本文将尝试着从《红楼梦》的经验资源里寻找答案。
一 《百合花》的文学谱系与茹志鹃的精神气质
1979年,冬晓向茹志鹃提出了这样两个问题:“你最喜欢看的是哪一类书?哪一个作家对你影响最大?”她的回答是:“开始时我只读《红楼梦》,在初中时一度喜欢过庐隐的作品。她写的作品不多,思想比较悲观、厌世,故事性不太强。听说这个作家后来自杀了。后来我读得最多的,一个是鲁迅的短篇小说,我觉得真是百读不厌;第二就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小说,尤其是那时的短篇小说,和他们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古典文学。这两方面对我的影响相当大。”我们可以从这段话出发,来研究茹志鹃所接受的文学影响,来寻绎和梳理她的文学谱系。
正像茹志鹃自己所说的那样,她的写作受到三种文学经验的支持。其中对她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无疑是“苏联”文学模式。收入《静静的产院》(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8月)、《高高的白杨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4年1月)、《百合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9月)和《茹志鹃小说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中的28篇短篇小说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属于“苏联”文学谱系的,因为,无论在主题上,还是叙事姿态上,它们都显示出与“苏联”文学的亲缘性和相似性——革命战争、政治生活和生产建设被视为重要的题材内容,用集体主义精神教育读者被视为文学的任务,对敌人的仇恨、对英雄的赞美、对领袖的崇拜则构成了作品的情感底色。然而,比较起来,她的这类以《里程》、《第二步》、《同志之间》、《新当选的团支书》、《黎明前的故事》和《给我一支枪》等为代表的作品,虽然也有一定的个性特点,但总体来看,价值并不很高,因为,它们不仅缺乏内在的深度和力量感,而且,风格上也缺乏变化,显示出较为明显的模式化倾向。
鲁迅无疑是茹志鹃喜爱的作家,但是,在新的写作模式的规范下,学习鲁迅冷峻的反讽姿态和深刻的怀疑精神,已经成为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茹志鹃按照“苏联”经验模式进行创作的较长时段里,她只是在《三走严庄》等小说里,借鉴了鲁迅小说的“第一人称”结构技巧和叙事策略。“****”浩劫结束以后,茹志鹃开始以怀疑和反思的态度审视复杂的生活和自己的创作:“过去,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用非常天真非常纯洁的眼光来看社会主义,歌颂那些美的东西。……现在在我的作品里慢慢出现了另外一种主题,就是反面的东西,要鞭打的东西,出现了。这在我过去的东西里,在《百合花》的集子里,是很少的。但现在经过‘******’这十几年的摧毁破坏,如果还看不到这一点,还是一切都好,一切都歌颂,起码是脑子太迟钝。”这种反思给她的写作带来巨大的变化,开启了她的反讽写作的新阶段。1979年1月,她写出了第一篇具有反讽意识和批判精神的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虽然这篇小说的反讽,像聂华苓所说的那样,不过是一种“温柔敦厚的讽意和诙谐”,但是,对茹志鹃来讲,却标志着写作路向的重大转折。此后,她的写作便极大地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消极影响,表现出对个人遭遇尤其是知识分子命运的热情关注。在短短的时间里,她先后写出了《草原上的小路》(1979年4月)、《着暖色的雪》(1981年4月)和《家务事》等叙述“反右”和“****”期间知识分子命运和境遇的作品,表现出对极左政治进行反思、对特权和腐败现象进行批判的自觉意识。
从文学谱系上看,独石成峰的《百合花》则属于另外一种文学传统和气质类型。它是《红楼梦》的孩子。这个文学生命的诞生,其实是一件极为自然的事情。因为,《红楼梦》是茹志鹃读得最早最多,也是与她的精神气质最为契合的作品。《她从那条路上来》是茹志鹃篇幅最长的小说,也是一部自传色彩最浓的作品。在这部小说里,那个名叫也宝的小女孩“从刘先生那里借到了一部《红楼梦》,一有空就看得如醉如痴”。事实上,茹志鹃自己就是这样读《红楼梦》的。她说“像《红楼梦》我看过九遍,里边的诗词一类的东西都背过。虽然很多东西当时我并不理解,但我喜欢,多读多背慢慢就理解了”。她写过一篇题为《紫阳山下读“红楼”》的文章,比较详细地记录了《红楼梦》对自己内心生活的巨大影响:“在那个时候,在紫阳山下,‘红楼’真像一股清泉,滋润过我,支持过我,使我在那样一个世界里,鼓足了勇气。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对那种半饥半寒的生活,尚能留下一抹美好的记忆,连同那个光秃秃的紫阳山在内。”其实,《红楼梦》对茹志鹃的影响,绝不止于此。她在《百合花》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生活的温柔而细腻的情感态度,那种从容、优雅的叙事语调,那种对于美好事物的精微的感受能力和充满诗意的表现能力,都无疑是受了《红楼梦》影响的结果。虽然,在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正像茹志鹃在一篇《后记》中所说的那样:“连《红楼梦》都带上了‘黄色’的帽子,我这一点点小不点儿的东西,又何足道哉!”但是,茹志鹃还是利用女性特有的感受能力,凭着她的不俗的才华,从《红楼梦》里获得了足够的经验支持,从而最终将自己的《百合花》作品,光荣地归入了《红楼梦》的精神谱系。
虽然,比较起来,茹志鹃与张爱玲都曾接受过《红楼梦》的影响,都从《红楼梦》里获得了文学的真传,领悟了小说的神髓,但是,她们吸纳到的东西以及表现这种影响的方式,却很是不同。如果说,《红楼梦》对张爱玲的《金锁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外在的语言层面就可以看出来,那么,在《百合花》里,由于叙事形制的短小,由于受特殊的叙事内容的限制,《红楼梦》的影响却是潜在的、隐约的,需要仔细地体味,才能感受得到,才能发掘出来。如果说,在写作《金锁记》的时候,张爱玲学会了《红楼梦》的从“背面”观察人性之恶的能力,对那种“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乌眼鸡一样”的生活有着深刻的洞察,从而能将曹七巧的泼辣、粗俗、恶毒写得令人不寒而栗,能将种种的算计、争斗、较劲写得如此淋漓尽致,那么,茹志鹃则学会了《红楼梦》的从“正面”感受人情之美、人心之真、人性之善的能力,学会了捕捉和表现童心般纯洁而美好的情感,学会了用细腻的充满诗意的文字,表现青年男女的混和着喜悦、羞涩、误解与和解的复杂而微妙的心理活动。
其实,就其天性来看,茹志鹃本来就是具有“红楼”气质的人。用母性的温情的目光看世界,爱一切美好的事物,具有内倾的感伤主义倾向,这些弥散在《红楼梦》中的精神之光,在茹志鹃的内心世界,似乎都可以看得到。王安忆在分析母亲茹志鹃的日记的时候说:“我应当承认,我妈妈身上带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分,她受教育并不多,可她喜欢读书,敏于感受,飘零的身世又使她多愁善感。年青时代的她,甚至是感伤主义的。她喜欢《红楼梦》。……虽然是在动荡和困窘中的少女时代,无一刻不为生计所苦,但我妈妈依然保持了清丽的精神。生活的压榨没有使这精神萎缩,反而将它过滤得更加细致和纯粹。这源于天性的结果。我妈妈天性严格,对感情要求很高,她生来不容忍低级趣味。”内心纯洁的唯美主义者和慈悲为怀的人道主义者,往往很容易成为世间最不快乐的人,因为,他更难忍受那些低俗和冷酷的东西,对世态的炎凉和人间的不幸,也更为敏感。所以,在女儿王安忆的眼里,茹志鹃自然就是这样子的:“她一直不快乐,甚至是抑郁的,住在人家家里,别人无意的一句话,都会使她流泪,引起她对身世的感触。她真有点像林黛玉了。”
从茹志鹃自己的日记里,人们看到的,则不仅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甚至还是一个有着悲观厌世倾向的人。1954年7月22日,茹志鹃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夫妻相对默坐,仍觉有趣,此乃好夫妻也;如夫妻相对默坐,双方觉得闷闷,或想找话说,或想找朋友玩,此乃恶兆。”这里多少透漏出了她对自己的婚姻的失望,透漏出了她自己在日记中多次宣泄的因夫妻关系不睦而来的内心苦闷。同年8月2日,她在日记中写道:“这几天,两个孩子生病,烦得我心神不宁,不想睡不想吃,如我有病的话,有谁来为我呢!真是‘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寥寥数语,道出了无尽的忧伤和深深的绝望。孩子的入托,也会给敏感的茹志鹃带来巨大的不安,也会使她对自己的未来产生悲观的情绪和消极的联想。她在9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为什么呢?为什么心会这样难受?我想到一个人也没有的地方去痛哭一场,倒也许会痛快起来。
四年前的今天,我正在那种幸福的朦胧中,又带一些淡淡的离愁,想不到四年后,我会变得像今天这般,人生啊!你将还给我多少经历和苦恼呢!我似乎已经厌倦了,对一切都厌倦了。
将我的能力,除了为人民服务外,能得我和我孩子的温饱,安安静静地过下去,也不希望从谁身上取得幸福,等孩子长大了,飞去的时候,我也将离开这个人生了,人生的全面貌已显示给我看,就是这副样子。
我可能是在胡说,不过这是我现在心中真实的话,即使不对也让它留下痕迹吧!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敏感气质,茹志鹃才在人人自危的时代,在独自向隅的寂寥的夜晚,在对往日生活感伤的追怀中,看见了青翠水绿的庄稼,闻到了清鲜湿润的香味,发现了三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一个小战士与新媳妇和“我”——之间的微妙的心理碰撞与情感交织;也正因为有着这样的气质,所以她才能打通时代与《红楼梦》之间的高高的界壁,写出了《百合花》这篇抒情诗一样优美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纯洁无瑕的爱的故事。
二”摆事实”:茹志鹃领悟到的《红楼梦》经验
从风格和技巧上看,《百合花》尽管通体弥散着浓浓的诗意,但是,它却清纯自然,不事雕琢,体现出一种令人赞叹的朴实与优雅。联想到它所产生的1958年,联想到那个时代喧闹、夸张、浮薄的风气,它所表现出的克制和平静,实在是难能可贵。
那么,从艺术上看,《百合花》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呢?它是从哪里来的呢?
《百合花》成功的经验,就是用白描手法对人物和物象进行简洁而准确的描写。这种由《史记》和《红楼梦》等经典作品传承而来的描写技巧,“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极大地过滤了作者的简单而随意的主观判断,排除了作者的缺乏真实性的消极想象,而是以一种切实、客观的方式,来写人物的神态、语言和动作。聂华苓在评价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的时候说:“这篇小说所表达的是客观的‘真实’,而不是作者现身说法主观的‘真实’。”事实上,早在《百合花》中,茹志鹃就已经开始这样写了,而且达到了极为成熟的境界,取得了令人赞赏的叙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