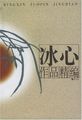在古代,从沙场凯旋的功臣,往往会得到皇帝的隆恩渥泽,要么御赐九龙辇和黄罗华盖,要么特许佩剑上朝,赞拜不名,入朝不趋,要么颁他一张“有司不得加责”的“丹书铁券”免死牌,总之,世俗世界的安富尊荣,可谓“蔑以加于此矣”!自打获了“诺奖”,莫言也成了与瑞典皇家“剖符作誓”的功臣,不仅获得了批评的“豁免权”,而且被赋予了不容怀疑和不容否定的绝对“正确性”。试看今日之宇中,还有几个中国学者和批评家敢说莫言的作品写得烂?
一个神话人物一旦产生,参与造神的所有人,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有为他辩护的责任和义务。倘若有人肆无忌惮,横加议论,就不仅是对神话人物的不敬,而且还是对神话制造者的冒犯。这样,你就不难理解,“诺奖”评委马悦然为何要无原则地为莫言辩护了。在马老先生看来,如果谁敢质疑莫言,敢对他有否定性的评价,那一定是谁的理解能力有问题,谁就一定要向被冤枉的莫言道歉。
上海的许纪霖教授,属于为数不多的敢于尖锐质疑莫言的学者。2013年1月18日,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访谈的时候,他从知识分子人格的角度,表达了与高度评价莫言的刘再复先生截然不同的观点。在他看来,做为公共知识分子,莫言的某些行为是让人失望的,而他的某些作品则俗不可耐。他用“平庸的乡愿”来评价莫言。他说:“90年代到今天,我觉得最大的伤害就是,犬儒和价值虚无主义盛行。”他怀疑“诺奖”的权威性和普遍有效性:“诺贝尔文学奖不过是欧洲一些学者、文学评论家以他们的眼光看出来的一个标准而已,多多少少有点东方主义的偏好。如果我们把这种偏好看作是最高的、唯一的价值标准,那么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文化就失去了自主性,所以我没有看得那么重。但从莫言得奖以后,上上下下引起的狂热来看,这恰恰是中国今天精神堕落的一个标志,失去主体性堕落的一个标志。”在一篇发表于2012年10月12日的题为《我为什么批评莫言》的文章中,他这样说道:“我并不期待得奖后的莫言能够成为‘中国的良知’,那是太高的道德要求,我只希望这位被许多人喜爱、并且引为国家骄傲、中国崛起的标杆性作家,能够自珍自爱,爱惜自己的羽毛,守护自己的信念,生活在真诚之中。这也是对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包括对我自己,让我们相互激励、相互监督。”
然而,马悦然先生无法理解许纪霖教授的焦虑和愿望,也无法接受他对莫言以及“诺奖”的批评。在题为《许纪霖教授欠莫言一個公开道歉!》(2013-02-23 05:33:39)的博客文章中,他在细致解读莫言“打油诗”的同时,批评许纪霖教授“在2012年12月16日与香港中文大学陈韬文教授公开对谈讨论莫言时”,严重误读了莫言的诗,因此,他最后的结论是:许纪霖教授“欠莫言一个公开道歉”。
马悦然的辩护显然具有打群架的性质。他的爱憎分明,他的挺身而出,虽然有一股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豪侠义气,但是,从文学批评的立场看,这种文过饰非的曲意回护,却实在是很有害的,实在是很要不得的。
马悦然在博客文章中所解读的那首诗,就是莫言的《打油诗赠重庆文友》:“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白蛛吐丝真网虫,黑马窜稀假愤青。为文蔑视左右党,当官珍惜前后名。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这首不顾平仄、不合格律、干瘪乏味的打油诗一发表,便引起成千上万网友的“围观”,也引发了不少人的尖锐质疑。网友戴建业跟帖:“这不能叫‘打油诗’,只能算‘打地沟油诗’。莫言先生还是不要写诗为妙,以免我读了他的诗以后不想再去读他的小说。”网友梦笔生花则质疑作者身份的真实性:“不相信,这么拙劣的诗歌水平会出自一个诺奖获得者,是山寨莫言吧。”
然而,在马悦然看来,包括许纪霖教授在内的许多人,都没有读懂这首诗,都误解了莫言,冤枉了莫言。八十八岁的“诺奖”评委慷慨激昂、言之凿凿地说:“对于一个平常智力而有基本汉语常识的读者,莫言的诗显然都不应该看作歌颂的诗歌,而应该是讽刺,对薄熙来有严肃的批评,并且莫言警告自己的朋友不要卷入重庆的唱红打黑运动。”遗憾的是,他的想象过于活跃,他的理解过于随意,他的最终判断,因为基于想当然,则属于“过于执”一类。
莫言写作此诗之际,正当“唱红”活动歌声嘹亮、响遏行云之时,正当“打黑”行动缇骑四出、势不可当之日,当此时也,所谓“讽刺”诗,借莫言十个胆,他也不敢写一句。事实上,像许多被蒙蔽的人一样,莫言也看不到“红”背后的“黑”,看不到“黑”之下的“打”,所以,他表现在诗里的情感态度一目了然,就是肯定的和歌颂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固然无须苛责他,但也不能因为他是莫言,就将事实和真相“一床锦被遮过则个”。
马悦然别出心裁,将莫言的八句打油诗分作“两段”:“第一段是清楚地批判薄熙来和他的运动:第一句:‘唱红打黑’诠释了薄熙来呼吁恢复****精神的口号;第三句:包括对网络上支持该运动的疯狂行为的一条说明;第四句:‘窜稀’(黑马)是指过去无名小卒目前在薄熙来王国之统治下获得声望的人,其行为就如**********中的‘愤怒的青年’。”诗歌要靠意象来表达情思,其意蕴具有一定程度的多义性和模糊性,因此,才有“诗无达诠”、“诗无达诂”之说,但是,这并不是说诗可以妄加臆测,可以像马悦然先生这样随意阐释。莫言的这首诗,虽然也有一点儿曲言隐喻的“比”,但基本上属于直言其事的“赋”体,大体意思昭然若揭,并不难懂。
“唱红打黑声势隆”,这句话像新闻报道一样准确地陈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此“声势隆”的“运动”,是非同寻常的,是很能吸引世人的眼球和注意力的。于是,这才有了下一句:“举国翘首望重庆”。如果说前一句还只是客观的描述,那么这一句就彰明较著地显示着莫言“歌颂”而非“讽刺”的态度。在汉语里,“翘首”和“望”通常都与值得期待的美好的人和事物相关联,表达的是渴望见到的迫切心情。例如,“翘首以待”(be on the tiptoe of expectation),意为抬起头望着远方,形容殷切盼望的样子;例如,“翘首跂踵”(语出宋人王明清《挥麈三录》:“天下之士翘首跂踵,冀阁下日以忠言摩上,不谓若今之为起居舍人者,止司记录而已也。”)则是抬着头、踮着脚后跟望着远处等待。“举国”而“望”,则所“望”者,必是非同小可的事物,必是值得“歌颂”的事物。马悦然在阐释的过程中,完全忽略了这近乎“诗眼”的一句,实在粗疏得很不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