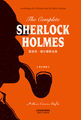郑仲兵
这是一篇难得的富有特色的真实再现“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太行山区一个边鄙山村农民苦难生活的小说。“文革”结束38年来,反映“文革”的作品本来就不多,有也是多为反映知青上山下乡生活和知识分子干校生活以及红卫兵从造反到挨整等题材的伤痕小说或灾难小说。而真正反映农村农民在“文革”中生活的题材,实属鲜见。
小说散发着浓烈的乡土气息。不论是环境的描写、人物的刻画﹙包括人物形象和性格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安排,还是语言和文字的应用,四者浑然一体,都充满着乡土味。
翻开这篇小说,令我不忍释手,一气读完。我有一种奇特感受,让我想起少年时代读过的鲁迅介绍的《何典》。《何典》成书于清朝乾嘉年间,是一部滑稽讽刺的中篇小说。通篇用的是吴地的方言俚语,甚至不乏脏话亵语,人称“鬼话连篇”——通篇说鬼,却深深道出了那个年代的世态人情。它画的是鬼,却越看越像人。
《驴》也用了大量井陉地区的方言俚语,人物对话中也有一些粗鄙的脏话,也给人以滑稽谑趣。但与《何典》相反,通篇说人——人话连篇,却越看越不像人话。画的是人,却越看越像驴。同样深深道出那个地区、那个特殊年代的世态人情。
记得《白毛女》里有句话: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可是当我们考量了历史——从建政、土改、社会主义改造,从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却看到一种莫大的历史讽刺——事实上是让人异化成非人,把人变成了鬼,变成了牲口,变成了驴。
不断的革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祸乱,造成社会、人、人的精神、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包括两性关系﹚的异化,在这篇小说中得以充分展示,真实的展示。人道的缺失,极端革命功利主义的张扬,社会关系中质朴的人情、亲情、乡情被否定,人伦、人格、人性的全面扭曲和变态,以及农村从物质到精神坠入原始、封闭、愚昧、野蛮、荒诞、黑暗的世界。造成人驴不分,人不如驴,人变成了驴。
当然,小说就是小说。把小说当成政治,认为“文艺即政治”、“用小说来反党是一大发明”,恰是蒙昧、野蛮、荒诞时代的意识形态。这是我们经历了解放后,特别是10年“文革”的血泪教训。我之所以要说说这个题外话,是因为直到今天,还有自我感觉很好的人,对文学表现如“反右”,如“文革”的灾难,说三道四、上纲上线,重复那个时代荒诞的意识形态的言语,还搬出所谓“苏东教训”。这些人的僵直的脑筋,根本不懂得总结、认识历史曲折、历史灾难,对于开辟正常的未来是多么重要!
我想起朱厚泽﹙1985.7—1987.1的中宣部长﹚曾对我说过,他刚到中宣部不久,与天津作家交谈的情景。
一位女作家对他提意见:你们中央太重视文学了!
朱厚泽笑道:你这个同志真怪,人家都嫌中央对文学重视不够,你怎么会说太重视了?
她说:政治上出问题了,也要怪作家,一篇小说、一首诗、一部电影,也被认为会亡党亡国,整天盯着作家和作品,岂不太重视了。
朱厚泽当然理解她,他当然知道政治上出问题,要从政治上找原因,要从政治体制上找原因。他对他们说:文学艺术创作,是最有个性特色的精神活动,它最不能按照订单来“加工订货”进行生产。文学、艺术、戏剧是最不能按样板定做的;刻出一个模具,冲压、锻压是不会得到成功的。我们应当营造一种宽松和谐的环境和氛围,使整个思想文化界能够在这种环境和气氛下,互相理解,相互依赖,积极进取,生动活泼地进行探索和创作。
朱厚泽这番话是27年前讲的,我觉得在今天还是有启示意义的。我赞同他的认识。
小说就是小说,它的主体功能就是艺术功能、审美的功能。它也可以发挥其他的功能——历史的功能、政治的功能、教育的功能、道德的功能等等。但它不是历史,不是政治,不是教育,不是道德。小说是一种语言艺术,一切其他功能都要通过其艺术、审美功能来发挥,来起作用。所谓文以载道也。它的真谛在于真善美——求真、善的寄托和美的给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