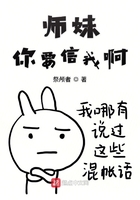让大七子始料未及的是,第二天中午,神通广大的络腮胡子司机带着车主竟然在街上找到了他。车主慷慨解囊,请大七子在酒店里撮了一顿。酒足饭饱之时,还交给了大七子一个红包,说是“不成敬意”,还望“日后多多关照”。钱虽然不多,只有四人头的一张大票,惊讶不已的大七子还是从中看到了某种制约的力量。
激发了热情的大七子在老槐树下转悠的次数因而多了起来。“敬请笑纳”的红包散发的诱惑力使他情不自禁地陶醉不已,而渐渐多起来的红包毕竟也是不要白不要、多多益善的事,你能送,我就能收,只要你认为值就行,不就那么回事吗?这种天上掉馅儿饼的事让大七子乐在其中,晕晕乎乎地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后来的许多时候他都觉得那段出手大方的日子过得特别开心。
岂料,整治路况、打击车匪路霸行动才刚刚开始,正在做着美梦的他就被掏进了派出所。这才知道,这种钱不是那么好赚的,他收的实际上就是“保护费”哩(尽管这是车主们自愿相送,他没有丝毫强迫的意思,但这种自愿相送不正是来自内心对他的畏惧吗)!与“吃黑”的性质相同。说到“匪”“霸”,大七子觉得冤枉,可大七子最终不得不低下了头。在他的潜意识里,“匪”“霸”都是扰乱社会秩序的下三滥玩意儿,人们唯恐躲避不及,而他自己向来也是深恶痛绝的!
后悔不迭的大七子走出派出所后,发誓痛改前非不再干那些乌七八糟没屁眼的事。他脑瓜灵,虽然一头栽在路上,一跤跌倒之时却也发现搞客运实在是件不错的活计,每天都有不菲的收入。于是,哥儿几个一商量,你三千他五千地凑足了钱买了一辆二手依维柯,在派出所的大力支持、帮助下,迅速办理了准运证等一应手续,满面春风地揣着驾驶证上了路。
与众不同之处是,大七子依维特的载客量总是比其他车的载客量要多得多。这一方面是个体司机心有忌惮不敢明目张胆地跑在前面与他争乘客,另一方面也与他那几个动不动就伸胳膊捋袖子的合伙人不时来“站牌”下转悠有关。大七子的车每天早晨七点半准时朝县城方向发车,十点左右开回——径直朝临湖镇开去,下午一点光景返回——朝县城方向进发。每到这些钟点的时候,大槐树下总有许多等车的人,虽然有车已赶到了这儿,但开车的司机就是不让人上车,有些路过的车甚至连站一下的想法都没有,干脆一溜烟儿似的开过去了,招引得性急的旅客追着车撵,竟也无济于事不为所动,直到大七子的车卡着点开来,一切才恢复了原有的秩序。据说,有不识相的司机、售票员也曾在这个钟点大呼小叫地揽过客,但第二天就遇到了麻烦——不是被人找了个碴儿教训了一顿,就是轮胎突然起爆被人暗算了。心有余悸的司机们脸上表现出的恭敬使得大七子风光万分,全然没有想到其他。好景不长,敢怒而不敢言的司机们虽然当面奉承他,背地里却牢骚满腹,不知是谁还给有关部门写了封匿名信。一来二去,便惊动了派出所,麻指导员不仅暗地里考察了一番,还特意找到了他,和他进行了一场十分严肃的谈话,指出了这种行径的恶劣性。装了一脑瓜子怨尤的大七子悻悻而回后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将他的合伙人们照样狠捋了一顿,勒令他们不准再去大槐树下帮倒忙,给自己上眼药。合伙人虽然不去大槐树下帮衬、助威了,但大七子的负面影响仍像幽灵似的在大槐树下徘徊不去,只要大七子的车一到,司机们依然故我,该迁就的迁就他,不该迁就的也一味让着他,有客仍然给他留着,有笑脸仍然给他上着。蒙在鼓里的大七子不知他们使的是请君入瓮之计,一根肠子通到底的大七子根本看不出笑脸的背后是一把看不见锋芒的软刀子——怨声沸腾的司机们虽然敢怒而不敢言,私下里却已商量好了,集体用谨小慎微的战战兢兢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以软制硬地让大七子开不成车,将大七子彻底撵出这条线路!有道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啊!绝不养痈畜疽的客运部门果真采取了果断措施没收了他的准运证,威风扫地的大七子虽有口却难辩,只得灰溜溜变卖了依维柯,老老实实待在了家中。司机们则皆大欢喜,虽然见了面仍旧拿足够的殷勤奉献,私下里却无不弹冠相庆。
大七子不跑车了,但生活无着的大七子经人指点终于发现了松树山可供开采的天然优势——也就是说,时刻都想干点事儿的他由此了然了生态养殖的价值,认识了驱逐帅开文的意义。有明白人支持,他当然********甘愿充当马前卒!
然攫戾执猛的他乘兴而去,不仅未能将彬彬有礼的帅开文挑落马下,反而一头撞上了令他气不得、发作不得的软钉子,只得败兴而归。而出谋划策者竟也“嘿嘿”一笑了之,并且一再叮嘱他“少安毋躁”,点到为止不必再“轻举妄动”,好像此举已大功告成。真不知道这半神半魔的人精葫芦里装的到底是什么药!
今晚,闲得无聊的他将往日执鞭随镫的几个好哥们叫了过来,说是喝杯酒、打打牌乐呵乐呵,其实是商量商量松树山的事——年关可是越来越近了——稍安可以,毋躁可不成呐!
可白酒喝了一瓶,黑杵也打了几圈,车轱辘话从酒精的燃烧中转移到了敌手不断更换的对垒、抗衡上,仍然没有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手气不顺,接二连三输了几把的大七子恼了,胡乱地洗洗牌朝桌上“啪”地一掼道:“你们是不是脑子都进水啦?就知道耍横的来邪的,捣捣乱、放放火、下下毒药什么的,那是什么?下三滥的玩意儿!你们还有没有王法呀?要动心眼子!懂吗?连那些一身汽油味的车夫子都知道以退为进,让咱们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你们就不能仿效仿效让他帅开文知难而退、拱手相让?”
好不容易当了一把“皇上”,终于有了进项的陆尚云脸上的灿烂之花刚刚盛开,一下子就蔫巴成了扒了秧的茄子、经了霜的山芋藤,嘟嘟囔囔地说:“咱的拿手好戏叫‘逼宫’!不来邪的横的能行?好比打杵,双杵被人家帅开文抓去了,揿了,亮了,又抓了一手能攻善守的好牌,撂在谁身上谁心里能底气不足?谁也不会缴械投降呀!上几句好话他就知趣了?他咋那么傻呀!”
“可是,倘若他抓的那手好牌中,鸡零狗碎的3、5、7、9谁也挨不上谁又有什么用,不是负担?咱们呢,上家老给他出联子,出对子,下家又攥着炸弹专炸他大牌,他的双杵再管用,充其量只能管一回!”
二癞子的虾米眼又眯了起来。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卖什么关子?说,什么联子、对子、炸弹?”
大七子精神抖擞起来。
“村人嘀咕出的怨气不是联子?放牛的好地场没了,只能牵着不能撒了,哪家哪户不怨气冲天?小雨、大雨一下,黑亮亮的地达子(地衣)不能捡了,肉嘟嘟的蘑菇不能摘了,眼睁睁的谁不怨声载道?偌大的松树山就那么一点儿买擦屁股纸的承包费不是对子?能与家家户户损失的方便相比吗?当然了,靠这样的联子、对子绝对赢不了他,还得要有威力强大的炸弹!至于这炸弹嘛……”
“又来了。玩什么深沉呀,说哇!”
“勾引有夫之妇不是炸弹?”
“你是说……”
“管月翠那天上山的事你没看见,你能说其中没藏着猫腻?”
“****,那叫什么炸弹哇?谁都乐意的事!”
“谁都乐意,可有人不乐意!”二癞子用含蓄质询大七子的不以为然,“你不当回事,屁都冲不得一个的陆尚能能不当回事?”
“打住打住。我可警告你啊,别屎不知在哪儿屁就乱炸!”大七子急了,面孔骤然板结起来,眼睛也瞪了起来,“别开口闭口一句一个陆尚能的,这件事扯不上他!”
“为什么?”
二癞子一头的雾水。
“我说你们是猪脑子吧?明杵暗杵作用相同?”
陆尚云说:“七哥,你越说我越糊涂了,转弯抹角、云云雾雾的,这不是你一贯风格呀!能不能交个底儿让我们心里也踏实踏实?”
“不能!”大七子故弄玄虚地一笑道:“该知道的到时自然会知道。不过,我可以提醒一句,帅开文的那句话还记得吧,松树山交给我们,你能经营,我能管理?”
二癞子顿开茅塞:“哦,我明白了,你之所以有此一想,是有人能经营会管理?我想,这人十之八九是能哥吧?”
大七子将牌洗得“哗哗”直响,很有几分按捺不住:“没有金刚钻,能揽瓷器活?嘁!继续,啊,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