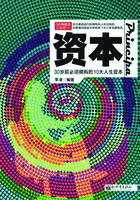“少安毋躁,听我把话说完。”帅开文的手不容置疑地朝下一按,示意他安静、坐下。“你们也看见了,偌大的松树山被铁丝绳、尼龙网拦腰切断了——另一大半闲置了。为什么会闲置?不怕你们笑话,实在是兜里没几个子儿,阮囊羞涩哇!这其实也是一种资源浪费。你们要养鸡,好哇,正好可以开发利用,我们做邻居,何乐而不为?为表示支持,我不准备收取任何费用!可是,听了你们一席话,我的心凉了半截。如果就这样草草上马,后果将不堪设想——第一年我盘算得那样周到、计划得那样缜密,还因事到临头被接踵而来的各种措手不及打得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哩,何况是知识储备、常识积累都严重不足的你们?所以,为慎重见,妥当考虑,我倒有个两全其美的建议……”
“什么建议?”
“不妨先实习实习。一来我可以鼎力相辅,提供必要的援手、帮助;二呢,你们也好慢慢熟悉程序、掌握规律为今后的顺利养殖打下坚固的基础,减少因不必要的盲目造成的无谓损失。”
“就是说让我们先来给你打工?”
“可以这么理解!”
“想得倒美。告诉你,”大七子流里流气的目光顿时像出鞘的刀子在帅开文的脸上剜来割去,冷笑了一声道,“我要的是松树山全部,不是局部!是你的卷铺盖走人,不是你的分封割据、分庭抗礼!今天算是下下毛毛雨,提前打个招呼,你呢,可以结合自己的利益前思思、后想想,反正我有的是时间等。告辞!”说罢,旁若无人地打了一个响指,突然又意识到了什么似的转身恭恭敬敬地朝着管月翠会意地一笑,随之跩着摇摇摆摆的鸭步扭头就走。
28.一切就这样发生了
“奇怪,大七子咋对松树山养殖场产生了兴趣?”望着他们扬长而去的背影,管月翠不无担心,“这小子可是个生冷不忌、浑身有刺的主儿,不达目的是不会就此罢手的,你可得当心点儿!”
身在其中,帅开文想得自然就多了些。“是否生冷不忌、浑身是刺倒不可怕,可怕的是暗中下绊子使坏!别的且不说,随便在铁丝绳、尼龙网上扯一个窟窿、剪一道口子,这鸡呀兔的能不钻出去?钻出去了到哪地儿找去?所以,我尽可能的不得罪他们,力图顺着他们的心愿说,真心实意地替他们支招儿、想办法。可他们哪是干事儿的呀,分明是来捣乱、添堵的!我怀疑是不是有人看我不顺眼,有意从中作梗!否则……”
他忽然意识到了什么,话到嘴边又生生咽了回去。
“否则什么?”
她追问。他心中有阴影,她心中也有阴影,只不过她不愿将那种阴影与他那种阴影摞叠、合并而已。只重内容不重形式的那个人是干大事儿的,不可能在这种不起眼的小事上耗费巨资、浪费心力吧?她虽心有怨怼,却也不愿将那个人想得太坏。
“恐怕我得罪过谁、让谁记恨了!”帅开文敏感地转换了话题,“否则,对养鸡一窍不通的大七子为何如此理直气壮、盛气凌人,而且一甩手就能拿得出五万元的票子?”
盐从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心有五味的管月翠其实已隐隐猜出了谜底。一贯提着小心、以免口舌招尤的帅开文不可能点燃自毁其利的烽火,大七子也非是嫉妒得了红眼病,唯一的可能只能来自自己与帅开文的关系——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哇(否则,言语无状的大七子为什么会像狼盯上了羊似的盯上了孤掌难鸣的帅开文?他的堂而皇之的底气又是从哪儿来的)!想虽这么想,但说出口的话却是:“你估摸得罪过谁?”
帅开文大度地一笑:“猜测只能使幻影迭生,心里黑暗,不说它了。”他突然将柔声捻成了心语,“能在松树山看到你就是我最大的快乐与满足,其他的事则不足挂齿、无需介意,不要影响你、我此时的好心情!”
管月翠白了他一眼,两朵红云又洇上了脸颊。
他知道她是不会无缘无故上山的,上山肯定是有不便表达的话要和他谈。管月翠艳如桃花的羞赧表情证实了他的猜测、判断,也让他看出了他在她心目中的位置。
谁知,心中倒海翻江、一时不知如何开口的管月翠却蓦然间悲从中来,眼圈儿竟径自红了。
她想说什么?她要说什么?她心里又藏着什么样的委屈、何等的愤懑让她觉得无法自控?
帅开文赶紧领她进屋坐下。殷勤地为她烧开水,沏茶。香气扑鼻的茶端到了她面前,却没能绽开她的笑脸,眼睑下的两行清泪竟越流越长。
他手足无措地望着她,不知道这变化意味着什么。
泪眼婆娑的她痴痴地望着茶杯里渐渐泛绿的水,失去了落点的心绪像浸泡的茶叶在慢慢伸展。从双肩的一耸一耸中可以看出,她心里翻腾的,是太多的苦涩与辛酸。
他虽不明所以,却也知道定然事出有因。她的身体每每抽动一下,都像有根尖刺在他心里戳扎了一下;她双泪的流每每在下颏聚成了滴,他舌尖上的味蕾便生出了酸涩的苦。她喁喁地向他敞开一直紧锁的心扉,为他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关钥大门。让他吃惊的不仅是陆尚能的卑劣用心,更是她滴血的心里积聚的累累伤痕!他不无珍爱地拥住了她,像拥住了一头受伤的小鹿。
她就那么温顺地将一头的秀发挂在他的胸膛上,只是,泪流得更欢了。他的手传递着心的信息,通过抚摸输进了他的体贴与安慰。他们就这种以倾听、倾诉的方式交谈着。一方是以抚摸为“说”;一方则是以感受为“听”,在这种简化了一切芜杂的“说”与“听”中,进入了声息相闻、心心相印的共鸣。接着,他控制不住地探过脸去,以自己心灵的窗口探视着她心灵的窗口,就那么目不转睛着。一滴亮晶晶的泪涌出了眼眶,闪烁着挂在她的眼睑上。他冲动地伸出舌头接住了这滴泪,不可控制地顺着泪的方向吮吸着那种流的起始之地,吮吸着那张雨打梨花的脸。不知不觉,这种贪婪的吮吸就变成亲吻了。他的唇与她的唇随之迫不及待地对接到了一起。
她呻吟了一声,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舌尖相碰的一刹那双手下意识地箍住了帅开文的腰。
青春的血在帅开文的胸腔里一下子沸腾了。有一种渴望像熊熊的烈火哔哔剥剥地燃烧起来。这种渴望曾经在梦中出现过,曾经被无数次的想象修补过,然而,当这种渴望真的以这种方式来临时,他却笨拙得手慌脚乱,舌头变得一点儿也不温柔,粗鲁而又有力的吮吸仿佛一下子就将她体内的苦涩、羞赧吮吸得一干二净,面如桃花的她两眼迷离娇喘不止,娇小的身体在他的肘弯里一点儿一点儿瘫软下去。像久旱的土地对于雨水,所有的板结都融化了,所有的龟裂都弥合了,所有的干涸都闪烁出了鲜活、腴润的光泽。
渴望升腾,欲望奔涌,理智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切都静寂下来,只剩下了一个年轻的男人和一个年轻的女人,只剩下了陌生渐次转化成的熟悉!
灵魂与肉体点燃的烈火开始熊熊地燃烧了。
这时候的女人才是地地道道的女人
不啻脸颊像早霞般的艳丽
不啻温柔像早霞般的艳丽
连娇羞也像早霞般的艳丽
连妩媚也像早霞般的艳丽
这时候的男人才是地地道道的男人
不啻粗鲁像月光般的柔和
不啻生硬像月光般的柔和
连野蛮也像月光般的柔和
连狂热也像月光般的柔和
世界在这一刻
突然静寂下来了
紫藤般的雷电暴雨般的流沙
走进了记忆的封闭
那些阴险的面孔、狰狞的窥伺、不公正的流言
都倒塌了退缩了烟消云散了
出现在眼前的
只有温暖的阳光、冲动的火焰、被幸福滋润的心灵
世界是分成两半的
有男人的一半
有女人的一半
只有男人女人合而为一的世界
才是完整、完美的
才是生动、充满生机的啊
那天,是帅开文人生的初次;那天,也是结婚五载、离婚一年的管月翠的初次。处女红的花朵不仅映红了管月翠心灵的皱褶,也映红了帅开文的惊讶与感慨。他们躺在单人床上,用身体不断地介绍着自己,呼吸着彼此的气息,神往着今后的日子。今后的日子是可以想象的。管月翠甜甜蜜蜜地说:“往后我上山给你当老板娘!”帅开文美滋滋地说:“有了你就有了一切!今后,不论有多少风狂雨骤都不怕,我已经很知足了!”
百世修来同船渡,千世修来共枕眠哇。那天,直到临近中午管月翠才依依不舍离去。从此,她的心就留在山上了;而他的心也被疾驶而去的轿车载走了。
随后的几个月里,他们的约会、温存差不多都停留在这种偷偷摸摸上,停留在这间充满了诗情画意的小屋里。
他们没忘记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们,但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已经融为一体了!
晃眼间腊月来了,牌局之后没几天,陆尚能就打来电话。接到电话,帅开文叮嘱了小佟几句就离开了松树山。一切的挑战都已过去了,而此行却是为了应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