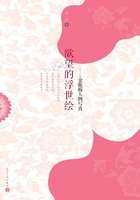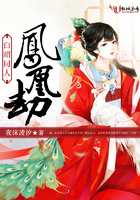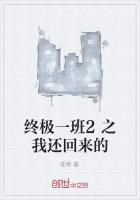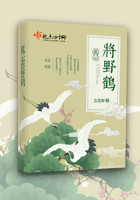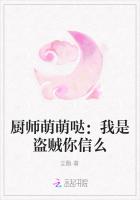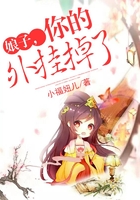如果说马原的故事被叙述结构压抑住,故事替代深度意义模式,那么苏童的故事则是赤裸裸地袒露出来;马原的故事不过是叙述的原材料,而苏童的叙述则全部消解到故事中去。然而,苏童的故事并没有统一构成的叙述纲领,构成苏童叙事机制的是“非理性情绪”。苏童1987年发表的《1934年的逃亡》看上去像个写实主义的传奇故事,而事实上构成传奇色彩的恰恰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叙述中不断涌现的“诗性感情”。苏童热衷于捕捉叙述中涌溢出来的非理性因素。把这些因素加以诗性的催化,使之构成叙述中最有意味的情态,不论是陈宝年坐在竹床上像个巫师一样注视着蒋氏的跟腈,还是蒋氏在草丛里像菊花般燃烧的生育,或者是陈文治性变态的一系列怪诞举止,都是如此。苏童的故事像~道闪闪发光的链条伸越而去,构成那些铮铮发光的环节,形成那些“非理性情绪”,这是故事敞开的时刻,事件和情节默然退场,只有那些光环毫无根由、毫无逻辑、毫无目的地突觋出来。它们构成了故事的阶段性动机和最活跃的叙述动力,成为故事的“绝对价值”。毫无疑问,“非理性情绪”的扩散要瓦解深度意义的统构成,当然,在这里,故事的深层模式不是不能构成,而是没有必要构成苏童后来在《罂粟之家》再次重复了一个家族的故事。他也依然能捕捉住那些“非理性情绪”,当沉草手提驳壳枪朝陈茂的裤裆里打去,在这个过程中,他“闻见原野上永恒飘浮的罂粟气味倏而浓郁倏而消失殆尽”。然而,随着这些‘非理性情绪”的弱化以及它们在多次重复中的理性化转变,苏童故事的那些瞬间不再那么闪闪发光。应该指出的是,这种“非理性情绪”经常在“马原后”的小说叙述中充当阶段性的叙述动机,并且构成故事的闪光链环,它们有力地支撑起故事的转折发展。
与苏童把那些非理性的因素直接当做故事的链环不同,格非把非理性因素作为故事潜在的转折来运用,它们控制住故事的局面,然而却无须受到逻辑关联的约束。格非总是出人意料地推出故事的局面,而那些偶然的疏忽、一时的冲动、突然的变故等等,充当了局面的所谓原因。显然,转折和局面的出现对于格非来说无须有原因或作出解释,格非过于注重他的叙述的故事性,以至于他根本不考虑他的故事有什么“意义”。格非1987年写的《迷舟》虽然留下博尔赫斯或卡尔维诺的痕迹,但仍不失为精彩的小说。故事叙述的主线是萧与杏的爱情纠葛,直到结局副线才突然显现出来:不声不响的警卫员奉师部的命令,只要萧去榆关就把萧打死;但是萧去榆关是去看望杏,却被当做是给敌方传递军情而死于非命。副线主题突然压倒主线的动机,叙述的转折同时是主线与副线动机的交换。结局是潜在的叙述副线的突然显示,竟然使得主线叙述充当剐线的解释。于是格非把主线和副线的置换解释替代了对故事的深度意义模式的解释。显然,格非在《褐色鸟群》里,把《迷舟》里潜在的对立因素发掘出来,发展为对立的互相消解的意群。每一个“现实”都为“同忆”所否决,而每一次的“回忆”又再度构成新的“现实”。
多少年之前“我”追踪“女人”到郊外,许多年之后,女人对“我”说她12岁以后就没有进过城;”我”追踪女人时曾把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刮倒在地死去;而女人的止大也曾经遇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落水而死;许多年以前棋认识“我”,“我”不认识棋,许多年以后,‘我”认识棋而棋却不认识“我’,棋是一个最终的否定。作品在现实与回忆之问构成了一个悖论式的“埃舍尔怪圈”,对立的息群经过否定又回到了对方。《褐色鸟群》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它直接触及到关于存在的不可重复性和不可解释性而打破了追踪意义统一构成的设想;更重要的是,它运用重复叙述而产牛的消解功能摧毁了意义实际存在的任何可能性,所有的存在都立即为另一种存在所代替,存在仅仅意味着不存在一一我不知道格非是否熟知德里达的思想,尽管这多少有些歪曲;《褐色鸟群》毕竟是当代文学中解构主义的第一个实践范本。
余华由于对“怪异”的特殊敏感性,使他的叙述向纯粹感觉还原。在余华的叙述视界里,再也没有像罪恶、丑陋、阴谋、暴力、色情、幻想更适合做“怪异”的原材料的东西了。我惊奇且钦服余华对残忍的承受力,余华对丑恶、暴力、死亡的特殊嗜好,使得他的故事当之无愧是当代最冷酷的叙述。余华1987年发表的《四月i日事件》,把幻想和实际搅成一团,叙述时间在精细的感觉中缓缓流过,一切是如此逼真又如此虚幻。一个无名无姓的“他”,在18岁生日的时刻,神经质地意识到“被抛弃”的恐惧,“他”的精神的漂流状态真切地呈示为对生存环境扭曲的细微感觉,“他”迷醉般地用“幺J觉”来审视实际的存在,毫无疑义,幻觉摧毁了实际。对于余华来说,幻觉比实际的存在更可靠、更真实。因此,他在《世事如烟》里丢掉一切禁忌,彻底进入他的怪异世界。这里只有罪恶、阴谋和死亡,它们被作为日常生活的必要的而又非常自然的内容。余华把生存推到死亡的边界,然后仔细审视人在死亡线E如何挣扎,如何突然消失。显然,“挣扎”对于余华来说不过是一连串毫无意义的怪诞之举,而死亡既不悲壮,也不町怕它不过是“突然消失”的特别方式。
余华给所有琐屑的生活行为都注入宿命的意向,“算命先生”作为罪恶、阴谋和死亡的根源,不过是生活神秘莫测而又充满危险的象征罢了。余华紧接着就写了《难逃劫数》是理所当然的,他再次到死亡的边缘去看人们的生活状态,他那怪异的感觉依然发挥得很好。余华完全不顾及任何“町能性”和“不可能性”,叙述不过是追踪怪异感觉的延伸线索,连接“怪异”的依然是“怪异”。余华的故事不足给解释提供一个模式,而是给阅读提示种特殊的感觉。余华不会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任何新的命题和有用的经验,或者说他摧毁了我们对生存的某种热情和期望:但是他提示的感觉经验无疑为小说叙述进入个人化和主观化的地域打开了最后的通道,当代小说因此可以毫无顾忌地以任何方式进入任何对象。
孙甘露的实验文体即使不是走得最远的,也是最靠近语言的实验。马原的叙述话语是为了构造叙述结构,而孙甘露的叙述就是叙述话语本身;格非也向往梦境,追求虚幻性,但是格非的梦境是为了瓦解生存事实的可靠性,瓦解意义解析的任何可能性;孙甘露的梦境和虚幻的想象不过是给予语词自律运行提供一个自由广阔的空间。孙甘露的《访问梦境》和《信使之函》通篇就是由语词在差异体系里自由播散掇集而成的议论文体,它把毫无节制的夸夸其谈与东方智者的沉思默想相结合,把人类的日常行为与生存的形而上阐发混为一谈,把摧毁语言规则的想象变为神秘莫测的哲理意趣。孙甘露的文本是一个放大了的叙述语式,而他的叙述语式当然也就是压缩了的文本。孙甘露的每一句叙述语式都在进行“瞬间”的情态与“永恒”的感情的转换循环,他把每一个具体的情态给予诗性描述之后再加上某种形而上的阐释,而他的每个关于永恒的顿悟都获得一种诗性的瞬间情态。孙甘露像个远古时代的术士端坐在时间与空间交台转换的十字路口,然后不失时机把他的语词抛洒出去。
他的《请女人猜谜》增补了比较具体的人物和情节,然而,那些人如同幽灵和鬼魂在时空中任意穿棱往来。孙甘露解除了文本与实在世界的任何关联,叙述仅只是~连串占怪的联想的任意延伸。孙甘露把小说的叙事功能变为修辞风格,在最大限度拓展小说的观念的同时也严重威胁到小说的原命题尽管睿智的人们从王蒙近期的小说,例如《来劲》、《一嚏千娇》、《十字架上》和《球星》里,可以读出各种母题乃至影射的寓意,我在王蒙的一系列语言实验里,更多地看到词与词碰撞迸射出来的火花,而主题和意义包括所有的隐喻和象征都被烧毁,惟有语言锻造的锁链,这条锁链迟早要勒死文学的精灵。王蒙善于把抽象概念和流行隐喻、社会名流和童话人物杂乱无章地混合一体,毫无节制的语无伦次与巴塞尔姆式的夸大其辞相结合,证明了王蒙在机智幽默和玩弄语言方面的惊人才能(像巴塞尔姆在60年代那样嘲弄讥讽和调皮捣蛋的才智至今还令人钦佩不已)。尽管我无法证实王蒙接受过巴塞尔姆的启不,但是他们处理语言的方式无疑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巴塞尔姆在60年代写下的实验小说大多由于没有主题而残缺不全,留下一个语言和讽刺无法填补的真空。他的叙述想入非非而东拉西扯,通过某种麻木不仁的机械风格和一整套语词异化的手法,巴塞尔姆有意识地阻碍我们在传统小说中进行的那种低劣而肤浅的识别。王蒙的叙述虽然还残留着某种生活主题和嘲讽现实的寓意,但是,王蒙叙述的驱动力已经转向了修辞风格的探索,故事情节更像是语词自由组合的粘合剂,主题和意义更有可能是嘲弄和幽默的阶段性的副产品。王蒙给失去了轰动效应的当代文学寻找到一个可供自由游戏的语言平面,当代的各种文化糟粕从语言的通道涌进文本,王蒙试图由此达到他对现实恋恋不忘的批判。然而,当代的文化槽柏以及王蒙的“批判”除了给语言的平面提供游戏的原材料之外,不会有更多的“现实”意义。
总之,“后新潮”实验小说解除了叙述的及物世界以及生活世界中的终极性价值,消解了故事中的先验的和期待解释的内在意义,叙述中的那些形而上的意念和感悟实际转变为不可知的神秘,它们促使意义变得难以辨认和不可解析。当然,“后新潮”还有切近现实而没有解除叙述的及物世界的另一股分支,他们是刘恒、叶兆青、叶曙明、王朔、北村,李锐、李晓等人。从总体上说,他们的叙事方式虽然不具有实验的先锋性,但是同样不考虑生活世界的信仰和价值问题,同样解除了预期的意识形态观念和寻找的神话的深重精神建构。在反抗文明的象征制度的主体中心化和消解价值体系的统一范型方面,写实小说与实验小说殊途而同归。当然,“后新潮”小说并不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实验小说的直接翻版,就从它所接受的启示或借鉴的痕迹而言,它更像是填补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约翰.巴思在1967年写了《疲惫的文学》,13年之后,巴思又写下《添补的文学》,后现代的先锋派也不得不从卡尔维诺、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那里索取改良的灵丹妙药。“后新潮”小说却占尽了时间差的便宜,侥幸地饮下了这杯西方后现代实验大师梦想调制的“鸡尾酒”。“后新潮”无疑借着这股酒力扮演着挑战者的角色,一旦酒力消失,它将剩下什么’它给我们的文明留下什么?
当我提到“我们的文明”这个称谓时,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犹疑和虚弱。我们的文明能承受什么呢?对于反抗和挑战来说,文明没有现实;可是对于不再拥有未来的文明来说,摧毁和破坏的意义何在呢?所有的超越因为拥有坚实的信念(即使是像西希弗斯式的信念)而否定现实流向未来,超越就是未来文明的基础。现代主义整个说来是超越性的反抗的文化,而后现代主义消解了超越,把“完整性”当做生活的本来的内容全部接受下来,美国战后的实验小说用实验的多样化束减轻暴山、屈辱棚脆弱性情感的多样分化。“不完整性”被当切断痛苦的开芰,做返叫到牛活原初状态的纯真里去的一种方式。然而时于当代中国的实验小说柬说,所有拆解深度的实验部意味着对文明的挑战和对现实的超越。深度解除了,文学却因此超越了文明和现实。
新潮文学“寻找的神话”构成当代文明的超越进向,但足这一进向并没有在文明中真正扎下根束,当代文明尤力承受那样的“深度”——那是当代文明不能承受之“重”。后新潮走出这个深度模式,它似乎预示了文明新的现实:当代文明的先锋文化由此走向了无深度精神和终极价值的自由“平面”。对于整个文明来说,对于我们生活的伸展来说,它提供了一种替代的感觉方式——这种“感觉方式”正是马尔库塞在后工业社会里惟一看到的可能的社会革命的来源。这种颠覆性的行为,无疑是一种创造的勇气,当然也是反抗的草率,它更有可能是对现实和未来双重屈从的结果。可是,当代文明能承受这种拆除了深度模式的“轻”吗?
这是否又是当代文明进行的一场虚假的实验?当代文学的“先锋性”尽管在绝对价值上为我们的文明寻找了一种替代苦难的感觉方式,但相对于我们如此虚弱而混杂的当代文化来说,那种激进的实验很有町能变成一种致命的颠覆力量。后新潮文学创造的经验对于实验者来说是向本位文明挑战的感觉方式,而对于处于这个文明中的绝大多数的芸芸众生来说,他们(挑战者)不仅是一些不可企及的先锋,而且是人们急于忘记的殉道者。当代文明决不是因为过久地怀抱了那种超越性的人类信念。沉入到精神厚实的深处底蕴去领悟生存的终极价值才抛弃“深度”,当代文明中滋长的先锋性实验实际是无力承受那种深重的精神而逃遁到“平面”去的。因此,当代文明可能更迫切需要一种不屈的自我拯救的意志,需要一种重新凝聚起来的信念,需要那种忍辱负重的深邃精神先锋文学创造的经验和感觉方式不适合当代文明的状态——它足当代文明小能承受之轻。历史无法跨越,它还要回到久远的过去重新开始,当代文明还要在重复里耗费精力、热情、思想和希望,直到筋疲力尽,直到突然死去或突然新生。这是我们的劫数。
原载《福建文学》199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