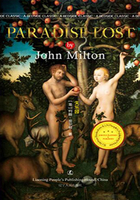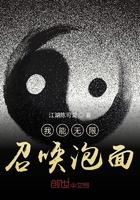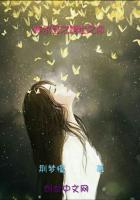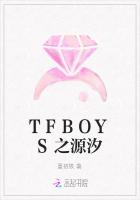评黑马的《混在北京》
黑马在中国文坛纵横驰骋已有数年之久,“它”还是一匹黑马。少有人知道“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它”现在还在沉着稳健地奔跑,与中国文坛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神秘、偶尔露一手,随即又不知去向。这是一匹真正的黑马,一匹反本质主义的黑马。直到“它”驰骋了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他是我十多年前的同学,作为职业的文学研究者,这回我可真是打眼了。我原本知道他是一位翻译高手,把劳伦斯翻得四脚朝天,准确而文笔流畅且有韵味,我以为他的英文比中文更好。
数年前,黑马出版《混在北京》,这部小说在文学圈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但却令电影界的大腕导演们心醉神迷。数名导演为争得电影电视改编权一改往日吝啬的品性而慷慨解囊。
电影也曾风行一时,还拿了一些外国的奖项。《混在北京》的德文版销量看好,一向谨慎自律的德国人也情不自禁大放溢美之辞说:“不论从哪方面来衡量,这本书都远远超过了在德国所读过的任何位亚洲作家的作品。”(德国《焦点》杂志)最近《馄在北京》再版,装帧精美,有高人发行,看来走俏文坛势不叫挡当然,这并不是一本畅销书,但很可能是,本常销书。要了解八九十年代中国青年文化人的生存现实,要了解人们的物质生活如何压迫精神生活,要了解人们的内心冲动、欲望和想象是如何从生活变形的边界顽强地涌溢而出,那就读读《混在北京》吧,它无疑是这方而顶极的作品《混在北京》讲述一群外地进京的大学生毕业后留在向导出版社的遭遇。这些人无疑部是尖子人材,但面对日常生活的困窘,他们一个个变成了卑琐的世俗小人,这里的故事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大部是人们面对的日常生活。这些曾经自以为是的青年才俊,一旦陷入生活的泥坑,他们所有的行径都显得可笑且可悲。这些向导出版社的编辑们本来应该引领人们的思想精神进发到一个高尚的境界,但他们自身却被狭窄的生存空间弄得颠三倒四,迷失了方向。
在这座筒子楼里,人们首先要为获得个人的生活空间奋斗,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存在方式的出发点就是排挤他人,或者被他人排挤。排挤与反排挤构成了这些拥挤在一起的人们的基本关系。沙新、胡义、高跃进、冒守财,都是聪明伶俐的文化人,现在他们把聪明劲主要用在了如何把同屋的人挤出房间,使自己独自占有一个生存空间。这本来是成年人生存的最低限度条件,但对于向导出版社的一批年青人来说,却是最高的生活目标,并且实行起来困难重重,不使出浑身的解数,不把别人搞倒搞臭,不把脸面和体面扔在脚下,那就不可能实现这一宏伟的理想。物质生活或者说经济基础具有不可超越性,黑马算是透彻领会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深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生活于这样的筒子楼里,要为狭窄的生活空间,为老婆的户口和坐月子,为油盐酱醋、水费电费发愁,你还能指望人们能有多高的情操?你还能要求人们不要为自己着想,多想想别人、多想想集体。这些人并不足特别渺小卑劣,他们不过足被推到了人的生存的最低限度,在这里,人们不得不按照动物学原理展开生存竞争。
多好的动物学原理,我们的文学长期描写宏大的主题,描写空灵高超的精神境界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贤亮的《牧马人》、《绿化树》等等,表现了知识分子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依然保持着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矢志不渝的理想情怀:
但在这里,这些人已经彻底被唯物主义打垮,肉体的存在需要压倒了精神追求。只有一个胡义,还装模作样地听些西洋唱片和国粹戏曲,但他充其量也就只有些嗜好而已,除此之外,看不出还有更高的精神信念。他最终的结果也找不准个人的社会位置。每时每刻的生存现实困扰着这些曾经有文化理想的青年,这部小说的描写冷峻而略显残酷,不给他们留有余地,把他们推到最低的生活限度,虽然不是什么水深火热,不是什么生死攸关,但作为文化人,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这也是他们作为“这种人”所能承受的最后一道界限。沙新的老婆坐月子,首先要把同屋的弄到其他房间,其次要忍受对门厕所流出的污水及气味;季子则用肉体交换方式获得一个单间;冒守财被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戏弄得几乎身败名裂;高跃进被孩子入托以及老家来的保姆搞得手足无措;一心要出国的单丽丽却不得不每天忍受同屋的谢美发出的叫唤声音;而在这座筒子楼里,当着第i者从事这类活动不是什么特例……所有这些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艰难险恶,也谈不上忍辱负重,但却足以把文化人的人格和体面弄得混乱不堪。《混在北京》就是在青年文化人的日常生活困窘中来看人是如何从精神性的存在变成物质性和动物学的存在。
黑马并不是恶意嘲笑他的同代人的遭遇,一方面,黑马的写作根源于他的个人经验,正如他在后记里所表述的那样,这本书的写作与他的个人经验相关,很多故事就是他的经历,他身边的人和事,里面也有他自己的影子;另一方面,黑马也许试图去揭示90年代以来一直困扰人们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在哪里出了毛病?在大众文化流行的年代,何以知识分子文化就一蹶不振,这本书并不是简单写出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出现的问题,同时试图探究知识分子文化是如何颓败的这样一个历史难题。当然,这一难题隐藏在非常生动具体而有个性化的故事里,黑马的解释未必全面,仍却明确而尖锐,在他看来,一定是因为这个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连基本的物质生活都无法解决,自顾不暇,如何去追求时代的精神信念,作为社会的精神向导呢?向导出版社不过是文化颓败的象征,权力轴心的运作以及物质生活困窘,这就是知识分子文化难以抬头的根源所在。黑马的“唯物论”无疑揭示当代文化溃败的深刻根源,但这只能是某方面的根源。也许人们有理由追问说,90年代末期以后,中国确立了以房地产和汽车产业作为刺激国民生产和消费的支柱产业,知识分子的居住宅间已经得到较好改善,这是否意味着当代文化的根本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呢,当然,这种追问对于一部从某个侧面表现当代文化人生存状态的作品是不恰当的,黑马的直接出发点并没有打算回答如此严肃郑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是他的作品生发出的某种思想副产品。对于作者来说,要解决这一问题同样感到迷惘,沙新和吕峰都下海经商,但他们在改变物质生活状况后,并没有找到生活的本质要义。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物质与精神之间,并不是直接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它们之间的连接方式是复杂而多变的。黑马显然意识到这一点,尽管还不及深入开掘。
这部作品真正的非同凡响之处可能在于它的反讽性叙述。
这种反讽来自作者对生活情境的极端化和夸张的处理,每个人的生活都被恰当地歪曲了,身份与语言,行动与结果,动机与效果,表象与实质……等等,显示出生活变形的那种可笑滑稽,黑马的叙述也由此显示出犀利机智与幽默洒脱的过人才情。
总之,这部作品打开了当代生活的另一侧面,最重要的是,它强有力地展现出那种变形了的生活情境和情调;而在变形的生活边界,人们永远无法遏止的生活渴望如此倔强地涌溢而出,怪异、忧伤而楚楚动人。它的偏激——把一种牛活状况推到极端的作法,把生活的本质全部掏空了给人看的本领,这是它的惊人之处。
2000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