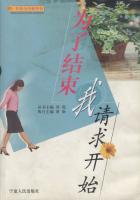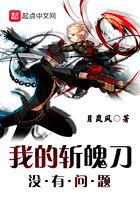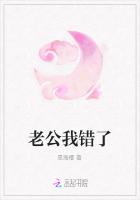“****”后至80年代上半期,中国文学一直充当思想解放的开路先锋,其势锐不可当。然而,进入80年代后期,由于种种现实原因(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当代文学已走向穷途末路,它无力在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实践中起到基础性的构成作用,去构造现实的想象关系,表述人们的共同愿望。尽管依然有许多人在写作,却少有人在阅读;也有人在谈沦一些崭新而尖锐的问题,然而却激不起多少反响:文学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激动人心的节日上演,在我看来,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已经死亡,而我们不过是些哭丧的人。
1991年,在这个毫无诗意的年份,我又能给当代小说描绘出怎样的形象呢?对于理解历史的人们来说,“历史事实”本身无所谓意义,历史的意义终归是谈论出来的正像人们经常说的那样:地卜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我无意于去虚构小说的历史,我只能去谈论我认为“有意义的”文学市实。我说过历史的意义是人们谈论出来的,因此,我并不惮丁承担杜撰历史的罪名,在这一意义上,历史是自生自灭的。
1991年,随着形式主义的探索彻底退化,小说面临的危机更加深重,因为这个危机并不仅仅是屈服于文明解体的压力,也不只是来自整个社会的冷漠,更重要的在于小说自身的创造性已经枯竭。正足这种危机使今日小说处于两难境地:在传统与创新、形式与实际、个人与社会、写作与政治,反抗与认同等等双重选择方面彷徨不定当然待徨也是寻找,它酝酿着变化。所史何上何从,非预言家无法断定;但是找到历史运行的轨迹,则是观察所史的人们必须绘出的地形图。
南于当今特殊的现实情势,我不得不回避那些过于复杂的问题,例如我尤力评价当今的“主旋律”。尽管在1991年,上流意识形态支配的文学活动占据了文坛上的中心位置,然而我更乐于谈论那些标志文学自身历史发展变迁的现象(或事实)。
企图在一篇文章中慨括1991年的小说现状无疑是困难的,与其浮光掠影,不如抓住几个要点,冈此,我主要从小说创作创新与常规的互动关系人手来勾画这一历史片断的简要轮廓。
1新写实主义:一面暧昧的旗帜“新写实主义”白1989年第三期《钟山》亮出旗号至今,不过两年多的所史,总算给寂寞的文坛找到一个多数人可以谈论的话题。我之所以称之为“暖昧的”旗帜,乃是因为它的动机、立场和含义始终混乱不清,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面旗帜的颜色不尽相同。“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写道:“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L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蜕创作低谷巾出现的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观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可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新写实小说观察生活把握世界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不仅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还分明渗透着强烈的所史意识和哲学意识。但它减退了过去伪现实主义那种直露,急功近利的政治性色彩,而追求一种更为丰厚更为博人的文学境界。”倡导者们把“新写实主义”描述成兼收并蓄的文学境界,因此也就难免似是而非,众说纷纭了。
“新写实主义”受到的批评米白各个方面。在某些人看来,“新写实”乃是一次企图对伟大的现实主义实施“和半演变”的拙劣勾当,什么“生活的原生形态”、“现象学还原”、“凡人琐事”,无疑是要冲淡社会主义“主旋律”;在那些新写实小说里儿乎看不到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更少有奋勇前进的角色——它当然没有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本质规律”;在他们眼里,提倡新写实主义居心叵测,那些鬼鬼祟祟的理论来路不明,不过是些鸡零狗碎的货色。而在另一些人看来,“新写实主义”是一次无耻的背叛和徒然的投降。他们认为,匆忙提出的“新写实主义”几乎从背后给了埋头形式主义探索的“先锋派”以致命的一枪,当代文学在形式变革的十字路口颓然倒地;提倡写凡人琐事,所谓回到“生活本相”,还原生活,无非是让上文学再次去队同庸俗的小市民生活;总之,“新写实主义”是一中平庸、调和,投机的货色。这种争执显然带有很强的偏见,很难取得公正的判断就一般理论意义上来看,“新写实主义”无法定义(命名),或者无法与“现实主义”作出基本区别,或者与“现实主义”根本相悖;而且有关“新写实”的具体理论也包含不少谬误,例如“现实牛活的原生形态”,小说是语言的构造物,它又如何能混同于“现实生活的原生形态”呢?特别是被广泛运用的“还原”这个术语,讨论者几乎没有渎过胡塞尔的书,更小知“还原”乃是同归主体意识的主观化的认知方式,胡塞尔现象学的前提条件是:主题应当看做一切意义之源和本,它本身并小真正是世界的部分,因为它原先促成了这个世界的存化“新写实”的解释者望文生义,把“还原”理解成“恢复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由此可见“新写实”有关理论的草率和粗陋。
虽然“新写实主义”的理论主张不甚明了,但是人头阵容却是清楚的,划归在这面旗帜下的作家主要有方方、池莉、刘震云、刘恒、李锐、李晓、朱苏进、赵本夫、叶兆言、范小青、周梅森等等。
这个阵容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以至于某些原米属于“先锋派”干将的人物,如苏童等人也被拉去入伙。“新写实主义”的旗号由《钟山》打出,但被视为“新写文小说”的作品却不限刊于《钟山》“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栏日,而且有些代表作晶刊于1989年以前,如方方的《风景》。更有甚者,除去典型的实验小说,凡是略有新意的作品统统划到“新写实”名下,似乎‘新写实主义”是一个巨大的垃圾箱,可以容纳任何发霉的物质。
1991年《钟山》第1~3期依然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白第4期偃旗息鼓(原因可想而知)。这三期推出的“新写实小说”除了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和苏童的《米》外,少有出色的作品。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连载《钟山》第1-2期,全书分成“村长的谋杀”、“鬼子来了”、“翻身”、“文化”等四部分,分别写民国初年、抗战期间(1940),土改期间(1949)和“****”期间(1966-1968)半个多世纪中国北方农村发生的故事。就小说要素和叙事方法而言,这部作品与经典现实主义(即1949年以后由意识形态权威确认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仔细推敲却大相径庭。其一,悖离“典型化”法则。经媳现实主义强调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反映所谓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不用说就足以同语反复的方式证明意识形态权威给定的意义。《故乡天下黄花》却把笔墨重点放置在琐屑的日常生活情境,去捕捉生活细节中散发出来的幽默因索和反讽意味,个人的偶然行为和状态被置于写作的中心,替代(颠覆)了原来的“本质规律”。其二,消解“阶级论’。以“阶级性”确认的人物关系法则被推翻,不管是地主还是农民,他们的本质都一样——崇拜权力并且为权力所驱使,当官、掌权、光宗耀祖、统治他人或被人统治,人的生存本能、欲望和最高的愿望在这里达到统一。其三,改写“革命神话”。这部跨越中国现代“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作品,却看不到经典现实主义神话讲述的农民革命的要求,也看不到他们如何接受“革命道理”走上”革命道路”的历史进程。相反,这里只有家族私仇和弄巧成拙的杀戮。革命的辩证法为历史虚无主义所消解,不管是在民国初年,还是抗战土改,或是“**********”,支配历史运作的,支配人们日常行为及其关系的法则,就是权力的辩证法。其四,悲剧感的丧失。这部作品也写到不少“悲剧性”的场面,但是作者更倾向于去描写造成这些“悲剧”的荒诞因素不是永恒正义的冲突,而纯粹是一系列弄巧成拙的小聪明构成了悲剧的动机,隐藏在背后的可笑的阴谋诡计消解了历史悲剧的“悲剧性”。总之,尽管这部小说未必达到多高的艺术水准,但是它那平实自然的叙述,于日常性中见出反讽和幽默的笔法,以及它那含而不露的解构“历史”、“革命神话”的思想,都有耐人寻味之处。
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成为1991年的热门话题。小说描述了深陷于家庭琐事中的小知识分子的生活困境,权力与贫困构成的恶性循环使小人物卷进粗陋的物质生活却精心谋划,结果,在每一次生活困难的解决背后,都隐藏着权力的戏弄。人们自认为精明却总是为生活所摆布,贫困单调却能自得其乐,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磨去人们的精神、意志、情感和希望,他(她)只能在跟前的暂时的利益中体味生活的乐趣。这篇小说到底是同情还是批判这种生括现状无关紧要,它的意义在于令人信服地看到权力关系如此全面又细致地渗透进入们的(家庭)生活。
正是对“权力关系”的认识,使“新写实主义”找到个理解当代现实的“症结”处,也因此具有现实力度。
苏童的《米》被放置在“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栏目中多少有些奇怪,曾经被看做“先锋派”干将之一的苏童,现在却乐意站存“新写实”麾下,足可见“现实”的诱惑终究比艺术冒险要有力量这部长篇当然比苏童过去任何一部小说都更注重故事性,它看上去像一部传奇志怪,其中每个人都是坏人而且都没有好下场,欺压、诈骗、作恶、诱惑、浮欲、阴谋、内哄、暗算和复仇等等构成故事的主要内容,而苏童叙述这些类似黑社会的事迹却也能得心应手,于舒缓从容中透示出凶险:显然,这部小说把个人的经验发掘得十分充分,人性的原始罪恶与个人的独特经历混为一体,使凶狠的复仇变成是一次合乎历史理性的自我确证。
主角五龙,这个来自乡村的流氓无产者,总是以“乡村”的心灵来感受他所蒙受的城市的压迫,在他仇视城市的瞬间,乡村的景象总是像梦一样绵延而至,他几乎是代表破败的乡村向都市实施变本加厉的报复。这个故事依然叙述得舒畅圆润,但是凶猛的劲头部显示出来了,却也可见苏童想换换口味。《米》的时代背景在20世纪上半叶(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中同样看不到“革命所史”的神话模式。因此,我不得不认为,“重写”中国现代史是这类作品无意识触及到的一个重大而冒险的课题。
1991年划归“新写实主义”麾下的出色之作寥寥无几,但是关于“新写实主义”的谈论却方兴未艾。“新写实主义”之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最主要的原因、与然是当代文学无话可说。但是“新写实”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很强的话题,这也是各式各样的人部能说上话,而且说的都不一样的缘由所在。所谓“众说纷纭”,其一是指话题本身的含混性引起歧义,其二是“众说”(说话主体)导致“纷纭”。对于老派批评家来说,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论题,只要在现有的理论典范下,侄现成的知识水准上就能谈论。对于崇尚新思想而又缺乏充足的现代理论准备的人来说,这个题日也大有用武之地,那些道听途说的“新名词”、“新概念”望文生义就能用上。“新写实”既满足了对“新”的急切要求,又掩饰了理论知识的匮乏,这就足“新写实”能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的主观原因1991年各地都召开过各种形式的关于“新写实主义”的座谈会或讨论会。引起注意的有年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举行的座谈会,会后以笔谈的形式在《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刊出,随后在《作品与争鸣》(1991年第6期)转载。这次对论并无权威性可言,就像所有关于“新写实主义”的争论一样,这也是一次“众说纷纭”的讨论,纠缠于“新写实主义”概念的辨别而难得要领,理论陈旧而知识老化,笼罩着意识形态的阴影而难越雷池一步。
“新写实主义”本来就是一次假想的进军,指望它有什么惊人之举,或怀疑它有叛乱之嫌都不实际,它不过是当今大陆文学在无可奈何之中所作的一次徒劳的挣扎,它的暖昧不清的姿态恰好是当今大陆整个文化情境嗳昧性的表征,如果说“新写实主义”有什么历史意义的话,那就是它在“政治与写作”的双重意义上打消了文学企图超越现实的任何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