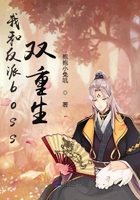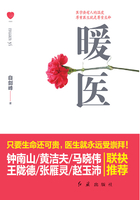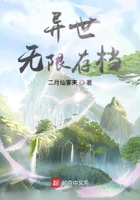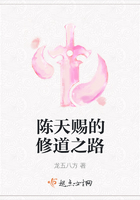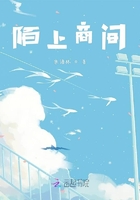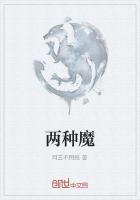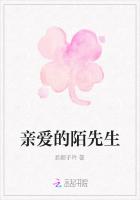第一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的一个秋天,从南宁到桂平的路,还是一条又窄又弯的“国道”,沿路的桉树叶已发黄,车至桂平,甫抵西山,顿觉一片寂寞,一片宁静,一片“原始”,一片苍凉,树绿鸨叫,飘然山野,过于单调。“当山风掠过,松涛浩浩,有如大海波涛,或如深山虎啸”,人们观赏这些古树,往往引发忠贞高洁之想。难怪“西山有古寺古庙四座,历代高僧驻”,使西山成为了广西的佛教圣地。佛家选桂平西山为驻刹之地,固有其观山察脉之玄妙。因而我头一次登山,在当地文友陈雄权先生的陪同下,我喝过释宽能法师亲自沏的西山茶,其色青绿,其味苦后而甘,啧嘴称叹,妙不可言。据说这西山茶早在唐代就有了,明清时代不少商家远道从香港、广州、长沙收购和贩卖西山茶。到了后来,西山的僧人们还把西山茶寄给******品尝,******喝了西山茶,表示赞赏,但他坚持把茶叶款寄回了西山,看来******的一生是清廉的。
第一次到桂平,不仅品了西山茶,还饮了乳泉酒,这酒现已不生产,甚是可惜。西山溪流纵横甘泉四溢,雄权先生说,在众多的甘泉之中,尤以龙华寺左侧的乳泉为最佳、最美,因此用乳泉水酿的酒就特别醇,有“广西茅台”之誉,饮罢,令我飘飘欲仙,疑为得到佛主点化的感觉。那次踏足桂平,匆匆而行,对于更多的有关桂平的情况几乎就只这些。
第二次去桂平,是新近,如今宽阔的马路直通桂平,离南T只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尤其是在香港启德机场与台湾高雄老教授的一番交谈之后,加上弓一贯致力于桂平文化研究的雄权先生忘年之交,他一本本关于桂平西山、关于金田起义、关于释宽能法师、关于李宗仁与郭德洁的许多专著和故事,使桂平这天国故园的传说盈盈地盘跟在我的脑海,满足我对天国故园的寻找。
来到桂平,我的心情是相当复杂的,这些年,人们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议论纷纷,一改过去的唯一认定,这是一种宽松的氛围,至少人们可以不用在一种思想下生活了。
也许前些年来桂平,我的想法可能是很简单的,从我们历来的教育上得到的答案,一位农民起义大军的首领、太平天国运动的首倡者,无疑那是要肃然起敬的。但在今天,读了不少人写的批评乃至否定的文章:一个不伦不类的造神者,一个并非进步甚至比之清廷更加腐化的称王者,一个心胸狭隘不能容人制造内讧的首恶分子,一个活该失败而不可能取胜的造反者……总之,在我的心上蒙上了一层未及掸拂的阴影……
其实,在这以前的若干年中,我对洪秀全除却在总体上认定他是一位反对清王朝的造反领袖外,对洪秀全这个人从情感上原本也谈不上有多么喜爱;但当我来到桂平金田实地感受了一番之后,我还是尽量不以个人意气睥睨这位历史人物,甚至比以前只从文字上读他更多了几分理解。在这一点上,我以为是不宜仅从习惯以“人好”、“人坏”的简单概念作出理性评价的。固然,当年他的举事自有其个人感情上的动因,他并不是一名伟人,他归根结底是农民。但在鸦片战争后的十九世纪中叶的社会现实中,发生太平天国抑或是别的反抗清朝统治者的事件是势所必然的。今日说洪秀全有帝王思想也罢,腐败也罢,我想最致命的就是他那“打砸抢”、“焚书坑儒”摧毁文化,反文明,逆人类的许多类似今天阿富汗“塔利班”破坏巴米扬大佛的行径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农民队伍与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不一样的性质就有了一种令人不能宽恕的罪行。
当然,我面对天国故园,面对金田后来一切的一切,却又不能不使我生出许多“假如”和遗憾,还有许多与过去不同的更加冷静的认识。
他——洪秀全,在屡试不中后,一怒之下将“至圣先师”的牌位摔在地,表明了他与儒家正统教义的决裂;可今天我又在想:假如他乡试中了一名举人,他是否会像范进那般狂喜,还会将造反的长剑指向他后来切齿痛恨的“清妖”吗?
然而,我们不能认定的事实是:他毕竟是以一怒为导火线,又有金田村的烧炭助燃,毅然驾上“拜上帝会”的征帆,扔掉积怨积垢的长辫,权作投向“清妖”的最高象征——咸丰皇帝的檄文。
这一檄文却闹成了气候。“金田”的战车出广西,沿湘江人长江,顺流而下,他的得力臂膀冯云山、萧朝贵先后战死,长发与辫子展开殊死博斗。突然间,杀出一彪人马——曾国藩和他训练的湘军,在长江两岸水陆较量。最初阶段,曾国藩也曾呛了几口江水,爬出水面托出一部“家书”。这部不同寻常的家书,在表述亲情和人生况味的同时,也隐录着石头城上的风云变幻,到今天,许多人仍热读这部“著作”。
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从前,我们读到的曾国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清朝统治者的忠实鹰犬、镇压农民起义运动的血腥刽子手;近年来,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另一种声音——“曾文正公”的行情和价码不断看涨,连我也买了一套《曾国藩家书》。与之同时,如前面所言,他的对手洪秀全们却大大贬值,犹如两座相连中间有水闸调节的水库,这边水位高了,那边水位便低了下去;反之亦然。可见,人们看待事物的目光,也是变幻不定的,至少更客观了。
不能说今天对洪秀全和他的事业褒贬得都不对。应该说,灼干天王府池水的是内耗;征帆行进至半途,换汤不换药的顽症毕显;也许,当湘军攻破“天京”打扫战场时发现,天王府里固然没有一尊孔子的牌位,却有一把与紫禁城太和殿竞奢的沉重难移的龙椅。
可见,一怒之火毕竟难以持久,金田村的炭火相对说来也很微弱,移至笙歌曼舞的秦淮岸畔终至熄灭;那被摔裂的“至圣”牌位重又复原,只望着被攻破的石头城残阳无声地嘲笑……
如今我来到天国故园,没有嘲笑。这毕竟是历史,至少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段落,它就像站立的一个巨大背影,你是无法挥拂而去的,也是不容我们嘲笑的。
挥之不去的天国故园不可忘却的天国故园。
面对太平天国如此巨大深刻的历史悲剧,无论在当时人和现代人的心理上所造成的创痛应该说是不可名状的,但这段历史其意义是沉重的,有分量的。至少它让我们明白,社会的任何变革应该是文明的,得民心的。因此,许多人都充满热情,纷纷致力于确认可能范围内的一切事实,并在此基础上,以各自的方法和特点,走着自己的探索之路,高举智慧与灵感的明灯去照亮那片叫人不能忘却的天国故园。
南宁花开遍地,那片海棠早已不在
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是悠久的。
1998年11月,考古工作者在南宁市郊的石火岭发掘出鸟臀类恐龙化石,从而将原定为新生代第三纪地层的那龙盆地和南宁盆地周围的红岩组的地质朝代改为中生代。
这里曾是一片泽国,大海,汪洋。人类文明史前的岁月是漫长的,时光沥尽,海枯石烂,几千万年过去,才成了今天的南宁盆地,象征生命的绿色与南宁从此息息相伴。如今,从南宁石火岭和顶狮山贝丘新石器古代遗址那无尽岁月的烟尘中,我们还可看到当时在这里唱着主角的巨兽和恐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南宁的先民早已在这片土地上进行原始农事和渔猎,开始了他们的劳动创造。
1997年,在南宁邕江、邕宁和武鸣一带陆续发现了豹子头遗址、灰窑田遗址等十五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在这些遗
文化地位。
处于失忆状态的人是可怕的,处于失忆状态的城市则南宁老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磨制石斧、石刀、石矛、石坠网、石磨盘等石器以及骨器、平砂陶片和动物骨骼。它表明大约在一万年前,这里已有人类居住,渔猎活动和原始农业已相当发达。
南宁顶狮山贝丘遗址的发现,其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中国考古学界长期以来一直以黄河、长江流域为重点和根据的状况,为人们研究和认识华南及东南亚史前文化特征和内涵,探寻其文化框架和序列提供了依据。
在那些文化的尽头处,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最初最本原的文化密码。谁能不说南宁的文化定位和文化地位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呢?
而后是百越世界,秦始皇建置时属桂林郡,三国时属吴,后归西晋、东晋、宋、齐、梁、陈,隋炀帝时归郁林郡;唐贞观六年(632年)始称邕州,元朝泰定元年(1324年)改邕州路为南宁路,南宁由此得名。
南宁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源远流长,它的历史文化链条,从来就没有断裂过。
从东晋至今,历代帝王和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南宁特殊的战略地位和是一个无根无魂的城市。
南宁是需要发现的。
南宁的魅力就仿佛在一夜之间被人们所发现和了解——直到二十至二十一世纪之交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成功举办,把南宁的美丽和南宁人的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甚至成为该市的一大文化的品牌。
于是,南宁在寻找文化。
然而,南宁的文化由来已久,四百七十多年前,一个大师级人物来到南宁。秋日,日丽风和。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南宁市人民公园,我瞻仰明朝大儒王守仁的遗像碑。
王守仁,字伯安,自号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史称:“终明之世,交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不过,王守仁并不看重武功,他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他穷毕生精力创立的旨在发掘人之“良知良能”的阳明心学,对近现代中国、日本及东南亚诸国的政治、文化、哲学都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明嘉靖六年(1527年),王守仁统兵南下广西,不战而平思恩、田州之乱。他痛感广西“理学不明,人心陷溺,风教不振”,于是在南宁创办敷文书院,开道讲学,由此,广西士民始知有理学。
王守仁只在广西待了一年,但历史却为这位大儒留下了三处弥足珍贵的“记忆”,南宁市北宁街至今仍立有一块镌刻“王阳明讲学处”的石碑,在人民公园镇宁炮台有一块“王阳明先生遗像”碑,一块“敷文书字碑记”。
然而,当我在镇宁炮台看到仰慕已久的“王阳明先生遗像”碑时,却大感惊讶。遗像碑和其他七块石碑被安排环绕镇宁炮台而立,看上去似乎是“王阳明”成了镇宁炮台这个庞然大物的附属物和点缀品。更令人觉得唐突的是,由于风化严重,遗像碑的线条和“王阳明先生遗像”几个字却粗黑抢眼,显然是人为“描红”的结果。环顾四周,一代大儒的遗迹与一个绿林好汉陆荣廷撰写的《新建镇宁炮台记》、一尊德国人制造的固定型陆防线膛加农炮、几块炮台碉堡里的哈哈镜奇怪地搀和在一起,阳明先生九泉有知,不知将作何感想?
我向东走去,找一个叫横县的地方,它的历史要比南宁还早。
横县,在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建置为县,称广安县,至今已有两千一百多年。如今横州一片片绿色的田野上,绽开着一片片白色的茉莉花。我信步田畴,借以排遣困倦,眼前总是绿意,那茉莉花覆盖在绿色的波涛上,在风的吹拂下就仿佛荡漾着一层层白浪;霎时,我们感受到一种蓬勃的气息扑面而来,心里蓦然一亮,温湿湿的。我情不自禁地摘下一朵闻闻,有一股沉郁的泥土香。这平淡无奇的小花,没有白莲的冰肌玉骨,也没有梅花劲挺的幽香;不像牡丹雍容妖艳,也不如梨花素白端庄,在一派旺盛的夏热中,她貌不惊人,却常常成为了人们吟唱的信物。据说如今中国的乐团出国演出,《茉莉花》就是一首必不可少的曲目,当演奏到这一乐曲时,那悠扬而深情的曲调令老外们也忍不住跟着哼了起来,优美的旋律走向了世界,属于了全人类。
走在横州的田畴上,我忽然明白了花是大自然的精华,是人们情感的橱窗。
难怪苏东坡要发出“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银烛照红妆”的咏叹,难怪林黛玉会噙泪幽幽唱葬花!我没有苏东坡的惜花之情,也没有黛玉的幽怨之痛。但走在横州的田畴上,看着它今日无根的茉莉花,我感知到横州自古的花语。
县城西隅有一条香稻溪。据说古时候,这条水溪的两岸田野广种香稻,溪边栽种着一片片海棠花。每当海棠盛开的季节,花色将溪水映成紫色,溪里有一股紫色水流在静静流淌,古人称为“紫水呈祥”。香稻溪流入郁江的溪口,横着一条长三十二米、高八米、宽四米的单拱青石桥,古朴、坚固,如长虹饮涧。每逢郁江洪水暴涨,桥面浮土不但冲刷不去,反而增高。无论阴天晴天,傍晚桥畔都要笼上轻雾或洒下小雨,使游客和情侣们舍不得离去,古人称这景色为“海棠暮雨”。但如今我却怎么也找不到海棠,眼前只有满目的茉莉,历史哪里去了?所剩的就是海棠桥了。海棠桥建于南宋淳祐六年(1246年),初是木桥;清代康熙十年(1671年),把木桥改建为石桥,至今已有三百三十年的历史。
海棠桥是因为被称为赫赫有名的“苏门四学士”之一、北宋著名词人秦观编管横州时,面对满溪海棠,吟下“瘴雨过,海棠开,春色又添多少”的名句,而扬名海内的。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曾担任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的秦观,被贬谪到湖南郴州后,又被编管到横州,寄寓在县城西北登高岭上的浮槎馆。一年之后,又被流放到广东雷州。秦观在横州写下了《醉乡春》、《月江楼》、《浮槎馆书事》等脍炙人口的诗词。他赞美横州“鱼稻有如淮右,溪山宛类江南”,把横州当做他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