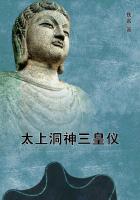我想起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我跟着村里的泥师傅学习做泥人,老师傅做的泥娃娃、泥猴,还有不倒翁,都适那么的活灵活现,就像真的一样。我们几个伙伴,也学着做,我的手慢,总楚落在别人的后面,而II还做得不好晋,心里很着急,越足焦急越是埋怨自己这双笨手,自己生气地将做好的泥兔揉碎了。冋到家黾,我把事情跟母亲一说,母亲批评我没有志气!夜里,我想了很多。以后的几天里,我很早就去了,虚心跟着老师傅学,我看着师傅青筋突跳的大手,揉着泥团,就像变魔术一样,变出好看的泥人。我精心审视着,用心学着做。一团泥在我的小手黾,揉来揉去,手上沾满湿泥。等别的伙伴到来的时候,我已经做了三个泥人这三个数目并不重要,主要是我做的泥人比别人做的都好。师傅说我,有一仅灵巧的手!我的手灵巧吗。不,是我用心了,是我自信了。我感觉,没有自信的手,没有志向的手,就会堕落成为一双废手!
人的生活和事业,是要靠双手完成的,要格外珍惜我们的这双手。双手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你自己的,一旦做了,无论好与坏都是抹不掉的。双手可以重复劳动同一件事情,却不能复制我们的才能。双手能够给我们带来辉煌,也能给我们带来耻辱。只要用好我们的手,人生就永远没有落伍者。一个明智的人,每时每刻都关注、爱护自己的双手,双手的劳动是神圣的,也是劳苦的。每一个手指的弹动,还能不断发现自身的内心世界,伴随我们的微笑获得一生的荣光。带着清新的头脑指挥我们的双手,头脑的细胞还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千万别怀疑自己这双手!
给生命来点剌激
去年的冬天,我听到这样一个事情、我所居住的廷城太平间出事了。一个平静的早辏,医院看守太妒间的老工人忽然死了,因为家人给他收尸的时候,能从他身上闻到浓浓的酒气。所以大家都疑心这个老人是喝了过量的酒而死,或是喝了假酒。所以在老马接任这个差事的时候,院方特别提出来,让他不要喝大酒:老马含糊地答应着,也给院方提了一个条件,就是把停尸房改成老马工作室。什么样的名称无关紧要,张院长同意将停尸房改成老马工作室。让张院长好笑的是,一个在澡堂子搓澡的老马,怎么说出这样雅致的名字呢?老马说是从电视里学来的。张院长笑着说:“你个老马竞来洋的!”老马解释说,他从澡堂子挪到太平间看尸,家里人都反对,他是瞒着家人来的。“再者说啦,这还不光是看尸,还要给死人整容,擦身子,背尸体,这不叫工作吗?”张院长觉得老马说得很在理。
老马是个小矮个子,微瘦,脸黑,说活时总是拖着很浓的鼻音。他过去是火车站的搬运工,还没到退沐的年龄就下岗了。五十五岁的年纪,家里又没了老伴儿,就常年泡在澡堂子里搓澡起初,老马的生意还行,后来南方扬州来了几个小伙子,就把老马的生惫给顶得够呛。那天正赶上他给医院张院长搓澡,随便扯就是:这份沾点鬼气的差事。
老马刚来的几天里,看见死人,头皮还真有点发紧,半个月过去,就慢慢习惯了,每当他给死人擦冼肴白的身子,就当成是给活人搓澡。惟一有所不同的是,这里有了女人。老马还学会了简单的美容,有吋,他还要帮着死者家属给死人穿衣服。像在燥堂子一样,他还能得到一牲可观的小费:竟然还有了给老马打溜须的人,医院旁边有个开花圈铺的王六甲就算一个。
王六甲时常过来看看老马,跟老马说说话,甚至请老马喝上一点酒。喝到节骨眼上,老马连连摆手说:“六甲兄弟,我不能喝了,真的不能喝啦!”王六甲笑嘻嘻地说:“我知道你酒量大,喝吧!”老马瞪着眼睛:“不是我不给你面子,要是在澡堂子,喝上两瓶,我也敢陪你!张院长不让我喝酒。你又不是不晓得,前一个不是喝酒喝死了吗?”王六甲就不再劝了。可他有事求老马给帮忙,就是让他把买花圈的死者家厲领过来。老马满口答应,不时领着人过来,没多长时间,王六甲的生意就红火起来。
连续好几天,老马工作室都很忙,王六甲的花圏铺也跟着热闹。这天傍晚,老马本想到王六甲的花图铺坐一会儿,可刚一迈脚,就听见外科的徐医生喊:“老马,快来背尸首啊!”老马急忙换上那件专门背尸穿的黑褂子,悻悻走上楼去。老马见到的是一具女尸,怎么死的,他从来不问,只是像往常一样,在家属的哭嚎声里,尽快把人抢出来,安放到自己的工作室。医生将死者的脸一盖,老马就背走了。老马把死者安放妥当,才看清是一个女人。过了一会儿,家属代表下来跟老马做了交待,请他给擦洗好身子,并做美容。老马接了死者家属的一百块钱,就开始了枯燥的工作。女人是车撞的,脸部稍有点擦伤,重伤在胸部,她的胸乳几乎给撞没了,身也没有伤,可是胸部的血流到下身。老马把女人的下身擦洗干净,却发现女人有一双健美的腿,白皙而丰满。这个女人的腿是咋长的啊?老马擦腿的时候,又慌张地擦她的脸,眼窝,鼻梁。颧骨处的擦痕已经被脂粉盖住。
死者的身体完全暴露在老马眼前,是那样的生动。老马真的为这个女人惋惜。他倒是希望她马上站起来。老马坐着,吸上一只烟,自语着:“年轻轻的,多可惜啊!”说着,望着那一团白软,竟然涌出一种从没有过的冲动,过去的激情也一下子调动起来了。可是激情只是一闪,就过去了。随后他的胸口像是被什么堵住一样。他自责地拍着自己的脑袋,拍得啪啪响:“你个老东西,想啥呢?真是不知廉耻啊!”老马很快把裸尸给蒙上,默默地走了。
一连几天,老马的眼前都晃动着那团朦胧的白影。老马的老伴儿去世已经七年了,七年里他对女人一点不想,那是假话,可想一想就过去了。两个儿子都娶了媳妇,大儿媳还刚刚给他生了孙子。他得给家里挣钱,不然就没人愿意管他了。晚上,王六甲把老马拽到自己的花围铺里,神秘地笑着说:“老马,兄弟知道你单身的苦处,给你找了个女人,玩玩儿吧!”老马愣愣地摇着头:“你看,我连自己都没个养老送终的窝儿,哪能再养活女人?”王六甲呲着金牙说:“你弄错了,谁让你娶后老伴儿啦?我给你找了个鸡!花上几个钱,玩玩儿。”老马连连摆手说:“我都多大年纪的人啦,哪能跟你比呀?不行!”说着就往外走。王六甲急了,一把拉住他的胳膊:“别,真是的,你不干,看看总可以吧?”老马说:“我在澡堂子里搓澡儿,啥样的鸡,我没见过?”王六甲的声音像个娘们似的低声细气:“老马,你才五十五岁,就真的一点也不想那事儿?”老马软了声说:“不想那是假的,可咱没那个福分。人家上层人士玩鸡,叫游龙戏凤,咱呢,叫流饭成性!”王六甲嘿嘿地笑了:“原来你是怕,怕给抓着?一切听我的安排,保你放心:他硬是把老马给拽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