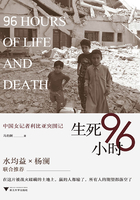老家夏天的原野是迷人的。
回到老家,只要天气好,我就往原野上走一走。那天,我踏过家门前的那条杨西木河,再走过河南岸上的一片开着白花的荞麦地,来到了老家的原野上。这里没有纵横交错的阡陌,一切都处于自然状态。山坡上有野桑树,洼地上长满白茸茸的狼尾草,野滩上的青草中开着各色野花,错落有致,蓝色的鸽子花,红色的野百合,色彩纷呈,互不侵扰。
偶有蝈蝈鸣声,随一阵清风传来。我循声摸去。一片长满沙蒿子的洼地上,有上百上千的蝈蝈在鸣唱,这里简直是一个蝈蝈王国。它们把生命化做了鸣唱,装点了这原野。没有蝈蝈叫的原野是不能称之为自然的原野的。
我听得出这片草地上,有一只蝈蝈王。风吹摇了草枝,其它蝈蝈都一时消声敛迹,惟有它不为风的摇撼所动,依然鸣唱不息,声音高亢有力,明快久远,一叫起来久久不停歇,似乎在不懈地呼唤着这绿色的原野、明亮的太阳,呼唤着这里的自由的空气。我悄悄靠近这只蝈蝈王。从下风处走走停停,慢慢摸准它准确的栖息地。其实这样的具有工作狂性质的蝈蝈是好逮的。目标暴露容易,不像那些不爱叫的蝈蝈不好找。不叫,无论如何是找不到它的。就像不干事的人不会被人找到错误一样。果然,我很快发现了它。在一人多高的蒿草枝上,它攀伏在一片宽叶间,把明翅冲太阳暖暖地晒着,惬意地随风摇荡,正起劲儿地欢叫。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只老蝈蝈,春末夏初最早出现在原野上的蝈蝈。
我轻轻举起双手,想从两侧悄悄把它捧进手心。机警的蝈蝈王突然停叫,并迅速地往下一跳,竟不知去向。
我惋惜不已。也不甘心。尽管四周有其它众多蝈蝈在聒噪,但我仍然专情于它。我耐心地等待起来。有这么温暖的阳光,这么空阔的原野,还有无数同伴的召唤,它终会不甘寂寞而露头的。果然,半小时后那熟悉的声音就从不远处的草尖上响起来了。
小虫毕竟是小虫。这次我小心又机敏地终于把这只原野骄子捧进空手心里。被它咬过的虎口处隐隐生疼,上边涂洒了一层它吐出的酱色汁液。我把它关进先编好的笼子里。它怒不可遏,在笼子里猛跳猛撞,接着又寻觅起可钻出的缝隙。我不去管它了,往笼子里塞进两片嫩叶,然后心满意足地往回走。半路上又发现了一只声音较嫩的蝈蝈,大概新出世不久,鸣叫声显得羞涩而迟缓。我心想给老蝈蝈王找个伴儿做仆从吧,于是不怎么费力地逮住这只嫩崽儿,塞进了笼子里。
回到家,我把蝈蝈笼子送给儿子说:儿咬,看爸爸给你带回来啥?
小儿八斤好奇地端详着:这里是什么虫子呀?这就是大肚子蝈蝈,大的是蝈蝈王,小的是蝈蝈王的仆从。
爸爸,这仆从怎么没有脑袋呀?小儿八斤歪着头问。怎么会呢?我接过笼子一看,也傻了。那只后逮的稚嫩的小蝈蝈,果然丢了脑袋,横尸笼中。而老蝈蝈王的黑红色铁脚,正踩着那只小脑袋。显然,这位暴君为了独霸笼中空间,咬掉了它仆从的脑袋,以泄失去自由的愤怒。这未免太残忍了,也违背了我本意。
算了,这只蝈蝈王不愿意让仆从侍候,咬死了同伴。也好,咱们就听它独唱吧!我叹口气,把笼子挂在窗外檐下。第一天下来,它没有叫。
第二天一早,小儿子就歪着脑袋守在笼下,等着它叫。这一天它还是没叫。它后背上的明翅紧闭着,没有一丝要叫的意思。看来它是以沉默来抗议着失去自由,抗议狭窄的笼中生活。它爬上笼子里最高顶处,鼓鼓的眼睛瞪视着远处的原野,一动不动。没有了自由的绿色原野,没有了随意攀爬的蒿丛绿枝,没有了此起彼伏的同伴鸣唱,没有了携带泥土野草清香的微风吹拂,没有了洗身的夜露晨霜,而被人强制地关进巴掌大的小笼子里,它是一时唱不出欢快的声音来了。我有些理解它。然而,它这种沉默,这种无声的抗议,能够坚持多久呢?
第三天,它仍旧没有叫。小儿早就失去了耐心,嚷着爸爸捉了一只不会叫的哑巴蝈蝈去玩别的了。
尽管拒绝歌唱,可它不拒绝进食,而且食量不低。那是第四天深夜的事。我正在睡梦中,忽被一阵吱一嘎吱一嘆的拉锯似的虫叫声弄醒了。一开始我还没想到那是窗户外的老蝈蝈发出来的声音。这是一个嘶哑生涩、有气无力的声音,全没了原先荒野的锐气和豪放,听着就像是一次压抑的哭泣!不过,它毕竞叫开了,向自己生命本能妥协了。诱使它的除230了这黑夜的寂静,还有来自原野的泥土之风。它终于放弃了骄傲的固执,重新开始了一种笼子里的歌唱生涯。
第五天开始,老蝈蝈就开始正常地鸣叫了。虽然没有像原野上那般自如和谐,有些断断续续,但它已习惯攀伏在小笼子塔型壁上,鼓背隆腰,不停地摩擦和震动着明翅,渐渐进入角色了。再过了些时日,老蝈蝈完全适应了笼中生活和庭院气氛,叫得非常勤奋卖力,而且不分昼夜,只要有倭瓜花吃。好像在告诉人们,是蝈蝈就得叫,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待遇,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无奈,叫是它的本分,喊叫才能证明自己是大肚子蝈蝈。
老听它没日没夜地聒噪,我有些烦了,索性把它从笼子里放出来,随便放进院角的菜畦里。我以为恢复自由的老蝈蝈,这回肯定跳离菜地,奔向原野吧。结果又使我感到意外。它依旧安详地留在菜地,爬上一棵大白菜绿叶上,还是那样日日夜夜地鸣唱,全没了原先那种奔回原野的狂躁不安,完全随遇而安了。我暗思,人何不是这样,有时也跟蝈蝈一样呢。几天过去了,我渐渐淡忘了它的存在。有一天没事,我坐在菜畦旁的树荫下读书,突然意识到好像半天没听见老蝈蝈的叫声了。我纳闷,仔细谛听良久,附近也没有传出蝈蝈叫声,走进菜地搜寻,又没发现它的踪迹。我心想它大概一蹦一跳返回原野了。到了夜里,我仍不死心地等待它从房子四周哪片草间树上突然鸣叫起来,然而黑夜一直很宁静,除了蛐蛐的叫声,没有任何蝈蝈叫声。它是果真远离这里,回归原野,彻底自由了。我心中暗暗为它庆幸。
翌日,小儿从鸡窝前拣到两根虫腿,跑来问我:爸,这是什么虫子的腿呀?
这是那只老蝈蝈的后两条腿,淡白色长腿经日晒已变得红褐,脚掌部长有微刺,显得很硬,这就是那双踩在同伴尸首的坚硬的双脚,我认得。原来,老蝈蝈被家里的母鸡或公鸡随便吃掉了。
我半晌无语,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些愀然。